薛保勤学长的诗文读着过瘾,很有一股“夫子风采,溢于格言”的劲头,貌似信手拈来,实则用心至痛,是他对世道人理的体察和醒悟。表达方法也不拘一格,有些是狂想曲,有些是旧戏文里的快板或慢板,有片段沉吟,有长气贯通,还有简洁又余音绕梁的“掐尖茶”,依文法可勉强归入偈子和双关语。他的诗不休闲,纵是娱情娱景的主题,也是删去了闲心的,“写诗浑似学参禅”,他是醒悟者,薛诗是苦酒,多喝几口,即可尝出隐于其中的人生之涩。
他的短文章给人留面子,基本上是点到即止;长文章讲方法和路数,长于给读者挖“阅读陷阱”,且有拨迷雾见亮堂的手段。他的文章讲求真情实感,情由心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难得的是,他思考的内容常闪烁“出格”之光,敢把脑袋探入“禁区”。文化上的桎梏是需要文化去突破的,动用粗暴的武手段不行,经济杠杆能撬动的也只是皮毛和外在。中国文化的雾墙是厚实的,社会的进步,需要清醒的认识力去拨开或洞开层层雾霾。清醒的认识力俗称良知,这是薛保勤作品中的可敬可爱之处。
保勤学长的作品有两个看点:第一,清醒的文化意味;第二,守文心之正。
把文章写出文化意味,清醒地表达出认识能力,在我们当代写作里是不被强调,甚至是有意识去回避的,就如同谈烹调时习惯讲“色香味俱全”这几个字,什么都谈到了,就是不涉及营养。对“文化”这两字的理解,在我们当代生活里也是存在认知误区的。比如政府有一句工作口号,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句话暴露出两个盲点:一是不理解文化的本意,不知道经济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再是违背了中国人传统行为里的一个基本规矩,我们老祖宗最反感说一套做另一套。
文化不是表面的东西,也不是多读了几本书就叫有文化,文而不化不叫文化。我是这么理解文化人的:在中国农村,几乎每个村子都有那么一种能人,谁家有嫁婚嫁娶的大事,都会请他去料理,甚至邻里失敬,家人失和,他一出面,难迈的门槛就迈过去了。这种人是最基层的文化人。高层次的文化人,对事物的认识力,以及行为方式是延此方向逐级上台阶的。
文化意识,从简单的方面说,可以理解为问题意识,发现意识,用文学表述叫发现之美。发现之美不是只看好的,漂亮的,高大全的,而是既看到生活的高地和洁净地,也要看出凹地和纳污点。每次和保勤学长闲聊时,都能具体地感受到他的问题意识,即使谈及细小的事情,他也能捕捉到事情的另一面。有一次他和我说起要下力气写一本关于陕北的书,我问他从哪些方面入手,他说不从高度写,陕北有太多具体的东西需要重新审视,尤其是一些观念和认识,更需要厘清和澄清。
保勤学长的文章有朴素的一面,文思清正的一面,是难能可贵的,在当下来讲,稍有那么一点儿出什么泥而不染的意思。
一个冬日到沈阳,见街两旁的树大多没有了叶子。叶子是树的外包装,是树的形容词。没有了叶子的树不葱茏,但接近树的本质。保勤学长的诗文就是沈阳这11月的树,自行卸去了外包装,在嗖嗖的风中传达着本真。
(作者为散文家、《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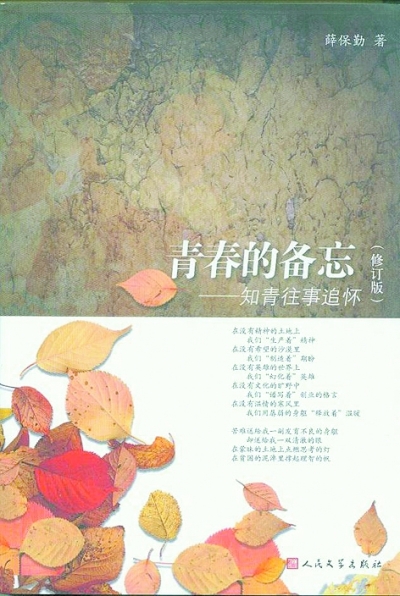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