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这辈子,最重大的事就是和老家有关的事,其他的,对于他好像可有可无。妻子、女儿(也就是我),都得和他一样对他的老家怀有浓重的感情,要不然就没啥可交流的。他已经在城里住了快一辈子,但生活内容也没有都市气息,除了每天去公园跳坝坝舞之外,剩下来让他上心的事情全部是老家来的人以及老家发生的事。比如:老家的谁谁谁病啦,他张罗在城里治病;谁谁谁家打官司,他在城里寻个能讲理的人;谁谁谁家孩子要去当兵啦,让他去走走关系……是不是有种病叫作“亲情浓得化不开症”啊?如果真有,研究这种病的人可千万一定要来研究一下我爸。
一
我想了想离家这十年来和他的交往,大概分为三个阶段——
头三年:他有一个打小就送人的姐姐,那时候他父母(也就是我爷爷奶奶)穷,养不起,孩子一岁左右就把她送人了。他一定要找回来。并且要求我协助,他强调:“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我是谁啊,我是他的女儿,帮吧。给电视台寻亲节目写信,让人来拍。那信写得,行行血字字泪的,动用了我积攒多年的写作激情和文学储备,导致我现在一抒情就恶心。人家还真的被感动了,来拍我爸和他寻找大姐的画面。节目播出之后,因为内容情真意切,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街坊四邻大妈大婶都纷纷在院子门口拦住我或者我爸,说:“哎呀昨天晚上在电视上看见老桑了的嘛,找大姐嘎?”“哎呀好感人喔,他都哭了的哇?”我就点头承认:“他是哭了的。”人家就加重语气:“好造孽喔!”
然后真的有从小和父母失散年纪相仿的人来相认,我爸挑选了一下,从几位应征者里选出了自己心中的姐姐。我问他为什么是这一位,他说:“她最有礼貌!我的姐姐就是应该懂礼!”据说有一位各个方面都符合他说的细节,就是因为“不懂礼”被他排除了。
我见到这位千辛万苦找回来的“大娘”,觉得吧哈,虽然外貌上没有任何与老桑家相似的特征,但是她性格开朗、随和亲切,而且还是一个爽朗的抽烟的老太太。我觉得她做我的大娘,也挺好的。
然后就是姐弟相认,以及紧接着的母女、父女相认,那电视台的寻亲节目都进行了跟踪拍摄,这一回全部画面都是泪眼婆娑加嚎啕大哭。花甲之年的大娘捧着花束——花束明显是电视台的主意——在去看我爷爷奶奶的路上,那眼神期待又惶恐,连我都看着眼发酸。这也是一个命苦的老太太,打小就送到了孤儿院,到老了都不知道有爹妈是什么滋味。画面中,大门一打开,我爷爷奶奶以后脑勺出镜,她扑向了他们,哇了一声拜倒在地,花束也散了一地。她呜呜呜用地道的成都口音喊着:“爸爸!妈妈!我来看你们了!”我爷爷奶奶却是遂宁乡下口音:“哎呀,大女,快起来!快起来!”
女儿和父母都是白发之人,在场的人们看了无不落泪。我在电视里看着这一画面的时候,也落泪了。我爸在旁边监督我看,见我落泪,也陪着再一次落泪。他很满意,说了句:“算是了了一件我这辈子的心愿!”我是谁啊,我是他的女儿,他说心愿了了,做女儿的心中何等畅快!我说:“哎呀,了了就好,你现在终于可以不用天天叨叨了……”
他却说:“这件心愿了了,可是我还有别的心愿呐。”
二
好,现在进入第二阶段:他要给我那将近百岁的祖祖风风光光地过一个百岁大生日。我一直觉得我们老桑家有点奇异之气,比如我爸这“亲情浓得化不开症”,还有我这百岁老祖依然精神奕奕、神思不减的精神头。我曾经和她睡一个床,我都睡醒了好几觉了,还听见她老人家在说:“……蓉娃儿,你说是不是嘛?”我就“嗯就是”一声,又睡过去。我从小最怕和亲戚睡一床,但是只要回老家,或者老家来人,我爸出于礼节,一定要我陪人家睡——好在男眷除外,都是大妈大娘奶奶婆婆之类的。她们那个唠叨,我也练就了睡觉完全不动窝,而且还能在梦中应答如流的功夫。我睡过的垫子,不多久就是一个坑一个坑的,就是因为完全不动不翻身的缘故。
好了,这个百岁又怎么献礼怎么策划呢?这成了每次回成都见我爸主要谈论的话题。他也很明确:风风光光,而且我必须出大力。他瞥了我一眼:“反正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了!咱们家族也没有比你老祖更伟大的人物了,你看着办吧!”我……是谁啊,我是他的女儿,是我老祖的重孙女啊。好在这一年,我刚刚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我说爸爸,我打算把这本书作为礼物题献给祖祖。我爸有点迟疑:“就是一本书啊,有啥子嘛?效果和请一个吹打班子比如何?”我说:“虽然在现场的效果可能不够热闹,但是全国都会有人买我的书,大家翻开书第一页就会看见我老祖过生日这件事情……”我爸一拍大腿:“好!那么就又请吹打班子,又出书献礼!”
我请了一个吹打班子,那是我爸钦定的:人民公园“豌豆尖”老年歌舞团。这个歌舞团的台柱“豌豆尖”娘娘,那是新疆舞藏族舞朝鲜舞蒙古舞秧歌舞无一不会无一不精,是我爸长达三年的偶像。他每个星期三下午都要去人民公园的坝坝捧场,有时候还要捧着一束塑料玫瑰。“豌豆尖”这个响亮的名字,就是形容那位娘娘在将近六十岁的高龄还拥有豌豆尖一样新鲜嫩气的气质。我远在北京的时候,我爸就在电话里形容她那高雅脱俗的气质,并且强调等我回来一定要和他一起观看这精彩的演出。他说这是他的心愿。还好,不是最大的心愿……我是不是得了一种叫做“只要是心愿一定要满足”的病啊?
回成都,和他一起站在人群中观看“豌豆尖”演出。虽然当时的成都细雨霏霏、寒气逼人,一群中老年观众依然兴致盎然地打着伞观看“豌豆尖”风雨无阻的歌舞。我爸是最盎然的,他眼中的神情甚至可以叫做激情,我都有点被打动了。所以,当我爸问我“豌豆尖”娘娘的歌舞是不是我看过最好的,我毫不犹豫地说:是的。
这个组合虽然在公园拥趸甚多,但是还没有被邀请去参加过商业演出,所以虽是从成都大城市去到遂宁乡下演出,也算是有人承认了他们的专业水准,在我老祖的生日宴会上演出得特别卖力。不仅把我爸喜闻乐见的新疆舞藏族舞朝鲜舞蒙古舞秧歌舞原样都演了一遍,还赠送了几个小品,其中有一个还指名道姓地送给“最懂得欣赏艺术的桑国全先生”,小品名字是“傻女婿回门”。
热闹的场面一波又一波,我那一百岁的祖祖都高兴得有点不知所措了,她几次颤颤巍巍对着麦克风说:“我是全宇宙最大的人!哪个也没有我大……”不知道是谁给她老人家喝了酒啊?唉,俺们这个家族的人,其实没喝醉时说话,也这样。一切正常。
我爸戳戳我,附耳道:“嗨,你该上去念你那个书的悼词了……”幸好人多声杂,没人听见我爸的这句措辞严重不当的话。我爸这个人,没有读过几年书,但又极好把一些书面语言挂到嘴上。在他的理解中,估计“悼词”和“献词”差不多意思而前者更加体面文雅些吧。我是谁啊,我是他的女儿。哪怕他说错了,我也能领会他的意思并帮他把要做的事情做好。我捧着新书走上台,对着台下的父老乡亲,脸红到了耳根子,用家乡话说:“各位老辈子好,我是晚辈桑格格,承蒙长辈栽培,我出了一本小说,叫《小时候》,今天我要在这里把这本书当做贺礼,献给我们最尊敬的老祖祖……”大家掌声雷动。毕竟,在我们这个小镇上,我极有可能是第一个出版书籍的人,大家都交口称赞,整个生日宴会完全符合我爸说的“风风光光”。我看着我爸在人群中激动得泪眼婆娑的样子,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觉得我算是尽到了女儿的责任。
三
我分析过我为什么对我爸的心愿如此言听计从,因为我想离开他,去过自己的生活。我打心眼里就不想被束缚在亲情的这根绳子上。我爸察觉到了。我怀疑这第三个愿望就是他为我量身定做的——他要编写一本家谱,希望我能大力支持。我惊慌失措地立马捐了五千块钱,然后忐忑不安地等待我爸接下来要安排我做的事情。我希望他千万别要求我回家,回到他身边生活。
他开始和家族里另外一个有此宏愿的老辈子伯伯一起着手这件大事,那位大伯略通文墨,自封家谱“主编”,我爸为“副主编”。每天主编和副主编在一起整理桑姓历史,从上古到近代,从近代到当代,煌煌巨作,洋洋大观。有些我觉得还算有根有据,另一些就可能有点失实……最终的效果是,让每一个姓桑的人都觉得自己的姓大概是有姓氏以来最伟大的姓了。好在家谱不管如何歌颂桑姓,还是交代了我们的祖先是从湖北一个叫作麻城的小地方来到的四川山沟沟,是逃荒的兄弟俩,看上去是很真实的,也和我知道个大概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史相符合。
由于我,作为一个女生晚辈,率先捐出了五千元巨款,而且还从事文艺工作,所以被写入了家谱前页的“优秀人物表”中。我爸要求我随时把这本家谱带在身边,给身边每一个人宣讲我们桑家的光荣渊源。家谱上下两册重达四公斤,平时要供在家中的最高处,初一十五还要上香。
又到了一年几度我和我爸相处的温馨时光,内容当然要从最近的热点家谱说起啦。他把家谱从柜子最高处小心地取下来,恭恭敬敬地从第一页翻开,一页一页往下数着,嘴里念叨着班辈的排行:“看,这个桑俊钟,是你的爷爷;桑俊钟的大儿桑国全,就是我;桑国全的女儿桑格格,就是你……”我突然觉得后背一阵激灵,有种神奇而亲密的巨大能量拍了我一掌。说实话,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对于事情本身并不真的投入,甚至有点戏谑地看待它们,或者只是在换取离开父亲之后内心安心的理由:远离的女儿也是女儿,远离的女儿也要尽到女儿的责任。现在他认真虔诚念着祖先名字的声音震了我一下,我把背坐得直直的,我爸好像也感觉到什么,停了下来,看了我一眼,说:“今天你好乖,和以前不一样喃。”我说:“爸爸,认真听长辈的话,这个不是我们老桑家的优良传统么?”他眼神欣喜:“真不愧是我老桑家的姑娘,和现在外面那些五马六道的屁娃娃就是不同!”
四
前几天,爸爸给我打来一个电话,电话里格外客气。我说:“爸爸,你那么客气干啥,有事情请讲噻。”他“唉”了一声,说:“现在这个城里头啊,空气不好、水源不好、吃的也不好……”我说就是,然后喃?他又说:“城里头住的人,不像是乡下那些乡亲亲热人,说话都皮笑肉不笑的……”我说是,然后喃?他终于说出了自己最后一个心愿:“你爸爸我啊,想回到乡里去住,养点鸡养点鸭,种点菜钓点鱼……”我说好得很啊!他又说:“但是老房子已经要垮了,住不得人了,可能要搭一个小二层的木房子,需要……”我立即说:“我马上给你打钱。”
他很不好意思地说:“乖女,这么多年来,我说啥子你就做啥子,你的心意我心里有数,这真的是你爸爸最后一个心愿了。人都老了,叶落归根,也没有啥子时间再有心愿了……”我说:“爸爸,放心,你的这个心愿,其实也是我的心愿。我也希望能离开嘈杂的城市,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现在你先去,我每年都回来陪你住。”
他那么啰唆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半天都没有说话。我又说:“爸爸放心,我会回到你身边的。”电话那边,他终于一连串地说:“好,好,好。”
(摘自《不留心,看不见》,桑格格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
(桑格格 70年代末生于四川成都,现定居北京,专职写作。已出版作品《小时候》《黑花黄》。)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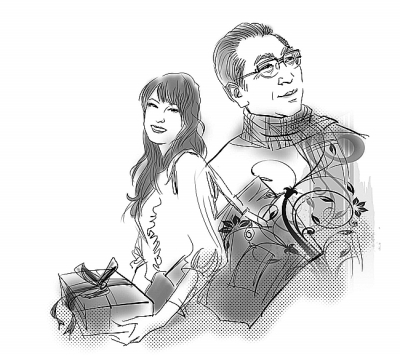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