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是1999年《商代史》刚立项时的合影,照片上我的头发还比较浓密,现在差不多都掉光了。”在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宋镇豪的一句话,引得现场听众把目光从屏幕上的老照片转到他那光滑的头顶,原本严肃的会场发出一片笑声。
笑过之后,读过《商代史》的人们,不禁联想起宋镇豪在此书总序中写下的两句诗:“少壮拳拳灯色暗,玄鬓岁月渐稀疏。”为写出一部11卷600多万字的《商代史》,宋镇豪和他的团队殚精竭虑,消耗了十几年的光阴,却“拉长”了中国古史,中国上古史体系中重要的缺环由此补上。
不负近百年的等待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越向前追溯,传世的历史文献就越贫乏。距今三千多年的商代是什么模样?生活时代距商代不远的孔子就曾有“文献不足征”的感叹,汉代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只留下不足3000字的记载,这让向来“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说话”的学者捉襟见肘。
1921年,胡适在致顾颉刚的一封信中说:“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宋镇豪常常会想起这段话。
现代意义上的古史研究经历了近百年的积累和发展,是否到了可以重建商代史、“拉长”东周以前古史的时候?宋镇豪认为,百年来殷墟甲骨文、商周青铜彝铭研究日新月异,先秦简帛文献屡有新发现,商史文献不足的困境得以改善,与此同时,考古学研究也使学者对商代社会有了崭新的认识,《商代史》重建工作的条件已经具备。
立项之初,宋镇豪就确立了一个目标:“《商代史》不应是单纯的文献整合,不应是古文字资料或考古学成果的搜集和堆积,而应该是一部全方位、整体性的断代史著作,要形成一门新学问。”
为了这个目标,13位先秦史学者汇集到一起。王宇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撰写《商代国家与社会》;杨升南,“夏商周断代工程”文献组组长,撰写《商代科技与经济》;宋镇豪,撰写《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常玉芝,撰写《商代宗教祭祀》;罗琨,撰写《商代战争与军制》……
破解三千年前的谜题
撰写这样一部恢宏的《商代史》绝非易事。
王宇信时而会遇到一些理不清的问题:“有时面对稿纸,怎么也想不出所以然,很快半天就过去了。虽然我坚持写下去,但写出来自己看了也莫知所云。”好在,老友杨升南总是安慰他:“学到疑时方能悟,文到穷时自有神。”杨升南虽然早年出版过《商代经济史》,但近年来新发现的古文字、考古材料亟待被吸纳其中,他还是一位恶性淋巴瘤患者,在经历了痛苦的治疗之后,病情刚好转,就投入书稿写作。
商代有多少人口?这一直是历史之谜。而人口数量的增减直接影响社会的发展进程,书写《商代史》,无法回避。没有直接材料,就间接考察。商代有多少城邑?每座城邑面积多大?每户占地面积是多少?一户有几口人?《商代史》一一求解,仅罗列出的考古数据就达37页之多,终于有了商代人口总数“商初为400万至450万人,晚商大致增至780万人”的结论。
喜热的大象、犀牛为何在地处北方的殷墟出现?曾有学者认为它们属于外来物种。《商代史》结合殷墟动物、古土壤、植物三方面的证据,证明商代中后期的殷墟地区气候比今天温暖湿润,既有森林、草原,又有大片的沼泽与河流。因此,这里不仅有大象、犀牛,还有水牛、竹鼠、漆树等现在主要生活在南方的动植物。
据记载,灭夏建立商朝的汤“始居亳”,亳在哪?历史学界、考古学界都十分关心,却莫衷一是。通过对文献与考古材料的分析,《商代史》指出应“在距离安阳殷墟几十里的范围内寻找亳邑”,进而考证出“亳”在今河南省内黄县一带的结论。随着这个问题的解决,文献中不少关于古地理的记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就是这样,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相结合,前人研究与当下学术相贯通,“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一个个细微、分散的难题勾勒在一起,商代历史的脉络逐渐清晰,中国的古史由此延伸。(本报记者 杜 羽)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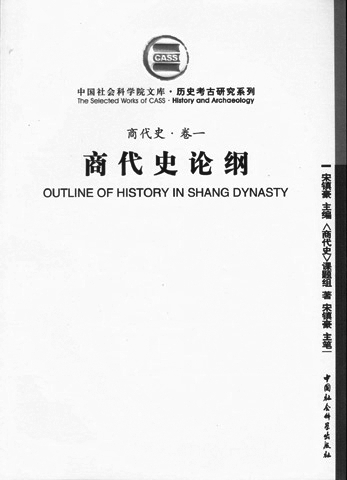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