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书柜最显眼的位置,展放着周恩来总理逝世后,《人民日报》编辑出版的一本纪念文集《五洲的怀念》。每当自己出版了作品,我总是把样书放到这本文集的前面,让敬爱的周总理第一个看到我的成果。等到下一次再有新书出版,便把前一次的换下来,迄今已换了42次……
与周总理结缘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历史老人的安排,亚得里亚海岸的“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成了与我们最要好的兄弟友邦。随着中阿友谊蓬勃的发展,阿尔巴尼亚语翻译成了中央各部委非常紧缺的人才。
1964年,我从北大俄语系毕业后,服从党和国家的安排,奔赴遥远的阿尔巴尼亚留学3年。1969年8月,我完成了陪同中国专家在阿工作的任务回国以后,有5个中央部门抢着调我去工作,其中总参某部和人民日报国际部为调我争执起来,最后争到周总理那里。因为新中国建立以来,报纸的国际宣传工作,一直是在周总理领导下进行的。周总理对人民日报国际部负责人戴枫同志说,最近一个时期,他在报纸国际版上,经常读到署名“红山鹰”的阿尔巴尼亚通讯,文章写得不错,看来作者是懂阿尔巴尼亚文的。为了加强报纸对阿尔巴尼亚的宣传,国际部是否可以考虑调这个“红山鹰”到报社工作?
戴枫同志告诉周总理,“红山鹰”正是他们要调的郑恩波。周总理高兴地说,这样的话,郑恩波还是到人民日报国际部工作合适。于是,总参某部便把事先准备好的调用材料主动转交给了人民日报社。报社以“特事特办”的办法给周总理打了调人报告,总理很快作了批复。这样,人民日报国际部便很顺利地从我所属的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把我调到了人民日报社。
当年9月16日,我满怀一个贫寒的车夫之子彻底翻身,当了国家主人的幸福感、荣誉感和非同一般的责任感、使命感,兴冲冲地走进王府井大街277号虽不很高但却显得异常神圣、庄严的人民日报社大楼,成为该报的翻译、记者,以笔为武器的新闻战士。这件事乐得我几天合不拢嘴,我反复地想:一个刚30岁的毛头小伙子,能得到驰名中外的伟大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文武双全的一国总理周恩来的关注与重视,这不仅是我们郑氏家族多少代的莫大荣耀,而且也是故乡盖州乃至营口地区历史上的大喜事啊!
44年前,在周总理亲自关心下,我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是我一生中迈出的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步,因为这一步为我终生的事业定了位,铸就了我平生既从事新闻报道、文学翻译,又搞文艺评论的三栖文人的模样,并激励我为成为一个真正的阿尔巴尼亚文化行家拼搏不息。周总理是塑造我这个文学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综合形象的设计者。
到报社不到10天,领导就嘱咐我做好陪同即将来华访问的阿尔巴尼亚新闻代表团的工作。10月16日,周总理要接见代表团,由我担任现场翻译。我既高兴,又有些紧张,心里想:一个月前,周总理批准我调到报社工作,现在马上又要我给他老人家当翻译,我也太有运气了。但是,一旦译不好,译的过程中打奔儿,怎么办?我知道周总理的法文很好,可用法语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交谈。阿文与法文比较接近,我怕有的词译不准,影响周总理的情绪,甚至影响整个接见。而且,不久前,周总理与苏联总理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会晤这件事,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如果总理谈话中涉及到此事,政治术语更要译得准确无误,不能出丁点儿差错。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就更不安了。陪同代表团的资深记者戴枫同志见我惴惴不安的样子,便很体贴地给我打气:“要有信心,保持平静、沉稳的心态。总理特别慈祥可亲,很体谅翻译。你大胆地译,就像在一般场合一样,没问题……”戴枫同志如兄长般的关心与鼓励,让我紧张的心情平静了许多。
下午4点整,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不太大的会客厅里,周总理面带笑容,精神矍铄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亲切地与每一个人握手、问好。戴枫同志指着我告诉总理:“这就是我们刚刚调进报社的阿尔巴尼亚语翻译郑恩波同志。”
周总理像长者对待孩子那样亲热地看了看我,握着我的手用力地摇了两下。这一握蕴含着他老人家对后生晚辈无限的关爱、信任和厚望,我顿时感到太阳穴的血管怦怦跳得好厉害,腿脚和双手变得轻飘飘的。
周总理接见外宾的讲话,向来都是书面体的,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很精彩的文章。那一天,他对阿尔巴尼亚新闻代表团的讲话,同样具有这一特点。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他主要是就自己不久前与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会晤一事,向阿尔巴尼亚记者朋友交了个底。口气极为真诚、亲切,是只有对真正的同志和朋友才能讲的体己话,措辞言简意赅,概念清晰精确。我越译信心越足,越流利,主宾双方的脸上都露出会心、满意的微笑。此刻,我再也不紧张了,呼吸也平稳下来。突然,总理转过脸来,和蔼可亲地问我:“最近,报刊上发表了毛主席关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一切侵略战争的新语录,就是‘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的那一段,你会背了吗?”我难为情地回答总理:“还不会。”总理说:“这样吧,我一句句地说,你逐句译。”于是,总理便有板有眼、一字不差地把长长的一大段毛主席最新的语录从头到尾背了一遍,我也不打奔儿地译了每一句。
接见结束后,周总理要和阿尔巴尼亚记者朋友们一起照相。按惯例,我和参加接待的同志们都自动地闪在一边。周总理一边向我们招手,一边说:“都过来,大家一起照嘛!”然后对外宾继续解释说:“翻译和接待的同志很辛苦。从前,他们只是忙忙碌碌地工作,照相从来没有他们的份儿。现在,我们就要改变过去的做法。”总理的这几句话是我没想到的,眼前的一切顿时变得更加绚丽多彩起来,我跟在戴枫和接待组的几个同志的后面,站到最后排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上。第二天,这张对我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献价值的照片,便在《人民日报》上登了出来。这张照片是我一生全部照片中最珍贵、最富有光彩的一张!
圆满完成了周总理接见代表团的翻译任务,接待组的全体同志感到轻松了不少。晚上,戴枫同志与我聊了许多,他说:“这次我们调你来报社工作,惊动了总理,他老人家讲了话,不然你是调不来的。今后要好好干,可别辜负了他老人家的期望。我们国际部很幸运,多少年来,一直在总理直接领导、关怀下开展国际宣传工作。总理多次要求我们都成为自己负责的国家的研究专家,要精通一国或几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情况……你很年轻,刚到30岁,要有信心,努力成为一个‘阿尔巴尼亚通’。”
永远铭记周总理的恩情,不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努力成为一个阿尔巴尼亚通。这是我调到人民日报社,特别是听了戴枫同志转达的周总理对从事国际宣传的人员的要求之后,在心里立下的誓言。
牢记总理的教诲与嘱咐
陪完了阿尔巴尼亚新闻代表团之后,领导又要我做好陪同解力夫和戴枫领队的中国新闻代表团赴阿尔巴尼亚访问的准备。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中阿关系第一次遇到了小小的波折。特别重视中阿关系的周总理,为了确保我党政代表团和新闻代表团的访阿圆满成功,两个团出访前夕,在人民大会堂特别接见了两个团的全体成员,我有幸听到了周总理的教诲与嘱咐。他老人家对阿尔巴尼亚人民纯真的友情和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成为我一生做好中阿文化交流工作的指导思想。40多年来,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对做好这一工作的决心与信心都毫不动摇。
“文革”中好人遭诬陷、受迫害的事司空见惯,我也没能例外。但没多久,领导报社运动的人又对我说:误会了,咱们还是一个藤上的瓜,是阶级弟兄。于是又恢复了我在外事岗位工作的资格。
1974年国庆前夕,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代表团来我国访问,人民日报社负责接待该团。已经正式恢复名誉、重新走上外事工作岗位的“红山鹰”又陪同代表团当了翻译。9月30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盛大的国庆招待会上,我陪着阿尔巴尼亚记者朋友,坐在离主席台最近的第一排正中间的一张大餐桌旁。当庄重、洪亮的迎宾曲振奋人心地响起,周总理率领党和国家领导人缓缓地走上主席台入席时,我贪婪的目光一刻也没离开他。望着他那比5年前与我握手时明显消瘦了许多的面容和一双依然锋利、炯炯有神的眼睛,我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我想起了9年前他老人家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在我驻阿大使馆的大厅里教我们学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红梅赞》的幸福情景,还想起5年前我调到人民日报社,他对我的关注和殷切期望,更联想到这5年来自己走过的坎坷道路,差点儿被打成“黑乌鸦”的遭遇,心里顿时翻涌起一种苦尽甘来的幸福感。主席台上首长们开始向周总理敬酒了,但周总理没有站起来,有人替他喝酒还礼。我的心怦然一跳,“莫不是总理的身体……”我不敢再往下想。
从这一天起,周总理的健康状况便在我的心里结下了一个疙瘩。
此后,报社国际部又多次派我赴阿访问,并要我做好到阿尔巴尼亚任常驻记者的准备。为了解除我的后顾之忧,报社政治部和国际部想方设法把我爱人和两个女儿的户口从辽宁盖县(今日盖州市)迁到京郊东坝河畔的北楼梓庄,彻底结束了我多年来经济困难靠公家补助、粮票要同志和朋友赈济的苦日子。我的情绪特别好,美好的未来正在向我热情地招手。然而,乐极生悲,1976年元月9日的一声炸雷炸得我头晕目眩,心撕胆裂,几乎都站立不住了。收音机里传来中共中央、人大会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讣告,我们敬爱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天哪,两年来不敢去想、不愿去想的这件最可怕、最叫我心惊胆战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这叫我们一家人怎么承受得了啊!生着了火的炉子我丢在一旁不管了,泡的玉米渣也不淘了,踉踉跄跄地回到屋里,全家人抱头哭成一团。那是举国同悲,万民共泣的日子啊!
根据上面的规定,各单位一律不开追悼会,但在总理生前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可以到北京医院参加与总理遗体告别的仪式,我当然有这个资格。国际部领导戴枫同志和即将成为报社级领导之一的潘非同志都分别正式地将此事通知了我。
在北京医院一个不太大的告别厅里,我眼含泪水,向我无限尊崇的慈父般的周总理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可我觉得怎么也表达不尽对他老人家大海一般的深情。第二天上午,我又冒着凛冽的寒风与国际部的几位同志到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站进了成千上万人沉痛悼念周总理的队伍中……
将周总理的骨灰撒在祖国大地和江河湖海的那一天,我站在报社的楼顶上,仰望着载有总理骨灰的飞机向长城方向飞去,久久不愿离去,直到飞机在湛蓝的天空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时候,才迈着沉重的步子,挖心摘肝似地走回办公室,站在窗户旁边,望着王府井大街呆呆出神……
“阿尔巴尼亚通”是我的毕生追求
我不能整天沉浸在悲痛中,决心化悲痛为力量。从那一天起,我对阿尔巴尼亚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的钻研更加投入了。从当天下午开始,我就将报社实际上是为我一个人订的、几年来的十来种阿文报刊在几张办公桌上摊开,剪起报来,然后分门别类装订成“工业成就”“农业成就”“教育战线”“群众文艺”“历史与考古”“文艺评论”“著名作家研究”“优秀通讯”“优秀诗歌”“影视评论”十大厚本,我命名为《郑氏阿尔巴尼亚百科全书》。这十大厚本阿文剪报成了我的宝贝。我反复地看,多次有效地使用,使我对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土虽小但人民精神可嘉的“山鹰之国”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我觉得自己距离周总理要求的“阿尔巴尼亚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毕竟是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阿尔巴尼亚通”,必须读大量的阿文书。留阿期间虽然买了不少书,但在阿尔巴尼亚书籍的海洋里,我那有限的两大木箱子书,实在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毛。王府井外文书店帮了我的大忙。整个“文革”期间,这家书店只卖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书,地拉那书店卖什么书,这里就有什么书。阿文书又非常便宜,因此,这里便成了我落脚最勤的地方。那时,我每月的工资只有62元,凭这一点钱养活一家4口人,日子过得有多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即使如此贫寒度日,我每月还是至少拿出5元钱买阿文书籍。因为我常到那里买书,书店里的工作人员都认识我了,其中有位叫祁从贞的老大姐待我尤其热情友好,书店里每次进了新书时,她总会打电话及时通知我。后来,中阿关系急剧恶化,书店决定将阿文书下架送造纸厂造纸,祁大姐立即电话告诉我可以到书店免费随意挑书。于是,我从房产科借了个平板车,到书店将各种阿文文艺书籍拿了个齐全,甭提有多痛快了。
过了几天,我在北大俄语系读书时的老同学、我的入党介绍人、已荣任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的赵惠媛同志,也打电话通知我可以到他们公司在通县的书库取一批阿文书。七月里一个雨过天晴、骄阳似火的中午,我骑着加重自行车,从我居住的东坝河畔的楼梓庄兴高采烈地向通县奔去。骑了三十多里泥泞难行的土路,顶着火辣辣、毒巴巴的太阳,汗流满面地赶到了书库。这里是外文图书的天堂,阿文小说、诗歌很多,没用几分钟,我就挑出10多本以前没有买过的书。后来,还把30卷的《恩维尔·霍查选集》也牢牢地封在加了一块长木板的车座上面。道路坎坷,烂泥满地,不时还要趟过脚脖深的污水。我担心车子倒了把书弄脏、弄坏,干脆不骑车了,手推车子吃力前行,硬是用两腿量了三十里泥泞路。赶回村边时已经是村烟袅袅做晚饭的时候了,我累得口干舌燥,凉白开水连喝三大杯还不解渴,可心里却是甜丝丝的。
“文革”后,我又重回社科院外文所工作。1990年夏天,应阿尔巴尼亚的特别邀请,我作为阿尔巴尼亚学学者和作家,再次访阿一个月。在阿尔巴尼亚我不仅耳闻目睹、亲自感受了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生活和思想状况,而且还拿到了一批很有价值的文艺书籍,其中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的《阿尔巴尼亚百科全书》和阿尔巴尼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编的权威性著作《阿尔巴尼亚文学史》,都是我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至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几十年的老朋友,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诗人,影片《第八个是铜像》《广阔的地平线》的原作者德里特洛·阿果里对我异常亲切、热情的接见。他代表作家与艺术家协会赠送给我8名阿尔巴尼亚当代最著名、最重要的作家的精装本文集(总共50卷)。可以说,他把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的精华都打包送给了我。再加上8年前雷法特·库卡依代表复兴出版社赠送给我的民族复兴时期的重要作家的文集,我小小的书屋便成了全国珍藏阿尔巴尼亚文学名著最多、最全的圣地,这让我感到分外荣幸与自豪。
几十年中工作地点虽然有两次变动,但成为一个“阿尔巴尼亚通”却始终是我追求的最崇高的理想之一。如今,当我再次盘点一下几十年的劳动果实时,不由得诚惶诚恐、满面汗颜。我真的把阿尔巴尼亚文学、艺术、文化搞通搞透了吗?我真的成了总理所要求的那样一种“阿尔巴尼亚通”了吗?差得远呢!我想,我还要写出、译出多少更新、更精、更尖的作品,才能不辜负周总理的恩情与期望?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外文学研究员,中国作协、译协会员,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外籍荣誉会员,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会长)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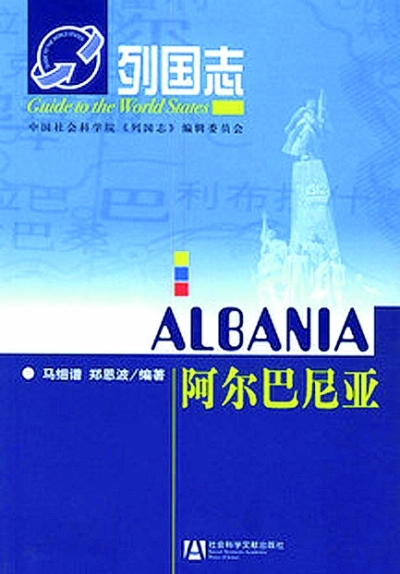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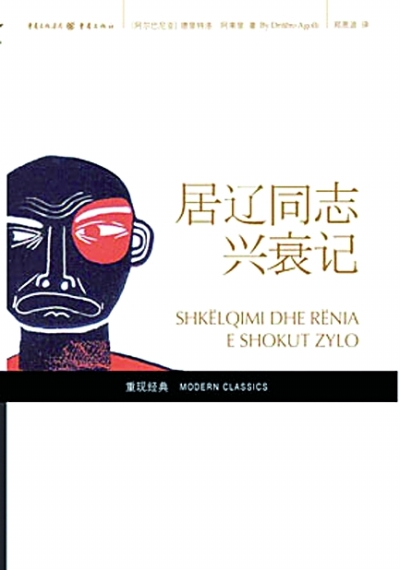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