辍学后,我成了梅子乡第一任邮递员。
邮电所用彩条布仓促隔出,有一扇面街的窗户,稍作修整,我成了那十多平方米的临时主人。
离我最近的是一个裁缝铺,里面姓蒲的师傅五十多岁,年年招纳一批徒弟,那些徒弟多是想有一技傍身的女孩子,个个头脑灵活,手脚伶俐。于是我就认识了那里叫香姑的女孩子。
香姑要帮她弟弟寄一封写给南方某家报社的信件。她问多少钱。她递来一张皱巴巴的一元钞票。不挂号还要找回几毛钱。香姑接过零头,转身就走。眨眼间,她又回来了。她依旧贴在窗沿边问:就这样了?放不放心哟?那声“哟”拖得很长,软绵绵的。我说一般不会丢的,再说也不是啥宝贝。我的回答令她很不满意。她睁大了眼说,你得保证能寄到才成。香姑说,那信里是我弟弟熬夜写出来的宝贝,可丢不得。
每隔一个星期,香姑就要把她弟弟的宝贝装进信封,托我寄给某某报社或杂志。香姑后来说,她唯一的弟弟因为小儿麻痹,落下了残疾……讲完后她提出一个请求。她问我能不能把外边寄来的信封上的旧邮票给她。这是不符合规定的事。我告诉她:如果是集邮,不如省省吧。香姑手足无措。以后,她再未提及此事。
香姑照常来帮我做饭。临到吃饭,我留住香姑,顺便还拿出她当天要寄出的一封信给父亲看。我想夸赞一番香姑会写文章的弟弟。
我看见了一个不愿意看见的细节:邮票上有一个裂纹,虽拼合精细,但仔细辨识仍能看出个中端倪。我以各种理由推测这种做法,结合香姑的境况,一种从未有过的酸楚感觉攫住了我的心房。显而易见,香姑或者香姑的弟弟在耍小聪明,他们把别人用过的旧邮票拼贴了起来。
香姑再一次拿来信件的时候,我故意把信封放在桌上。我说这封信肯定超重了,得再加贴一张邮票。接下来,我把一张崭新的邮票贴在了那张邮票上面。自从这件事情以后,大约半个月我都没有看见香姑了。她离开了隔壁的裁缝铺。
又过了大约五个月,我收到香姑从遥远的南方寄回的两张汇款单。钱多的一张寄给她的家人,钱少的那张写着我的名字。我揉了揉眼睛,确定那真的并非别人的名字。她另外还写了一封信,给我说明了寄钱的原因。真相很残酷,但有时也很温馨。香姑已经是南方一家制衣厂的打工妹,她的手艺派上了用途。
半年后的某一天,香姑的弟弟抱着一本书出现在梅子乡的邮电所前,阳光照着这个执着于文学的残疾男孩——他的姐姐帮他自费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子。
而我,正在去往香姑所在城市的路上。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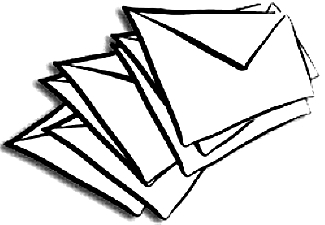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