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诗歌似乎日益被大众疏远,漠视,“当今时代,诗人何为?”不断有人发出类似疑问。然而,事实上,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仍有不少诗人在坚持诗艺探索,严肃思索诗歌问题。法国诗人克罗德·穆沙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他曾多次访华,不久前还来到中国云南,参加由云南师范大学主办的首届“西南联大国际文学节”。我们特邀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诗人李金佳翻译了穆沙的一篇诗论。本文中,在“何谓诗”这一问题统领下,穆沙通过对几位诗人的解读,发出了他关于诗的沉思。
马拉美:诗的痕迹
美国诗人华莱士·斯蒂文斯说过,诗就像是深夜冰封的雪地上,一只猫走过时发出的足音。这是描述诗的一个根底性的意象,混合着视觉与听觉。它让我想起德彪西的钢琴前奏曲《雪地上的脚印》。那是一种极为简约的音乐,紧贴着沉默前进,每一个音符都在标志向前跨出的一步,在节奏的驱使下,行进于黑夜里一片苍茫而寒冷的雪地中。
读诗,倾听一个可以被视为诗的句子,不就是感觉语言的各种特征是如何借助言说,在某一片雪地、某一个平面上,留下了不可抹去的痕迹吗?诗的痕迹赖以生成的这个平面,或者说介质,非常特殊:它具有很强的韧性,既支撑着痕迹,又抗拒着它们,构成诗歌生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语言的各种成分,原本处于一种冷漠的惰性之中。而诗,诗留下痕迹的过程,使它们豁然活跃起来,全都变得同样重要,像步子那样可以一个个计数,而不再只是一种潜在之物,一片等着人穿行而过的空场。
语言借助诗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这种实现尽可以无比精致,却终归只是顺着语言的固有倾向而进行。在诗中,语言总是仍旧保有某种变动的可能,即便这种可能性因诗的完成而变得轻微;总是仍旧处于悬而未决之中,这种悬疑不易觉察,然而却是决定性的。语言并不因进入诗而变得安稳。相反,它不停地震颤着,无法自我规定,就像贾科梅蒂素描中的那些线条。
承认语言在诗中保有可能性,就是承认诗有一个“底子”,而且非常重要。斯蒂文斯把这个底子想象为一层包着冰壳儿的雪。的确,诗的介质在诗的深处延展着,它可见可闻,具有韧性,容许诗的痕迹一步步刻印于其上。时间——诗句排列的先后次序,空间——诗歌行为的瞬时开拓,交会于这种介质之上,并因它的韧性而互相促发成为真实。诗的介质抵抗着诗,诗人只有凭借重力的压迫,才能使这种抵抗一点点减弱,成为他所希望得到的那种支撑。诗人每一次都能确信自己在写一首诗吗?他只是感到自己正把一些印记留在一个底子之上,这底子排斥着他,因此他必须刻画得尽量有力。
诗与诗的介质之间进行的这场较量,将时间和空间以一种局部然而强烈的形式调动起来。是否可以说,诗因此蓦然置身于一种最广泛意义上的时空延展之中?瓦雷里讲到他初读马拉美的《骰子掷出并不能废除偶然》(后文简称为《骰子掷出》),为诗中的时空感心醉神迷:“在这里,真的是空间在说话,在遐想,不断地为时间制造一个个形态。”在《骰子掷出》和其他现代的诗歌杰作中,时间与空间猛然灌入,骀荡于诗的介质之上,嚣然地彼此鼓动加强。这个特征,大概与现代整体的历史变迁有关。历史变迁超越诗,构成诗发生发展的背景。然而,它又总能进入诗,渊沉于其中,因诗内在的张力而获得密度。
两个世纪以来,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诗都以它自己的方式经历着人类的总的历史。许多来源久远的传统被抛弃,许多公认的形式和仪式被搁置,而正是它们,曾在漫长的时代保证了诗的社会性,使诗人得以相互接近,彼此衡量。马拉美在《诗句的危机》中,将自由体诗的诞生归因于现代特有的个人主义:“从此任何人,凭借他个人的技巧和听觉,都可以自我构成一架乐器。”在马拉美自己的诗中,其实只有一首《骰子掷出》放弃了“百代相传的伟大风琴”,转而进行自由体的创作。的确,现代个人主义的内涵,不仅是个人的奇思异想,更还有一种弥漫宇宙的孤独。
自由体诗使诗丧失了原先那种公认的、一眼即可识别的形式。从此,每一首诗都必须一步步地独自探索,以一种总是在更新的赤裸,建立自身的特征,并使它们成为一种必然。诗的特征不再遵从任何事先规定的模式。而与此相应,诗的介质变得陡然重要起来,因为是它,只是它,使每首诗的特征成其为特征,使雪地中穿行的猫的脚步,能够一次次轻轻落下,发出细切的声响。在传统诗歌的写作中,诗句周围的空白只是一个消极的陪衬,留在那里以便剪影出诗句的姿态,比如说一首商籁。而在现代诗中,空白活跃起来,变成一种动力,冲进诗本身。作为一种气息,它总是与书写的气息相吹相薄,有时承受后者,有时又把它旋抛到半空,甚至永远地打断。
策兰:诗的空白之处
诗与围绕诗的空白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阅读保罗·策兰的诗来理解。在策兰的诗中,词语的每个动作都立刻受到抵抗,言语的每一次发出都立刻激起一股回荡,将它拦腰斩断。沉默总在运动着,冲击、驳回每一个诗句,并把下一句里即将成形的话语按压下去。诗总在重新开始,继续尝试;然而,词语的核心其实早已破碎了。
策兰诗的字里行间,总是让读者感受到历史的断裂。纳粹德国对欧洲犹太人的屠杀,构成这些诗一个永恒的背景。诗句的稀薄制造出一种缺失的效果:本该在的人不在了。这种稀薄感并非单单来自表达的省略,它其实是一种顽固的追求,它要把某种最根本、最性命攸关的东西,通过词语的脆弱组合,重新创造出来。
在他1963年出版的诗集《无人的玫瑰》中,有一首诗叫作《苏黎世,白鹳》,题献给内莉·萨克斯。白鹳是苏黎世一家旅馆的名字,1960年策兰曾在那里与萨克斯相遇。同他一样,萨克斯在二战时也曾饱受纳粹迫害,家破人亡。诗很短,最后几句是:“可我们/不知道,你知道吗/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
这些随生随止的诗句诉说着一个渴望,一种困难:在生活中,在言说里,怎样分辨出什么是重要的,什么不是?这种分辨的意义,在那场惨痛的历史浩劫之后,变得格外重要,然而却越发难以达成。策兰的诗,让音节和空白互相碰撞,用呼吸秘密地计数,它以一种不可预计的方式进展,不遵从任何前定的格律。同时,这首诗也是一篇对话,收尾的这几句是引用,它们出自另一位诗人之口。因而,在作者追求的那种最根本的东西之上,就始终笼罩着某种不确定性:“重要的”东西,可以是一首短诗的构成,一场交谈的进行,也可以是——诗在头几段影射出这一点——某种广大无比之物,比如人与人互相铰接着的生命,比如他们之间永远都被错误地揣度着的重重纠葛。
策兰原籍罗马尼亚,父母在二战期间死于纳粹集中营。二战后他辗转来到法国,在巴黎以教书和翻译为生,用德语从事诗歌创作。1970年4月,他在塞纳河投水自杀。得知他的死讯后,亨利·米肖写过一首悼念的诗,名为《日子,所有日子和日子的终结》。在诗中,米肖把策兰之死比作“风落深渊的一日”。空气,原本是生命和话语的元素,现在却成为一种致命的威胁。水,从柔软的浸润,转而成为凌厉的破坏力,凶猛地斩断诗人的生活和工作。米肖那首诗的最后几句是:“我看到僵直不动的人/躺在平底船里/出发。/无论如何总是出发。/水的漫长的刀子会中止言词。”
米肖:诗的变形力
我的诗人生涯从阅读亨利·米肖开始。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偶然读到米肖的一本诗选。突然之间,诗在我面前变得真实,像我呼吸着的空气,使我的生活成为可能。当时我十五六岁,住在奥尔良,那是一个阴沉无光的外省城市,还没有从二战的大破坏中完全恢复。法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气氛让人窒息。殖民战争一场接一场地打下去,先是印度支那,然后是阿尔及利亚。在那种环境中,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是怎样从他那小小一隅开始关心历史,注意暴力的?又怎样厌恶社会,因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都表现出一种奴性,不论从政治还是从道德上说?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当初我那么愤怒的原因。
1956年出版过一本书,叫《艺术家的变形》,是画家安德烈·马松写的评论集。书中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凹处于一场世界范围的变形之中。如那些身在风暴中心或海上旋流的人一样,我们再也感觉不到空间给人的安全感。”马松的画,一直追求涡卷旋飞的布局效果。而此处他的词语,更是清晰地把这种特殊的时空感表达出来。这是一种政治感觉,也是一种诗的感觉:一场变形,从卡夫卡到卡内蒂等许多现代伟大作家都预感到、经验着、书写出的变形,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它触及整个世界,关系到每一个人。
几乎就在马松写下这些句子的同时,我第一次读到米肖的诗,并且被诗中的变形,或者说“变形力”,深深地打动了。米肖的诗句显示出这样一种力量,能把读诗、写诗、全身心投入诗的人,从他原本所在的地方,从他被指定的身份里,猛地拔离出来,甩向高处。你一旦跟这样的诗发生关系,就永远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你的自我——如果说你必须拥有一个自我——在更改,你在时空——可感的时空与象征的时空——中的位置在迁移。
诗的变形力的风暴使诗人再也无法拥有任何“安全”。诗人接受这种不安,并动用它来映照整个现代历史的不安,对他来说这几乎是一种逻辑。然而,现代诗的这一特性,不可避免地对它的接受造成影响。当诗把诗人从原处拔离,卷扬着抛出连续性之外时,它同时也就将读者投掷于一种悬疑和运动之中。讨论这个问题的经典文本是曼德尔施塔姆的《论对谈者》,而这篇文章在西方的第一个译者恰恰是策兰。在曼德尔施塔姆看来,诗人之于读者,就像荒岛上落难的人冲着汪洋大海,抛出装着求救信的瓶子,盼望“总会有人”能捡到它;对他来说,这个将救助他的人,既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他的出现一天天地被延迟。我当年在读米肖的诗,受它的触动自己开始创作时,心中所怀的感情,也是这样一种孤独和渴待。
米肖的诗有很强的空间感。在他笔下,空间不仅作为一个主题被说出来,而且作为一种机制在运作着。1954年,他创作了一首散文诗,名叫《属于阴影的空间》。诗比较长,各个段落以碎片的形式存在,絮絮叨叨,仿佛被一只危险而愤怒的手撕裂了。它们组成了一段处处中断的口信,由一个遥远的声音发出,依稀传到倾听着的诗人耳中。讲述者的声音所发出的空间,那个“属于阴影的空间”,是一个我们永远无法进入的别处,在那里只有一些幽魂怨鬼,幢幢而动。这个诡异的空间,被讲述者隐约地描绘出来,它同时也被诗的形式本身,或者说它的造型,通过字句与段落的排列显影于视觉。对于那些游移逃遁的魂灵来说,空间本身是一种威胁,阴沉而又残酷:“空间!可你们无法想象什么是真正的空间:一种可怕的内在与外在。”
《属于阴影的空间》并不是直接在写某一种特殊的历史事实或境况。它的创作灵感,也许既来自刚刚发生在欧洲的历史浩劫,也来自作者个人生活的痛苦经历:他的妻子在1948年惨死于一场事故中。然而今天读这首诗的人,不能不想起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二战中纳粹集中营对犹太人的屠杀。米肖的诗继承了欧洲一个古老的神话传统,即希腊罗马时代史诗中的“降入地狱”和后来基督教对地狱的许多描述,并以一种现代特有的极其暴烈的形式,将其再次表现出来。文学传统在米肖笔下聚合为一个个飘摇的人形:一些威胁着又被威胁的魂灵,在一瞬间一闪而现。
遗忘与记忆
米肖的诗动态地体现出一种丧失:本应自然地支持人的生命的那些东西,忽然被抽走了。同样一种丧失,我多年以后作为研究者接触一类文学作品时,又一次深刻地感觉到。最近二十多年来,我阅读并分析被人们称为“见证文学”的诗、小说和回忆录。这是一种20世纪兴盛起来的文学体裁,指的是那些遭遇过有组织、大规模、毁灭性的政治暴力的人,为记录和思考自己惨痛的经历而写下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地狱”一词也常常被用到,但它们与古代神话已毫无瓜葛,而是指称着现实的、历史的、政治性的暴力形式:战争,集中营,种族灭绝。
见证文学在20世纪产生了众多优秀的作品,无论在德语、法语、俄语和日语中都是如此。讲起这些文学作品来,恐怕3个小时也说不完。我今天只讲一讲雪,这个我们从一开始就接触到的母题。见证文学,特别是前苏联的见证文学,与雪有一种奇妙的不解之缘。1937年,曼德尔施塔姆在沃罗涅日流放地写下一首短诗,对雪做出这样的描绘:“雪把嘁嚓声送给眼睛,/像一块面包那么洁净。”
他当时还写过一首诗,咏雪上薄冰:“一层冰,灰色的面具。”在他看来,无论是谁,只要有一次“独自审视雪地的脸”,就将永远被一种无边无际的荒凉所占据。
曼德尔施塔姆写下这些句子的20年后,另一位苏联作家沙拉莫夫,在撰写《科雷马纪事》的开卷语时,又一次写到雪,并把这篇开卷语——它同时也是一篇美好的散文诗——命名为《雪地中》。
“怎样在雪地上开一条路?”《雪地中》劈空提出这个问题。这篇开卷语长一页,只有两个段落。第一段写一个男人独自在松脆的深雪上艰难前行,身后留下一串不规则的黑色小洞。第二段写5个男人,并排走在雪地上,沿着第一个人踏出的足迹,在那一串黑色小洞两边,用力踩踏着“还没有人走过的雪”。“他们这样走过后,路就开出来了。人、雪橇和拖拉机可以由此通过。”
直到这里,文章的描写是现实主义的,它的场景明显是科雷马的冬天,那几个开路的男人肯定是劳改犯。然而,在文章即将收束时,作者的笔锋却忽地一转,荡出现实主义语境,打开一个隐喻的向度:“第一个人的工作最艰苦。当他精疲力尽时,其他5个人中就有一个赶上来,代替他走在前头。而后面跟着走的人,哪怕是最瘦小、最没有力气的一个,也必须在旁边的雪地上趟出自己的路来,而绝不能把脚步落到别人的足迹中。至于拖拉机和马,它们不属于写作的人,它们属于读者。”这最后一个句子突兀地出现,迫使我们从头把文章再读一遍,寻找它的另一层含义: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开路者,原来就是作者本人;他脚下的洁白的土地,是一页白纸,等待他在上面留下一些“不规则”的黑色痕迹;而其他的踏雪者则是读者,他们沿着作者的痕迹,沿着痕迹指示的方向前进,踩出一些平行的附属的路,并使它们渐渐合而为一。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雪地之白是一种空间的空白,它可以被理解为一道鸿沟,分隔着两个时刻:经历科雷马的时刻和书写科雷马的时刻。这种分隔,作者只能靠他自己孤独的前行来一步步穿越。而在读者,却可以借助别的资料,比如历史研究,对其加以弥合。就像沙拉莫夫带着苦笑所说的那样:拖拉机和马全都属于读者。
“第一个人的工作最艰苦。”穿越漫漫无边的雪地,对沙拉莫夫这样的作家来说,是竭尽全力朝一个过去返回,一个可怕的、惨痛的、许多人希望尽快忘掉的过去。科雷马的经历,难道不就是经历自己如何被寒冷吞噬、被雪沉默地抹去吗?那些漫长的年头,在当时残酷得让人丧失所有记忆:“在科雷马的寒冷中,人连他自己都想不起来。”而到事后,又渐渐被一片白色笼罩,在任何人头脑中都无法形成真正的记忆。
然而,这种无法记忆,是否就是记忆本身?是否就是诗?在雪地上,斯蒂文斯那只精灵一样的猫趁着夜色轻轻走过时,也许可以蓦然看到一个人,也在踟踟行走着,可是步子更沉重,更僵硬,而且好像快要停下来了。
(本文刊出时有删节,全文将刊于《诗与思》第2期)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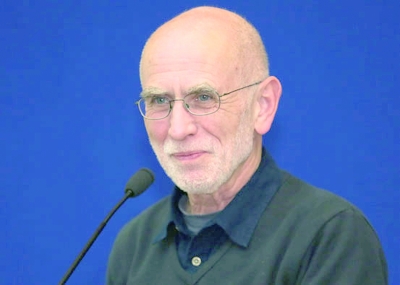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