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策兰和英格褒·巴赫曼于1948年5月在维也纳相识并相爱。然而,维也纳对策兰而言只是一个流亡中转站,作为来自罗马尼亚的犹太难民,他不能留在奥地利,只能去法国,而巴赫曼当时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巴赫曼比策兰小五六岁,生于奥地利的克拉根福特。她父亲曾参加过纳粹军队,这使她长期以来对犹太人有一种负罪感。这就是为什么她会和策兰走到一起,并始终和他站在一起。
在后来的20年里,两人在文学上都获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策兰与巴赫曼,代表着德国战后文学史上的一个时代。
一本具有文学价值的书信集
几年前,德国出版界一个重要事件是巴赫曼、策兰书信集的出版。书信集名为“心的岁月”,出自策兰《科隆,王宫街》一诗,共收入两位诗人自1948年6月至1967年7月,20年间的196封(件)书信,另外还收入了策兰与巴赫曼的男友弗里希的16封相互通信、巴赫曼与策兰妻子吉赛尔的25封相互通信。根据出版惯例,这些书信要到2023年才可以问世,它的提前出版(征得了双方亲属的许可),很快引起了广泛关注。它不仅为一般读者展现了这两位伟大诗人更为隐秘的一面,也为策兰、巴赫曼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就文字的深刻优美而言,其中很多书信本身就是具有高度价值的文学作品。
这些书信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不仅是两位诗人富有戏剧性的爱情、朋友关系和人生、创作历程的记载,也是战后德国文学的重要见证,集中体现了战后西方知识分子最为关注和纠结的历史、政治、道德和文学问题。这一切,正如德文原版的“诗学后记”所言:“巴赫曼与策兰的爱情关系是1945年后的文学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章节。通过这本通信集,可以了解到这两位重要的德语诗人之间的关系及其文学与历史的维度。这是作为奥斯维辛之后的作家写作问题秘密的典型文案。”
一个爱情悲剧故事
对于中国读者,我们不仅从本书中可以了解到这两位德语重要诗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及其“文学与历史的维度”,还会从中反观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自己。换言之,读这部书信集,不仅历史迷雾中的奥斯维辛,还有人类存在的一切,生、爱、死,还有我们自身的历史和现实,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
在这“心的岁月”里,常常是巴赫曼不停地写信,而策兰保持沉默。但他们都从对方吸收了思想、激情和灵感,对彼此的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激励作用。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他们各自的“存在与死亡”深刻相关。当然,这种痛苦、复杂、持续了一生的爱和对话,也带有一种悲剧的性质。对这种“爱之罪”(因为策兰后来在巴黎有了妻子和孩子),策兰自己有诗为证:“嘴唇曾经知道。嘴唇知道。/嘴唇沉默直到结束。”(《翘起的嘴巴》,1957年)
这些书信首先见证了他们的爱。有别于一般的情爱,这个故事中的年轻男主人公向对方奉献的信物是“罂粟花”,这也许是因为从这奇异的花中可以提炼出鸦片,而鸦片是一种麻醉、镇痛物质。幸存者也想忘却历史,因为他们要活下来,不被奥斯维辛的死亡幽灵所纠缠。为巴赫曼的生日,策兰还写下了《花冠》这首名诗:“我们互看,/我们交换黑暗的词,/我们互爱如罂粟与记忆……”(为纪念这种爱,策兰1952年在西德正式出版的诗集就叫《罂粟与记忆》)。
《花冠》深受巴赫曼的喜爱:“我常常在想,《花冠》是你最美的诗,是对一个瞬间的完美再现,那里的一切都将成为大理石,直到永远。”“唉,是的,我爱你,而我那时却从来没有把它说出。我又闻到了那罂粟花,深深地,如此的深,你是如此奇妙地将它变化出来,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为此,巴赫曼渴望去巴黎,“别问我为什么,为了谁,但是,你要在那里等我……带我去塞纳河畔,我们将长久地注视,直到我俩变成一对小鱼,并重新认识对方。”
但是,正如策兰的诗所喻示的那样:“一条弓弦/把它的苦痛张在你们中间”(《里昂,弓箭手》),在他们之间,也充满了阴影和“莫名的障碍”。1957年前后,策兰与巴赫曼旧情重燃,纵然这种爱情的复发给他们带来了最充满激情的时刻(“我证实了你,你证实了我,在一种新的生命里”,巴赫曼致策兰),策兰为此也写下了众多动人的诗篇,但这只能是短暂的爆发,而且会留下痛苦的伤口。
在这之后,这两位诗人仍经常保持着联系,但都已理智多了。他们都意识到他们只能生活在一种致命的“缺席”里(策兰在1963年出版的诗集干脆就叫《无人玫瑰》)。
一部命运的启示录
把策兰和巴赫曼都深深卷入其中的,是持续多年的“戈尔事件”。1960年前后,诗人伊凡·戈尔的遗孀对策兰的“剽窃”指控达到一个高潮。更使策兰难以承受的,是这种诋毁与在西德死灰复燃的反犹浪潮的某种“同步性”。纵然巴赫曼、恩岑斯贝尔格等著名诗人和批评家都曾出来为策兰辩护,德国语言和文学学院、奥地利笔会都反驳这种指控,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以至于策兰很难从中走出——对策兰来说,这完全是“奥斯维辛”之后再一次的“死亡的追猎”!
而巴赫曼,这位看上去坚强、理性的知识女性,实际上如她自己所说,也同样是一个“常常感到沮丧,在各种重负之下濒临崩溃,身上带着这样一个如此孤绝、充满自我解体和疾病的人”。书信集最后的“诗学后记”特意引用了巴赫曼的名诗《延期支付的时间》中嵌入的一句“你不要回头张望”!仅此一句,女诗人将俄耳甫斯神话引入到她自己的生命中。天才的歌手俄耳甫斯未能把自己负罪的爱人带出冥府,他自己最终也“身首异处”,这就是命运!而从神话回到历史,从这个“1945年后”的再版故事中,我们听出的,则是“奥斯维辛”的持久回声——1970年4月20日夜,策兰在巴黎跳塞纳河自尽,巴赫曼随后在自己的长篇小说《玛丽娜》的手稿中添加道:“我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因为他已经在强迫运送的途中淹死,他是我的生命。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的生命。”
在巴赫曼看来,策兰的自杀是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继续。加缪也称策兰之死为“社会谋杀”。他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策兰之死无疑也加深了巴赫曼的痛苦和精神抑郁。1973年5月,巴赫曼到波兰巡回朗诵,特意拜谒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犹太人受难处——她在那里是否想到了策兰?肯定。就在同年9月25晚,巴赫曼死于她自己在罗马寓所的一场突然的火灾,年仅47岁。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它在我们的心中永不结束:
心的时间,梦者
为午夜密码
而站立。
有人在寂静中低语,有人沉默,
有人走着自己的路。
流放与消失
都曾经在家。
你大教堂。
你不可见的大教堂,
你不曾被听到的河流,
你深入在我们之内的钟。
这就是策兰于1957年10月写下的那首名诗。他们曾一起住在科隆王宫街的一家旅馆,该街区在中世纪以来一直为犹太人的居住地和受难地。策兰写出这首诗后,曾从巴黎把它寄给了巴赫曼。
多么好的一首诗!读这部书信集时,我想我们也会不时地为那“午夜密码”而站立的——它会把我们带向对人生之谜、历史之谜的探寻,它会让我们久久地聆听那“深入在我们之内的钟”!(作者为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心的岁月:策兰、巴赫曼书信集》 [德]保罗·策兰 [奥]英格褒·巴赫曼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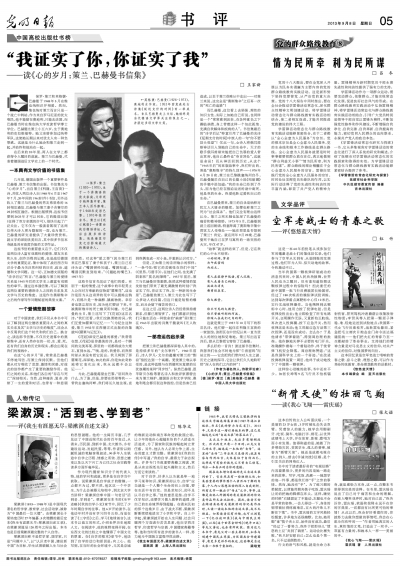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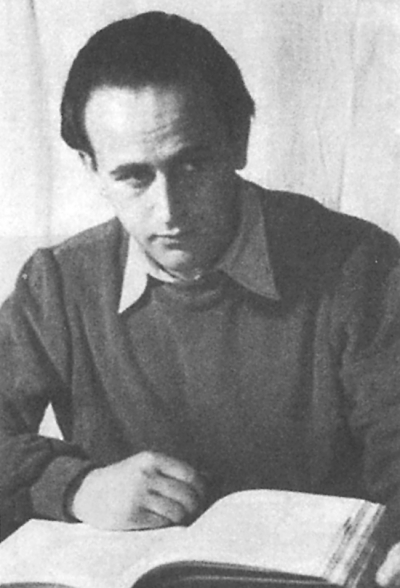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