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蛮北匪
她从来没有去过北京以北,也没有去过南京以南。她在南北交界的小城里生活,古老而狭小的城市布满熟悉的面孔和熟悉的目光,她没有秘密,乖乖地长到了十八岁。她不早恋,也未经叛逆期,她的脾气,就像这座小城一样折中,不南不北,不偏不倚。她按部就班地上学,考学,落榜,工作,记得她的人很少,她记得的人,也不多。
她甚至没有理想,宾馆客房服务员的工作做得泰然安心,每天在客人离开的空房间里收拾散乱的被褥,打扫狼藉的卫生间。她很少与客人照面,除非客人有特殊的要求,比如,加两个枕头,换一双拖鞋。多半,他们只是在她轻敲房门后,开出一条细缝,一条足以伸手接东西的缝。很多时候,她拆下留有余温的床单被套,陌生的体味钻入鼻孔,她想,昨夜,一个男人睡在这张床上,抑或,这条被子里裹着一个女人。偶尔,她闻到被褥里散发出的气味,属于两个躯体,两种性别,甚而,一个北方人,一个南方人。
这种时候,心脏里就会迸出几缕温热的激流,她忽然感觉些微的遗憾,为自己不属于北方,也不属于南方。
她没有机会自由恋爱,聚集在休息室里的客房服务员一律女性,且多半中年上下。有人给她牵线搭桥,她总是平平淡淡地去相亲,平平淡淡地回绝掉。她想,若她是南方妹,就嫁个北匪;若她是北方姐,就嫁个南蛮。问题是,她不南不北,于是,没得男人可嫁了似的,总不能停留于某一个她想象中的胸怀。这么说来,她亦是有理想,小小的梦,关于北方或者南方的梦。
那位说一口纯正普通话的男人住进来的午夜,正是她当班。她困得睡眼惺忪,接到要农夫山泉的电话,房间内的矿泉水不合客人的口味。她道歉,没有农夫山泉,小城里也没有通宵便利店。电话挂上两分钟,再次响起,这一回,要一把切水果的小刀。小刀有,她给他送去。602房间大门敞开,他埋头整理行李,口中朗声喊:请进!
寂静的走廊,寂静的午夜,纯正的普通话朝她扑面而来:真对不起,这么晚打搅您。
他直起身,平常的面容,洁净,轮廓却模糊。他手托一只金黄的菠萝,朝她颠了颠:有盐吗?能不能给我找点盐来?
幸好她有一包当夜宵的方便面,里面有酱包、胡椒包,还有盐包。她把方便面拆开,取出盐包给他送去。他已经把切成片的菠萝浸入温水,白色细盐融进水中,瞬间消失无踪。他抬头道谢,发出了邀请:一分钟就可以吃,请坐吧,尝尝菠萝,它跟着我从西双版纳飞到哈尔滨,又从哈尔滨飞到这里。上帝,中国太大了,大得简直让我失去方向。
她逃一样退出602房间,留下灯火通明的房内他朗朗的笑声。第一次,她闻不出他究竟是北匪,还是南蛮。
第二天,客人退房离开后,她去打扫房间。垃圾桶里堆着依然散发出醉香的菠萝皮,孔雀羽一般的花纹,黄黄绿绿。床头柜上丢着一张布满褶皱的明信片,皑皑雾凇挂满树枝的丛林,雪原深处,还是雪。她无法自控不去读明信片上的手书,两行娟秀的字迹:踏遍曾经共同的足迹,没有你的踪影。落款,宁。
那个叫“宁”的女子,早已挽回不了他。他从南方飞往北方,又从北方飞到中原,他把她丢在旅店里,轻薄如一张纸片。拆下他睡过的床单和被套时,她用力嗅吸着某种似是而非的气味,菠萝,烟蒂,以及男人的汗酸……热流悄悄涌入她的眼睛,仿佛,被丢弃的女子,就是她。
休年假时,她去了一趟哈尔滨,又去了一趟西双版纳,有生以来第一次,她坐了飞机。她想,她若是那个叫“宁”的女子,会想念一个不像北匪,也不像南蛮的男人吗?
她终于去过了北京以北,南京以南,便不再觉着遗憾。
她嫁了人,小城里的中学教师,土生土长,朴实,甚至木讷,与她的单纯一百个般配。
她依然是不南不北、不偏不倚的小城人,这一点,任谁也无法改变。
老八样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厌倦了在家里过除夕。这是一年中最繁忙、最嘈杂的一天,她总是借故赶稿子而躲避着厨房。她身上穿着父亲的大棉袄,脚上拖着母亲的老棉鞋,像一只慵懒的家猫一样身陷沙发的怀抱。她的面前,小小的折叠桌上立着超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开着一页空白的文档,上面还没有留下只字片言。
空调嗡嗡驱赶着寒冷,玻璃窗阻隔了正逐渐入侵的暮色,遥远的爆竹声渐次密集起来,“椰岛鹿龟酒”金红闪光的广告在央视春晚开始前试图夺人眼目。人们让喧闹留有余地,是为零点以后新年的莅临表示更为热烈的欢迎。一切都在拥挤着来临,旧年只剩下最后一日,“旧”,一和日的左右结构,将成为一段打上句号的往昔。
妈妈往花瓶里插入一束银柳,然后抓起一块抹布擦着早已亮闪闪的电视柜,一边唠叨:要在零点之前扔掉垃圾,在零点之前冲好抽水马桶,在零点之前洗完脏衣服……大年初一,不可以做一切与“扫除”有关的事。
父亲正在准备年夜饭,忙碌的身影不时从厨房进入客厅,又从客厅进入厨房。进出间,熏鱼和酱鸭的香味飘逸而来,油锅正发出“哔哔啵啵”和“哩哩啦啦”的哼唱。老八样,还是老八样,他三十年如一日地为除夕的餐桌奉上最古老的八道菜。她给他买过一本《时尚家庭菜谱》,他只粗略地翻了一遍彩页,并且对华而不实的菜式表示了他嗤之以鼻的不屑。他排斥“时尚”或者“流行”这样的字眼,他认为,那是“浮躁”和“骗术”的代名词。他并未意识到他的过时,一如既往地操作着古老的年夜饭,并且永远保持着三十年前的热情。他看着自己做出来的一大碗一大碗的菜肴,脸上流溢出满足的表情。他好像从不知道,她早就吃腻了“老八样”。整个春节期间,他把那八道菜端出端进,从除夕一直端到正月十五。
这是她记忆中千篇一律的春节,她过够了。于是今年,她准备出逃,自然是有人领着她逃。她只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有一双大手牵着她的小手,长了翅膀一样,远走高飞了。去海南的机票竟不打折,原来那么多人和她一样,厌烦了在家里过年。满员的经济舱里空气浑浊,却浑浊得让她心安理得。
深冬的海南没有一丝深冬的气象,绿意葱茏的热带植物染绿了她的眼睛,碧蓝的大海边,暖风飞扬起她单薄的衣衫,赤裸的脚趾里灌满了温暖的细沙……没有人忙于过年,没有人惦记着插银柳、大扫除、做年夜饭、放鞭炮,没有人记得,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个日子叫除夕。直到午夜,手机忽然发出一记布谷鸟的呼唤,是短信。白天的疯玩让她疲惫不堪,她打开昏昏欲睡的眼皮看短信:阿囡,新年到啦,爸爸妈妈祝你快乐,进步!
新年到了吗?她以为她在梦中,梦中的新年如何是一盏昏暗寂寞的床头灯?怎么是一床除了白色还是白色的被褥枕头?怎么是一间没有飘逸出熏鱼酱鸭香味的标准房?她终于清醒地意识到,她逃离到了一个不需要过除夕的地方,可新年还是马不停蹄地来临了。
她推了推熟睡的人:新年好!
熟睡的人发出梦中的呢喃,好!继续熟睡。
她发了一会儿呆,然后,感觉有点饿,她听到胃壁在暗暗地较劲,发出微弱的研磨声,身体内的生物钟醒了,她终于惦念起了某些食物,那些应该出现在除夕餐桌上的三十年不变的食物。她便问熟睡的人:现在,你最想吃什么?
熟睡的人没有回答她,她便自问自答:第一想吃八宝饭,第二想吃白斩鸡,第三油爆虾,第四咸肉炖笋干,第五熏鱼,第六酱鸭,第七扣三丝……她掰着手指头数了一遍,才七个,还有一个,对了,还有一个,肉圆蛋饺三鲜锅。
她简直胃口大开,她几乎要吃成一个大胖子了,她第一次用想象和回忆,品尝出了老八样的美味。美味的老八样,让她忽然有些想念她厌倦了的家。
她忍不住又推了推依然熟睡的他:明天,我们还是回上海吧,我想吃我爸做的老八样。
薛舒 “70后”女作家。作品多次被转载或入选年度精粹。现居上海。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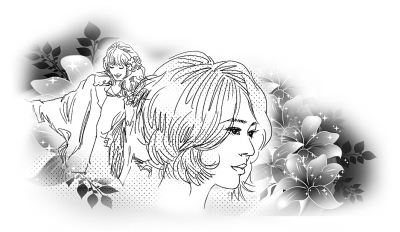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