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说他素不解棋,只是喜好看别人对弈,在一旁安坐竟日不以为厌。偶而步入黑白世界,全不在意胜负,“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作家徐怀中也是如此,看高段位的国手们在电视大棋盘旁边讲棋,不到节目结束不离开座位。
围棋有“打谱”一说,对照棋谱,把前人的名局一着着摆下来,捕捉盘面上此消彼长的每一个玄机,以触发自己的灵感。或者可以说,长篇非虚构文学《底色》是徐怀中为越战“打谱”,是他对于“越南流”所作的独特注脚。“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战争与围棋同理同义。不仅围棋,中国的琴棋书画,都是“观夫天地万象之端而为之”,含有东方古老文化深厚的底蕴,透着人生智慧哲理的光辉。而徐怀中说,他虽然在《底色》中多处以棋理评点战争风云,仿佛深谙此道,其实只不过是借用了围棋的一点皮毛而已。
1966年初,徐怀中作为“中国作家记者组”组长,率组从金边秘密进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总部,自1965年冬至次年春,经历了四个多月战地采访,多次近距离领教过美军B-52战略轰炸机“地毯式”轰炸。少年时代,徐怀中曾经在太行山经历了日军的“二月大扫荡”,接着又是“五月大扫荡”,日军连续实施铁壁合围和篦梳式清剿。没想到20年多年后,徐怀中又同越南南方军民一起,见识了美军陆、海、空立体化的“一月大扫荡”……
对战争的亲历未见得就可以转化为文学作品,但是徐怀中做到了。他曾经写出《西线轶事》《阮氏丁香》等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品,《西线轶事》以九万余读者直接票选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被誉为“启蒙了整个军旅文学的春天”,无愧于“当代战争小说的换代之作”的美誉。48年之后,他根据当年的“战地日记”完成了长篇非虚构作品《底色》(人民文学出版社),真实记录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位中国军人作家、记者,在战火纷飞中的种种情感阅历与生命体验,记录了他对战争冷静客观而富于哲理的观察思考。因为有“抗美援越”以及1979年“对越还击”两次参战经历的“换位”经历,加之拉开了近半个世纪的时空距离,他获得的是在以往战争中从未有过的深思明悟。
写作《西线轶事》,徐怀中并没有过多描绘那场战争的“树冠”,而是着力于地面以下的“根须”部分。
作为一位军旅作家,只有争取到最前线去经受种种考验,积累丰富的战场体验,才可能进入文学写作的殿堂。以往每次去前线,徐怀中像小孩子过新年穿新衣,满怀激情跃跃欲试。但奔赴“对越还击作战”前线,以及写作《西线轶事》,他的心态要复杂得多、沉重得多。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徐怀中提及当年写到某些人物和生活细节时,仍禁不住潸然泪下。
突然接到电话通知,领导决定让他参加战地采访小组赶赴云南前线。那时,他刚刚大病初愈,身体非常虚弱,一度出现休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是提着几大包中药丸子上的飞机,看上去完全不在状态。1979年2月17日“对越还击战”打响,3月16日战争结束,部队采用“倒卷帘”(即交替掩护)战术撤回国,徐怀中又随着作战部队到四川乐山访问某师通信连女子电话班。在连队写出了小说《西线轶事》的一部分,他读给女电话兵们听,征求她们的意见和建议,姑娘们谁都不说话,一个个低下头在笑个不停。那笑声含有女孩子的羞怯与抑制不住的欢乐,显然她们给予了完全认可。
初稿为中篇,6万多字,徐怀中是把中越两方面人物交叉在一起写的。那时《人民文学》只登载短篇,编辑建议把描写我方人物故事的章节抽出,紧缩为不超过3万字的短篇。从初稿中抽出的描写越方的另一部分文字,经作者重新整理,拟题为《阮氏丁香》,作为《西线轶事》的姊妹篇,发表在《十月》杂志。这一来,倒形成了一种鲜明的效果,对比之下,能够清晰地看出中越两国是在怎样一种特定社会背景下投入这场战争的:中国刚刚从十年动乱的梦魇中挣扎出来,是最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越南则是连绵二、三十年遍地烽火刚刚熄灭,未及疗治创伤。两个社会主义邻国鸡犬相闻,他们的战士却用对方的语言彼此大叫“缴枪不杀”。
文革刚刚结束,思想解放运动随之潮涌般到来,《西线轶事》的写作,实际上是十年浩劫后在心中积郁已久的沉思愤懑,以那场边界战争为井口喷发而出。如果将战争比作一株大树的树冠,引发战争的社会原因就是深扎在泥土中大树的根须。徐怀中并没有过多描绘那场战争的树冠,而是着力于地面以下的根须部分。作者写到,“文革”中有关部门竟发出通知,征集新的国歌歌词,随即他发现周围的一些词作者兴高采烈地投入创作;徐怀中觉得又可笑又可气:国歌是可以随便修改的吗?虽然聂耳、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是电影插曲,却正像是预先为新中国准备好的一首国歌。建国多年,徐怀中仍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所谓“文革”,即是中国害的一场政治天花,但上帝没把免疫性给予我们。一个国家混乱、落后、贫困,是要挨打的,我们再经受不起了。
徐怀中谦虚地说,“不是《西线轶事》《阮化丁香》写得多么好,也并非自视颇高,但这两篇战争题材小说,包括刊载于1966年3月3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一篇通讯——《坚贞不屈的女英雄阮氏珠》,我都十分珍视,诚可谓敝帚自珍。”他说,这篇通讯拿给现在的年轻读者,他们会感觉枯燥无味,难以下咽。但通讯被译为越语,在战火纷飞的南方丛林中广为传播,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总部以及各地军民,每天傍晚准时集体收听连续广播。这令徐怀中感动不已。作为一名战地记者,还要什么?这两次战争,他都是亲历者,自然会在感情上产生某种特殊联系。他总是自作多情地想:我的这些文字,是为在战争中失去生命者和苟活至今的人,保留下来的他们彼此相通的一线信息。
对作者而言,在越南南方的一段生活经历,是“一页翻不过去的历史”。
一次搬家时,偶然找到了近40年前在越南南方作战地采访时的两个日记本,这使徐怀中获得意外的惊喜。翻阅旧时日记,他似乎可以伸手触及时空纵深,俯拾流云逝水。从越南南方最高军事指挥员阮志清大将、越南的“圣女贞德”女副司令员阮氏定,到普通士兵,以及城市武装的女“交通员”们,徐怀中在他的塑料封面小本上记录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人物,记录下战地生活中那些平平常常又颇有声色的逸闻趣事,也描述了炸沉美军“卡德号”航母之役、布林克饭店之战、公理桥伏击失败之憾等重大事件……
徐怀中决定放下其它创作,先着手写一部长篇非虚构文学《底色》。若以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为顺序,这一部新作《底色》在前,本应该列为“上集”,《西线轶事》《阮氏丁香》在后,本应作为“下集”。也就是说,在推延了三、四十年之后,作者才来补写了“上集”。
上世纪下半叶,以意识形态为分野,世界进入了一个两极对峙的“冷战”冰河期,越南战争便是在“冷战”格局中的一场局部“热战”。越南这片焦土上撒播的是中、美、苏彼此牵制激烈竞逐的火种,这个“等边大三角”内部的一垄一畦间,又生发出了中、苏、越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的“小三角”;就像玉米地里常常套种豆角,高梁地里往往套种倭瓜。比之“大三角”,中、苏、越“小三角”错综复杂的“内部游戏”则是更尖锐、更复杂、更激化。
“中国作家记者组”是在中苏论战高潮时出去的,大家学习了“九评”,用“防修反修”理论武装到了牙齿,随时准备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但实际上当时尚不能很清晰地观察那场战争和国际关系。在写作《底色》的前后,徐怀中阅读了国内外大量关于冷战史研究的文章以及有关解密档案,受到启发,才真正认识到当年这场战争是怎样的多变诡异。
正是在抗美援越激战犹酣之时,基辛格秘密从南苑机场进入了钓鱼台国宾馆,“小球转动大球”的进程开始了。中美历来是针尖对麦芒,情势急转直下之际倒启动了建交谈判,“栽刺栽刺栽出了一朵花”。徐怀中说,除了“菊香书屋”的主人外,没有人想得出这一步棋,就是想到了,也未必就敢主动提出来。越南被挤在几大国的夹缝里,自会施展他们的生存哲学和外交智巧,虽是谦恭低调,却也时时期待着国际战略上的超常发挥。“我不能就此得出‘春秋无义战’的结论,但套种在冷战中的这场热战,决不是以正义或非正义战争这种简单逻辑解释得清楚的。”
《底色》的写法,融小说、散文、通讯、政论于一体,同时又显示出作家长期的知识储备、文化修养和战争思考的底蕴。他确定要用非虚构形式出现,做到观察高度真实、客观、公正,强调作者的亲历性,作为自己戎马半生的一行足印;同时又希望在宏观展现上更开阔,揭示复杂多变的冷战国际格局,既有一条时间顺序的线索,又力争突破呆板的回忆,尽可能适应叙事的需要。现在看来,基本上达到了预期效果,但徐怀中也坦言尚有不足:“还应该写得更活脱灵动一些。有关冷战与大国关系的议论部分还应该更加鲜明犀利,进一步强化思辨意义。”
一部战争史往往讲不清楚,究竟是因为什么,两国之间或是多国之间竟至于妄动干戈。天下兴亡系于一身的最高决策者们,不论多么伟大英明,也不免在这里留下败笔。
在越南南方的四个多月,给徐怀中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记忆。在他看来,越战和抗日战争及抗美援朝有根本的不同。现在到处都在讲“非对称性战争”,一个陌生的军事学术语。其实,越南南方抗击美国大举入侵不就是典型的“非对称性战争”吗?交战双方军力以及支援能力差距之大根本不成比例,使得这个差距已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说明问题的是什么呢?是越南人的加重脚踏车,是绑在车座和车把上的两根木棒棒。直到越战结束,美国的补给物资还在海港码头堆放如山,而越南人多是靠光着脚丫子推着脚踏车驮运大米,来支撑这一场战争。
徐怀中在《底色》后记中写到,1979年中越两国兵戎相见,这一页历史插曲过于沉重,道理上可以讲得清楚,但从感情上翻过去这一页绝不是那么容易。在战争生活中,徐怀中不仅看到毁灭和绝望,也看到无限希望和光明,看到永不泯灭的人性光辉。他到南线收容所访问越南女俘,炮火停息没几天,越南女孩子已经在向中方小卫生员递纸条了:“我觉得你的性格特别好,你可以写纸条给我吗?”她全然忘记了不久前她们如何争先恐后报名参加青年冲锋队,誓与“北寇”战斗到底。
一部战争史,往往讲不清楚究竟是因为什么,两国之间或是多国之间竟至于妄动干戈。天下兴亡系于一身的最高决策者们,不论多么伟大英明,也不免在这里留下败笔。所幸的是,人们世世代代经历多了,也便懂得了抛却仇恨,越过种种有形无形的警戒线走到一起来,彼此给予同情,给予友善,给予援助。而那个越南女俘,更是不顾一切,把寄托着她无限遐想的一张小纸条递过去了。她是何等痴心,不受任何观念的束缚与驱使,仅凭一缕倾慕之情,就足以抵消国家战争动员令。人的纯粹感情属于天性,不是任何战争力量所能阻挡所能改变得了的。
作为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战争文学作家,徐怀中从未停止对战争的反思,也未停止对自己思想感情的反思,他甚至说自己仍没有真正感知在越南南方土地上进行的那一场旷日持久而又极端残酷的战争。
澳大利亚记者贝却迪在越南待了十多年,以第一手新闻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加拿大广播公司驻远东记者迈克尔·麦克利尔也在越南待了十年,写下了《越战10000天》。这些战地记者的职业精神对徐怀中有很大的触动,他发自内心地感到钦佩。“我们与西方记者不同,我们只能集中时间做战地采访。他们是从始至终跟踪越战,追求历史观察,着重从战争各方领导层的决策谋篇加以宏观把握,对态势发展有透彻的了解,这是我们做不到的。”美国记者在前线以身殉职的就有135名,多数是摄影记者。全世界战地摄影家,国籍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到头来却总是不可避免地相聚在同一个陌生的“故乡”。
在徐怀中他们之前,有“中国新闻工作团”一行九人经胡志明小道,行军九个月才到达南方。徐怀中出访的时候,我方已经和金边打通了关系,徐怀中之行已不必由河内南下走胡志明小道,而是直接从金边潜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总部。正因为对胡志明小道没有亲历生活,感同身受欠着一层,导致了他顺水推舟的描写,说什么在战争后期,“胡志明小道上的女志愿者们,已经悄无声息地度过了青春期,发育成熟,成为健壮俊美的南方妇女了。”而事实上,在极端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女志愿者们身体受尽摧残,不可挽回。“胡志明小道”作为一个无法仿制的战争品牌保留了下来,而留给十多万女志愿者的只能是无尽的苦难和悲惨。
好在《底色》初稿中这段文字得到及时改正,但徐怀中一直感到很愧疚。他坦言:“我不能不承认,自己并没有真正感知这一场战争,并没有真正感知越南南方。作为一名战地记者,我缺少内心情感的充分投入,我太麻木,太冷漠,我太轻松愉快了。”又说:“根本上讲,还是有做客思想,毕竟战争是在人家国土上打,真情投入不能与越方人员相比。我回敬人家的是低度酒,兑了水的。”老作家的自我反思令人感动。
以《底色》为书名,是徐怀中的一声呼喊,是他对于这个世界发出的一个独特的“警告”。
美军驻越司令、四星上将威廉·威斯特摩兰曾说,在“越共”高级将领中,“阮志清是唯一具有第一手知识的人,只有他懂得,面对美国火力进行常规战争是多么大的不幸。”正因为阮志清痛切意识到了美军的火力超常强大,他打定主意,迫使对方不得不分散兵力,疲于奔命。“逼美国人用筷子吃饭”,阮志清大将的言语通俗化、生活化,充满军事辩证法。最基本、最高的作战原则,被他一语道破:趋利避害,把握主动。远起冷兵器时代,及至现代战争条件下,这个原则始终为兵家之圭臬。
“中国作家记者组”南方之行分量最重的一项安排,就是采访最高军事指挥员阮志清大将。在徐怀中的印象中,阮志清就像一团火,极端热情,两眼穿透力很强,好像能洞悉人的一切。阮志清被认为是越南劳动党上层的一个“亲华派”,他口无遮拦,讲了一大段完全是同情中国的话,令徐怀中非常吃惊。访问没有做记录,机密性太高,徐怀中害怕丢失,后来他凭记忆写出阮志清的原话,再三跟同去越南的战友核对,以求准确。
战争,无论规模大小或时间长短,也无论内战还是对外战争,无论是最神圣的保卫战争还是最不韪的非正义之战,最终都是以人的个体生命来结算的。在《底色》中,徐怀中以凝重与激越的笔触记述了阮志清之死。这位大将并非如河内讣告中所称死于突发心脏病,而是同众多“越共”官兵一样,也是在B-52轰炸机的机翼之下定格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一位将帅,无论你怎样大智大勇,怎样久经历练沉稳老到,也无论你建立了怎样的丰功伟绩,在某种必要情况下,个人所能采取的最后一个动作,和所有参战士兵们一样,那便是交出自己活扑棱棱的一条性命。”
徐怀中对战地摄影大师卡帕怀有深深的敬意。卡帕的作品被誉为“战地摄影不朽之作”,他总是擅于捕捉战争中稍纵即逝的动感形象,将人在生死交替的一瞬间定格为永恒。徐怀中说,卡帕以他无声的语言塑造了一系列人的生命雕塑,他的镜头纵深无限,他摄取到的是人类战争的“底色”。
所以徐怀中决定,自己的新作就以《底色》为书名。战争是人类历史的永动机,无论以何种名义发动这一部机器,它的“底色”不会有任何区别,那就是死亡,是毁灭,是残酷,是绝望。卡帕本人也没有逃出战地摄影者的宿命,他正是在越南战地触雷身亡的。他原希望出现在他镜头下的种种惨剧有一天能够停止上演,看来卡帕的一番苦心恐怕也只能是付诸东流。正如卡帕的挚友唐·麦库里所说:“我不再生活在幻影中,人类只能一直遭受苦难,直到时间尽头。”
采访的最后,我问徐怀中,能否评价一下自己在创作上的理想和遗憾。他说,翻查自己的文学流水账,其中写满了遗憾和沮丧。由于种种原因,荒废了很多时间,加之有写作习惯上的弊病,总是要把一段段文字背诵下来,才能落笔到纸上,这就决定了他的“爬行姿态”,写不了几篇东西。他说,“我读过这样一段箴言:‘一个被揉皱的纸团儿,浸泡在清水中,渐渐平展开来,直到恢复为一张洁白的纸。人的一生一世,也应作如是观。’现在对我而言,时间很有限了,但我还是会在文学写作这一汩清澈的泉水中浸泡下去,直至重新平复为一张白纸。”(本报记者 舒晋瑜)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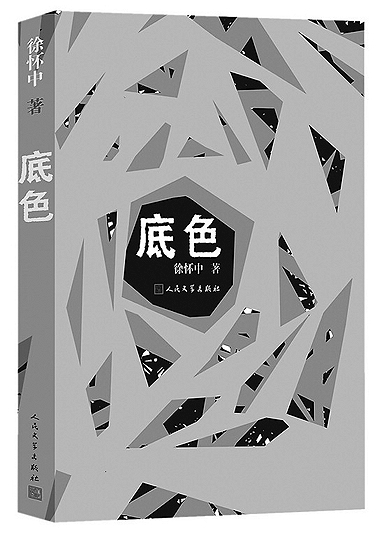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