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1889—1978年)不仅是19世纪以来瑞典最杰出的学者,也是西方世界最优秀的汉学家。高本汉以毕生精力研治中国文化,尤其致力于汉语音韵训话的探究。他花费数十年时间,根据古代韵书、韵图和现代汉语方言,以及日本、越南、朝鲜诸国语言中汉语借词的译音,重新构拟了以唐代长安方言为基础的中古汉语语音系统。他的科学方法和思想观念对同时代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根据马悦然的考证,高本汉于1910年2月来到中国,先后在北京、太原等地学习两年。他操着当地口音,穿着中国普通读书人的服装,带著仆人和一匹马,访问了北京和太原周围的大部分村镇。他不仅搜集各种方言资料,还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报道寄回瑞典,发表在《每日新闻》上。这可能是瑞典报纸最早的关于中国社会状况和人民生活的直接报道。在这两年当中,高本汉为音韵学研究的课题搜集了24种方言材料(后来增加到33种),这为他后来从事音韵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5年初,高本汉回到瑞典,在母校乌普萨拉大学准备他的毕业论文。5月20日,他被授予硕士学位。次日,又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中国音韵学研究》成为重新构拟中古汉语语音系统的奠基之作,被汉学界公认为19世纪科学研究汉语语音的第一部宏伟著作。
1812年,清代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段玉裁在《答江晋三论韵书》中问江有诰:“能确知所以支脂之分为三之本源乎……仆老耄,倘得闻而死,岂非大幸也。”然而精于审音的江有诰未能回答段玉裁的问题。在缺乏语音学知识和方言学知识的背景下,汉语音韵学在清儒手里达到顶峰之后,走进了困境。20世纪初,章太炎发表《国故论衡·二十三部音准》,虽然讨论了古音的音值,由于没有音标的辅助,仍然没有讲清楚。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中国的古音学研究一直在考据的范围内“前修未密,后出转精”,难以跳出这个困境。正如王力所说,“只有运用西方语言学的重建方法,才能把古音构拟出来。”而西方语言学的重建方法正是伴随着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进入中国的。
《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共4卷,898页。其中1-388页为博士论文。第一卷(1-316页)1915年出版;第二卷(317-468页)1916年出版;第三卷(469-700页)1919年出版;第四卷(701-898页)1926年出版。这一考证与法文单行本第一版(即Archives D’etudes Orientales Vol.15)、中译本《中国音韵学研究》、法文北京刊行版、周斌武(1987)所表述的各卷发表时间均一致。
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原为法文版。它由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翻译成中文于1940年在上海出版后,才为广大中国学者所了解和接受。不过在此之前,已经有多位学者翻译、介绍、讲解、讨论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了。
1941年魏建功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一部影响现代中国语文学的著作的译本读后记》中说,他很早就从钱玄同先生那里知道了高本汉的著作及其主要内容。“钱玄同先生讲音韵学,可算是最先用语言学的理论的一个人。按照魏建功先生的回忆,1919年,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法文版前三卷出版完毕,随即送了一部给钱玄同先生。钱先生从原书里把高氏的《广韵》韵类构拟的音值抽录出来和国音系统一同亲自手写油印,在北京大学讲,自然又加了他自己的意见讨论过一番。”1923年7月,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刊登徐炳昶的译文《对于“死”“时”“主”“书”诸字母内韵母之研究》,就是由钱玄同先生决定选译的。从徐炳昶的经历与时间来看,很可能徐炳昶在法国留学期间就读到了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
1923年,林语堂在《〈答马斯贝啰论切韵之音〉跋》中说,“我两年前读此书(即高氏《中国音韵学研究》),于许多点上大起疑惑,现在见此篇原著,知道珂君(珂罗倔伦,Bernhard·Karlgren的另一中文译名,下同。)于所有构定可疑之处多已改良,不禁为此而喜。因为照现在情形,很可以做到专家同意的境地。此篇实是珂君著述中的重要者。”从林语堂的话中我们可知,他在1921年就读到了高氏的著作。1921至1923之间,高本汉对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进行过修订。这恰在马伯乐于1920年发表《唐代长安方言》一文之后。高本汉采纳了马伯乐的部分意见,将《中国音韵学研究》修订后印成单行本,1926年出版。这修订应该就是高本汉于1922年在《通报》上发表的《中古汉语的构拟》,即林语堂翻译的《答马斯贝啰论切韵之音》。
钱玄同先生不但在他开设的音韵学课上讲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还根据高本汉的研究将《广韵》的韵类和所构拟的音值列成一表,把高氏所用音标改为国际音标。这张表何时所定,不可考。1957年赵荫棠将它附在其名著《等韵源流》第334页。其实在北京大学课堂上讲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不仅有钱玄同先生。罗常培先生在中译本《中国音韵学研究》出版前,也曾在北京大学课堂上讲过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第三卷“历史之部”。此外,赵元任先生于1925年在清华国学院开设的《中国音韵学》中,也曾讲授过高氏的学说。
作为《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文版的主要译者,赵元任与高本汉并不相识。他手中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来自地理学家丁文江。丁先生的朋友安特生与高本汉颇有交谊,安特生送了一部《中国音韵学研究》给丁文江,丁则转送了赵先生。这件事后来被胡适、傅斯年两先生知道了。于是,在胡、傅二位的鼓励和支持下,三位译者开始了这项译介工程。
在1940年之前,中国学术界译介高本汉著作的文章和书籍多达50种,与《中国音韵学研究》直接有关的有9种。中译本《中国音韵学研究》出版后的六年间,仅书评(包括读后记)就有5篇:魏建功(1941)《中国音韵学研究——一部影响现代中国语文学的著作的译本读后记》,重庆《图书月刊》第1卷6期;高华年(1941)《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校读记》,重庆《图书月刊》第1卷7-8期;罗常培(1941)《介绍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重庆《图书月刊》第1卷7-8期;周法高(1942)《图书评介:读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读书通讯》第53期;陆志韦(1946)《书评:〈中国音韵学研究〉(高本汉著,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民国二十九年商务出版)》。由此足见当时中国学术界对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关注度。
1957年音韵学家赵荫棠说过这样一段话:
等韵图的编制,至劳乃宣已走到穷途;宋元等韵的解释,至黄季刚亦陷入绝境。设若没有新的血液灌输进来,恐怕我们中国的音韵学永永远远停留在株守和妄作的阶段里。幸而我们借着创制注音符号与国语罗马字的机会,激起来新的趣味,于是近代语音学的知识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以及国际音标的好工具,都从美欧介绍到我们中国。这种介绍,自然对于中国音韵全体都有大的帮助,而等韵学的研究亦因此而开辟新的纪元。在音韵学的新运动之下,有新的贡献的,是赵元任,钱玄同,林语堂,李方桂,黎劭西,刘半农,高承元,魏建功,罗莘田诸位先生。他们或介绍,或发明,或补苴,共成音韵学的新园地。所以我们现在叙述起来,很难确定他们各人学说的来源和相互的影响的脉络。但是,我们从何处叙起呢?我们现在只能以高本汉(B.Karlgren)所研究中国音韵学的结果为起点,然后叙述国内各家之补充与修正。
赵荫棠先生的话不仅道出了20世纪初高本汉学说引入中国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而且道出了高本汉学说之所以能在中国被接受的重要推力。由此,中国音韵学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范式——高本汉范式。
毫无疑问,高本汉范式就是对汉语语音系统的重新构拟,这是高氏学术工作的中心内容。他一改中国音韵学家借反切方法照韵图考证古音的做法,改用注音字母,与反切系统所划分的韵类相互检测,同时从现代方言和外国语言借音中查核古音足迹。因为现代各种方言都是从古汉语语音演变分化而来的,通过对现代方言的比较研究,可以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有助于重新构拟古汉语语音系统。此外,中古时期,中国人受印度人拼音学理的影响,把那时的字排成许多音韵表 ,这些图表对古音的研究参考价值极大。后来,中国人和中亚及西亚诸民族交往,外国人用译音把汉语中的名称记录下来,中国人也以汉语语音直译部分外国的名称,这些译音对古汉语语音的考证有着宝贵的启示作用。特别是汉语输入到日本、高丽(朝鲜)和安南(越南)都被这些国家的人以拼音记录下来,成为今天人们考定古音的宝贵材料。高氏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主要部分就是采用考证古音在不同方言中语音演变的方法写成的。高氏以西方学者的身份,在本世纪初对于如此复杂的中国方言和古代音韵开始进行科学的研究,确实是筚路蓝缕 ,功不可没。罗常培曾评价:“这部书不但在外国人研究中国音韵学的论著里是一部集大成的工作,就是在我们自己所作的音韵学通论中也算是一部空前的伟著……”。
除在汉语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高氏的研究领域还涉及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美术和宗教方面,可以说,高氏不但对中国文化学术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对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的相互影响具有特殊的意义。特别是他的科学方法和学术态度,为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的研究开拓了一条新路,深深影响了一代国人。同样在历史语言学研究领域,许多国学大师如赵元任、胡适、刘复、白涤洲、周祖漠等都在各自的专业范围内做出了创造性贡献。他们的共同努力,奠定了现代中国文化学术研究的基础。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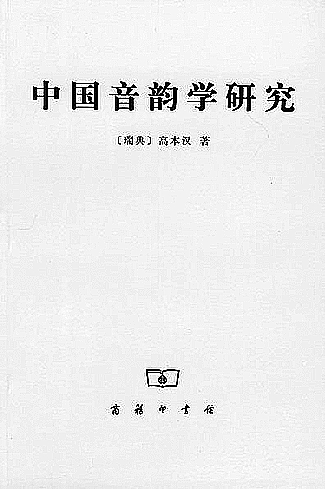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