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实在,何为诗歌?《论语》中有两个例子。
“实在”的例子是《论语·子罕》: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说出这样的“欲居九夷”的话,显然是孔子在中原华夏有些失落,于是想起老子出关“化胡”,也想模仿。当然,孔子不是老子,他坚守“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不会真的离开,这不过是一句兼有感慨、牢骚的叹息罢了——用想象中的逃离,来让自己的精神暂时从沉重的现实中脱逸一下。所以,孔子此时的“欲居九夷”,只是叹息,而当不得真。从叹息的角度说,与诗意已只有一步之遥;但从当不得真的角度说,这毕竟还不是诗,只是有了诗的趋向。
但是,旁听者中出现了一个当真的人。他改变了孔子此时的诗意化趋向:他问孔子:“陋,如之何?”
一句话就让孔子从近乎诗意化的情绪中回过神来,恢复了理性,他傲然答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住到那里,教化那里的人。那里的人教化好了,也就自然不落后了。
此时的孔子,心理上进行的,是理性活动。实际上,当孔子说“欲居九夷”时,他就是介于浪漫和理性之间——虽然想逃避现实,但九夷毕竟是可居的,是可以“移民”的,或者说,这可以是一个人生的“愿景“或“计划”,并且是在现实中可以实现的。所以,我前面说,此时孔子的情绪,与诗意只有一步之遥,但,毕竟还有一步之遥——他还踏足在现实之境。
下面这一则,则一开始孔子就跨出了现实的土壤,直接站立在诗歌之境: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
“道不行”,这也还是感概,虽怅触万端,却不离现实。但下面接着的,就不再是“欲居九夷”这样的“计划”,而是“乘桴浮于海”这样毫无现实感的浪漫“想象”,是天风浩浩烟波渺渺的超现实之境。他没说道不行,我悲观绝望,找一个什么地方解闷去——这样说,就“实在”了。不。此刻,他看到的,是海,是那烟波浩荡、气象万千的大海,此时,他心灵中,完全不是人生的规划,而是精神的飞升。
大海辽阔,神秘,暗示着宇宙无限可能的空间和人类精神无限可能的境界。为什么孔子就能想到海呢?圣人的心胸,对于我们,也是大海,也是一个谜。人与人的心胸是不一样的,人与人的智力是不一样的,人与人的情怀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总能和一种大而深的境界对接起来,有的人,永远只局限于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肤浅空间。
说“乘桴浮于海”完全没有现实感,不光是“海”之不可居,还有“桴”之不可乘。假如孔子说:我要乘坐游轮去大海,他就只是陈述一个可能的“事实”,一个现实的“愿望”或“计划”,而仍然没有诗意。诗意是对现实的超越——我们知道,孔子也知道,一个小木筏子是不能航行于大海之上的,但是,唯其如此,唯其如此“不现实”,才与现实拉开距离,大海之大,木筏之微,满眼烟波之中,人如沧海一粟,世界之苍茫衬托心灵之孤独,形体之细微凸显精神之傲岸,这才是诗意,才是境界!
思维太拘泥太实用的人,很难理解诗歌。理解诗歌,需要智力和情怀的双重优越。
说“乘桴浮于海”完全没有现实感,除了“海”之不可居,“桴”之不可乘,还有一点尤其重要:这样的不现实的航行,其实还是完全没有目的的。“欲居九夷”是有目的的,无论是消极的逃避还是积极的“化胡”,都是目的。而“乘桴浮于海”是没有目的的,它其实只是一种想象中的航行,精神的航行,心灵的航行,是精神的脱逸,而不是身体的位移。
美是什么?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诗是什么?诗是不现实的现实性。
诗歌并不远离现实。它与现实的关系,不即不离——即了,不是诗,离了,也不是诗。我们还是跟着孔子来理解诗歌吧:辽阔的大海之上,一个小木筏,两个彷徨人,烟波满眼,飘摇沉浮,天遥遥,水淼淼,不知去何处,也不要去何处——这不是生活中的“现实”情景,却又是生活的本质写照!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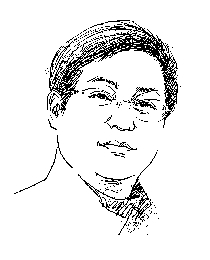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