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八岁时,邻居家来了个乡下亲戚。大姑娘,十八九,喜气的圆脸,梳两根油光滑亮的麻花辫,辫梢儿上系朵跳跳的红绒花,我觉得她:嗯,好看。所以在她走过路过我家门口时,我便常睁大眼儿瞧她,直到她脸儿红红的,伸手抓住我脑后的两把“小刷子”,使劲地、慢慢地拽一下。“大姐儿,哪有这么盯着人看的?”叫我“大姐儿”,就因为我在家排行老大;她叫我妈大姨,叫我爸大姨夫,这排行却不知从哪儿论起。
邻居那家大大小小五口人,一叠声却只叫她小玉,她每次都应得那个响亮,那个脆而甜,那个兴高采烈。“哎,来了,好的……”那带着乡音的普通话,在楼道走廊里回荡,像唱歌一样,真是好听。
邻居太太是个会过日子的人。孩子们吃饭前,她总陪某老师先扒拉几口,再去管孩子们的吃喝和洗涮。“某老师”是这家的男主人,老师是他的职业身份,女主人却常常在他刚拿起酒杯时,这样尖叫:“某老师,还喝还喝,明天我们家要喝西北风了!”我们隔几间房都听见了,可“某老师”却好像当耳旁风。“某老师”的话很少,那天他醉了,或许是借酒掩脸长叹道:“要是不喝一点,会病的……”不知是赞是叹,小玉姐见缝插针地说闲话:“乡下男人若不喝酒、不发脾气,就一定没结婚。”
有一次,四下无人,她悄悄地跟我说:“岁数大了,不好。”那当口,便叫我翻了脸,我正盼着自己长大,盼着自己的十八九,能长得像她那样的,如一只水蜜桃。
小玉姐到隔壁家才住了一个星期,就有居委会大妈上门来看长短:“姑娘,来看亲戚吗?”那笑吟吟的意思其实是:走亲戚的话,时间未免长了。那时的户口查得紧,但她早有准备,沏上香茶后,行李袋里拿出一份病历,又翻出若干土物,小心地递上,说:“上城里看病呢,亏得收留……”在大妈慢慢喝着茶,问东问西时,小玉姐却并不坐下,她侧着身子,微微弯腰,嗓子眼里不断发出讨好的“呵呵”的声音。
这“病”,一看就是大半年。我好奇地问过,究竟“凤体”哪里不适?她支支吾吾的,嘴角下撇,可就是没个准话。再问,便涨红着脸,吐果核一样吐出“妇女病”三个字,直让我的脑袋嗡嗡响,隐约觉得这不是好事。
她除了帮老姑家打理家务,还顺带帮了另一家,带个二三岁的婴孩。小宝的亲妈是知青,不在上海。说是帮忙,可那是真忙,婴孩跟她吃,跟她睡,把她当妈了。小玉姐对小宝真是没说的,掏心掏肺。小宝夜哭,她便整夜不睡,抱着哄。孩子发烧,她带去打针,那张脸竟忧郁得老了,像担心得就快晕过去似的。只有在夜阑人静,我才时常看到小玉姐,守着安睡的宝儿在织袜子,用复色的棉线,如绿配白,黄配蓝……袜底用深色,袜筒浅粉,收边处各收出不同的凹凸花型,煞是别致。那袜子显然不是织给哪个孩子穿的,亦非男袜。我只知道这傻大姐偏爱光脚。夏天午后,常见她赤脚大仙似的,飞奔在一条煤渣路上,为老姑家到饭店打一暖瓶冰水,用来冰镇晚饭的菜肴,也做冰杨梅汤饮。
小宝被养得白白胖胖的。她老姑也眼看着温柔许多,心情好时,常和老姑父对杯。小玉姐看着觉着有趣,洗碗时捂着嘴乐。而老姑的半大孩子们,也被管束得井井有条,头脸干净。老姑常夸小玉姐:“样样好,就一样,女孩家胃口未免大了些。”楼里各家大聚餐那次,她突然上前,拿掉小玉姐的大碗换上小碗,并且莫名其妙冒出一句:“跟你们说吧,女孩还是瘦的好!”
楼里最大的女孩就是小玉姐了,往下滴滴拉拉算起来有十几个之多。一次我问大家,都怕什么?只她犹豫、羞涩地回答:怕结婚。什么?什么呀?一群疯丫头因此而笑倒了。
那次笑场后不久,小玉姐就被逼回了老家嫁人,所谓妇女病,有点。可也是出来打工的借口,她借此攒嫁妆。那婚姻,据说是他们家乡女孩的传统老路,也并不算特别委屈她。但她真的不想这么早就结婚,可又不得不听从家里的安排。她说她姐出嫁的年龄,比她还早好些。
走之前,到我家来告别,哀哀的:“大姨啊,这些日子,是我做女孩儿过得最舒心、最自在的……”我妈含泪,硬塞给她两双尼龙袜子。她抚摸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穿呢,舍不得。”小玉姐走之后,我在枕头底下,找到了她趁我们不注意,悄悄留下的一双线袜。它们打扰了我整整半夜,或者更长,更长。
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失眠,也是进入青春期前的唯一一次。
(作者为作家、诗人,著有多部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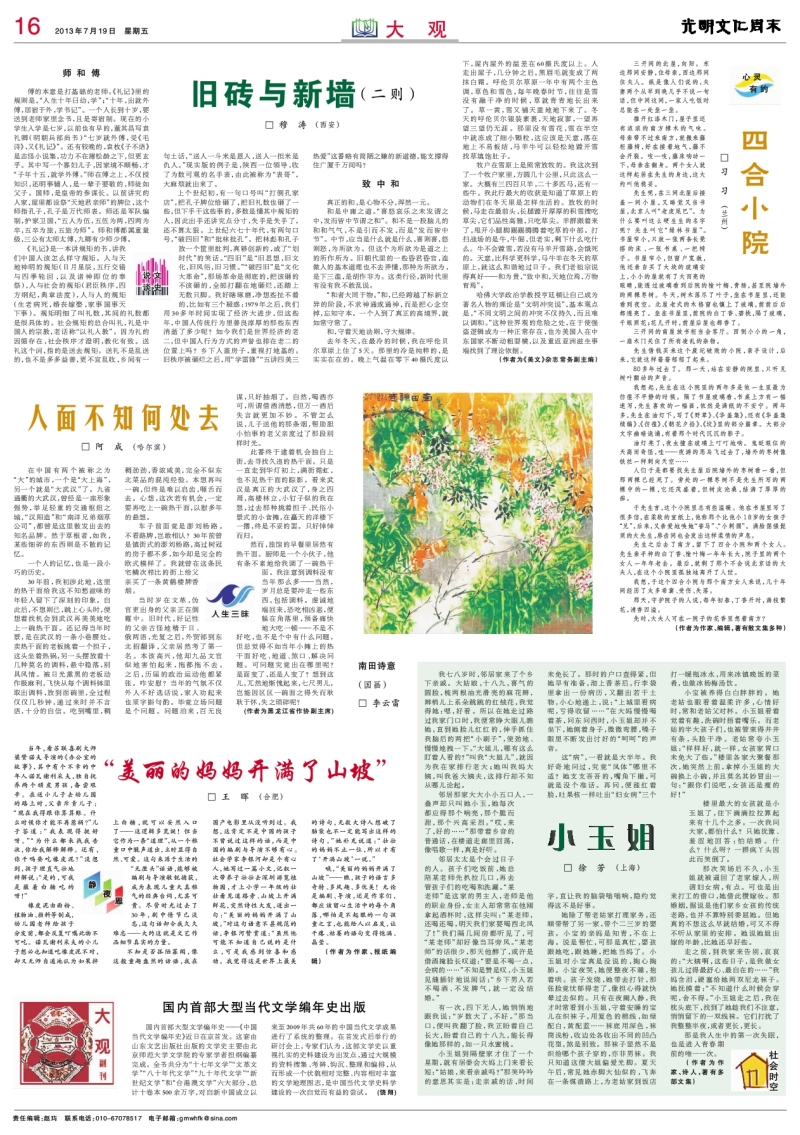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