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到“城市与文学”这几个字,我首先联想到的是西方古代的雅典与罗马,现代的巴黎与伦敦,中国古代的长安与洛阳,今日的北京与上海。在也斯的《城与文学》中,说的是香港。《城与文学》可以说是也斯对文学、特别是香港文学,其中也包括他对自己创作实践的思考与总结——完成这部书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也斯对香港文化的深刻论述,特别是他对香港商业文化特性的分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香港文化的驳杂,都市文化及对严肃文艺的蔑视;香港文人知识分子关于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与挣扎;商业潮流中文人知识分子的趋炎附势及学院中人的庸俗化与功利化,热闹非凡的表面下所隐藏的荒凉与冷漠等等。在世界上其他的大城市中,这种中西混杂、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城市文化景观是较为少见的,经历风霜重重转化的香港在世人面前呈现出的仍是一张模糊的脸。书中还多次提到“文化沙漠”的称号,使我们感觉到文化交流的趣味与诡异之处,我们也能体察到也斯对香港至今仍被称为文化沙漠的质问,对香港文学不为外界所知的愤懑,其中也有对香港文化的反思。
像也斯这样思维开阔而包容的知识分子是很少的,正如他自己说的,他看到的是多面的香港,因此更能反思香港的现实。这一切与也斯复杂的文化背景有关:从内地移民香港,在香港的乡村长大,到香港的城里谋生,再到美国留学,最后回归香港。因此,也斯对香港既有无法割舍的乡土之情,也有宽容、平和的反思。
在也斯讨论的众多关于香港的论题中,笔者最感兴趣的就是关于香港的文化身份问题。城乡不仅仅是西方现代文明与文学的基本主题,也是中西传统文化与文学共同的主题:苏格拉底的雅典,但丁的佛罗伦萨,狄更斯的伦敦,巴尔扎克的巴黎,乔伊斯的都柏林,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司汤达的《红与黑》,德莱赛的《美国的悲剧》无不反映了城乡的主题。中国《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文王的“作邑于丰”,《小雅·斯干》中武王的定都镐京,特别是《小雅·都人士》对城中人的描写更是令人感受深刻:“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其对城里人的崇拜与向往我们在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中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他如屈原的郢都,中国历代文人反复经历的被贬谪、流徙、放逐的经验,无不以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这样的大都市为中心,展开政治人生的各种悲欢离合。鲁迅、沈从文、贾平凹、莫言等人作品中的城乡主题,则从另一个角度呈现了现代中国的城乡悲喜剧的发展历程。
阅读也斯对城市文明及文学的思考,对于理解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城乡文化历史的国度,且正在大规模推进城镇化进程的今日,会有很好的启示。
也斯在给友人苦瓜的诗里说:在田畦甜腻的合唱里/坚持另一种口味/你想为人间消除邪热/解脱劳乏,你的言语是晦涩的/却令我们清心明目。我们拿这首诗来述说城乡的不同的审美价值趣味,不也是很合适吗:在城里甜腻的合唱里/坚持乡间的另一种口味/城市想为人间消除邪热/解脱劳乏,乡间的言语是晦涩的/却令我们清心明目。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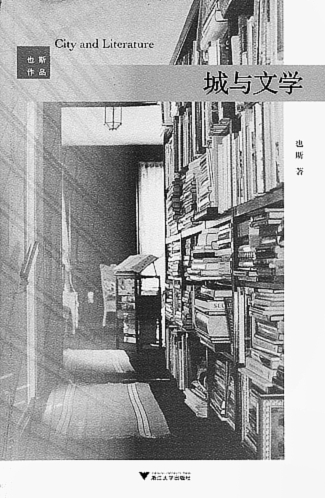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