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曾经说,他所写的一切都来自《圣经》,因为《圣经》是“艺术的伟大编码”。他没有夸张,人们甚至可以说,西方的所有思想都可以追溯到《圣经》这个源头。比如在西方思想中,人类喜欢把自己视为万物的“灵长”,动物王国的高级物种,生物界的王中之王,进化链中的最后一环。在西方中世纪神学中,有一个“生物之链”的概念,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存在,从上到下按顺序排列应该是上帝、天使、人、动物、植物、无机物。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时,为每一个类别都安排了固定的位置,因此整个世界才有秩序,这就是所谓的“天命”或“上天的安排”。人类可能会抱怨,上帝没有给予他牛的力量、鹰的视力、狗的嗅觉,但是上帝并没有亏待人类,上帝给予了他更多的智力,并使他能够使用智力去控制身体比他更强大的动物。这种人类即灵长的思想可以说也来自《圣经》。
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对人类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大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引文中“治理”(subdue)和“管理”(dominion)在原文中的意思都更加尖锐,应该理解为“征服”和“统辖”,那么上帝对人类所说的这句话就是授权人类“征服大地”、“统辖万物”。这样的思想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为人类开发自然和利用自然提供了理论依据。
十七世纪是西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发展的关键时期,笛卡尔的哲学、培根的经验主义、牛顿的物理学逐渐开启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人类的主体与世界的客体被分离开来,自然被视为外在的、机械的、没有灵魂的物质存在。人类由于具有理性、道德和精神意识,被认为具有至高无上的优越性。人们相信,理性可以穿透一切奥秘,科学将把人类智慧的“帝国”延伸到自然界。
欧洲十七世纪的科技发展使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自然不再是中世纪的人们所认识的自然,不再有神仙和精灵。自然仅仅是由微小颗粒构成的、机械的物质世界,因此毁坏自然仅仅是毁坏了没有感知的物质,人们的良心不再会受到负罪感的困扰,对自然的开发和掠夺就更加肆无忌惮。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予了人类更多的毁灭性力量,其结果就是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更大的破坏。可以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对自然进行破坏的历史。米歇尔·布瓦索在《羊皮卷》一诗中描写了一本羊皮书,可以说这本书同所有书籍一样,承载了人类的思想和文化。如果没有羊皮作为纸张,那么这些思想和文化根本就无法传承。也即是说,文明的传承依赖于对自然的开发。上层建筑依赖于物质基础。人类文明的发展,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必然对自然造成破坏,问题是破坏的程度是否在可持续和可控的范围之内?
在西方文学中,人与自然常常表现为两个对立面,并且人类常常具有世界主宰的气场。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小说《白鲸》描写了亚哈船长出海剿杀白鲸的经历,其特别之处在于他的猎物不是轻易就范的动物,而是一头巨兽。但是亚哈船长已经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杀死这头曾经咬伤他、在他看来代表了邪恶的鲸鱼。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描写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古巴老渔夫出海捕鱼84天未有收获,第85天巧遇一条大鱼。虽然他年事已高、力不从心,但是他没有放弃,而是表现出了“只可被毁灭、不可被打败”的男子汉气概,最终征服了那条大鱼。读者应该已经意识到,捕鲸或捕鱼都具有寓言性质,它是人与自然进行斗争的一个缩影。自然就像一头巨兽,它不会轻易就范,然而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总是表现出“人定胜天”的气概和勇气。值得人们思考的是,这种“人定胜天”的精神是否应该提倡?它是否是我们对待自然的正确态度?
自然没有了树精、河怪和土地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随意对自然进行破坏、随意对自然进行掠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人类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在《采坚果》一诗中描写了一个乡村少年对林木施暴的过程。他来到一片静谧的树林,这里人迹罕至,花朵盛开,树木葱郁,溪水潺潺,一幅原生态的景象。他在那里稍事歇息,感到心旷神怡,然后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动手折断树枝,直到树林被完全毁坏。这时,少年才被自己的行为惊呆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故事也是一个寓言:它反映了人类为了生存对自然进行的索取。采坚果是乡村生活中的一种常见行为,是生存的一部分,然而贪婪和无知也可以使这一简单行为成为一种罪行。这说明生存的理由是有一定限度的,生存不能以破坏自然作为代价。
同样重要的是,人们应该意识到破坏自然不是一件可以随意为之的事情,而是一件必须为之付出代价的事情。英国诗人柯尔律治在《古舟子咏》一诗中描写了一次驶向南极的冒险航行,古水手从英国出发,跨过赤道,到达南极。一路上,有一只信天翁尾随船后,捡食船员们丢弃的食物,同时也给航行带来了平安。但是,古水手突然拿起弓箭,射杀了这只大鸟。这次毫无理由的攻击改变了这只船的命运,招致了“极地精灵”的可怕报复。在回程途中,风停了,水用完了。船停在赤道上,经受着烈日炙烤,酷热难耐。水手一个接一个地倒地死亡,古水手在炎热、干渴、恐怖的环境中进入了他的人生地狱,生不如死。古水手的行为招致了良知的谴责,他的灵魂从此无法平静。罪恶感迫使他周游世界,讲述他的罪孽,以求救赎。也许我们也意识到,古水手射杀信天翁的行为是人类破坏自然的象征,古水手所受到的惩罚实际上是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应该说,欧洲具有全世界最优越的地理环境。它没有沙漠,没有地质灾害,没有酷暑严寒,终年气候温和、雨水充足,因此形成了植被丰厚、鸟语花香、流水潺潺的怡人景象,有点像《圣经》上的伊甸园。莎士比亚称十六世纪的英国为“神奇的岛屿”,“梦幻的岛屿”,然而工业化、城市化给这片美丽的土地增添了许多烟囱,使伦敦变成了雾都。到十九世纪,英国变成诗人布莱克所说的“魔鬼的作坊”。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实际上给人们展示了欧洲的“失乐园”的历史。气候变暖、空气污染、森林退化、资源枯竭、物种消亡,我们时代的生态和环境危机似乎都跟工业化、城市化有关,跟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有关。如果我们了解了以上思想史,也许我们就更能够理解欧洲人对环境保护的热情。可以说,它代表了一种“复乐园”的冲动。
(张 剑)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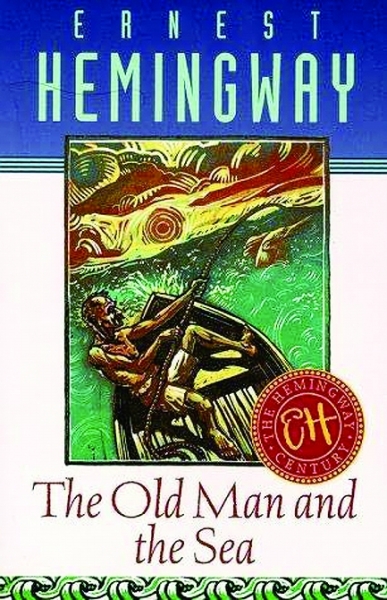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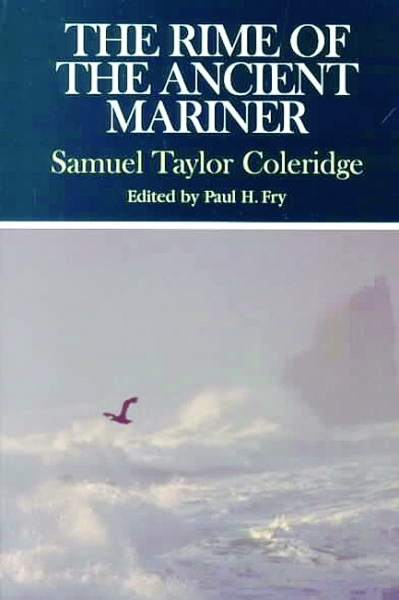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