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八佾》: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子贡想省去鲁国告朔(每月初一祭祖庙)用的那只活羊。孔子说:“赐呀!你舍不得那只羊,我舍不得那个礼。”
其实,在礼坏乐崩的时代,鲁国国君已不亲自去祖庙举行“告朔”之礼了。子贡想,既然一切都只剩下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洞的形式,那还不如再简单些,何必每月还费一只羊,又麻烦,又浪费。但孔子是那么深深地眷恋着古代的礼呀!即便是一个形式,也是古礼的遗留,他也不忍心丢弃。再说,假如礼仪形式照这样简化下去,到最后,那古礼不也就真的烟消云散了?
有时,保留一个形式,哪怕它是空壳的,对人也还是一种约束,一种提醒,也还存在一种象征的意义,提示我们一种文化、政治与道德上的价值。这种价值我们可能会漠视,但不能遗忘,更不能否定。关键时刻,这种价值还会给我们提供一种道义上的支撑,以及反抗的理由,批判的依据。
所以,很多传统礼仪的形式,即便是看起来已经沦为空壳的形式,也是极其重要的,决不是可有可无的。
再看《论语·卫灵公》:
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
盲人师冕来见孔子,走到台阶边,孔子告诉他:“台阶到了。”走到座席边,孔子告诉他说:“座席到了。”大家都坐下后,孔子告诉他说:“某人在这里,某人在这里。”
按说,古代的盲人乐师都有“相”,也就是扶持他走路的人,不必孔子如此费心指点,何况此时孔子身边还有很多学生,也可以照顾这个特殊的来访者。但是,孔子看见盲人进来,眼睛就没离开过他的一举一动,并随时予以提醒。这些提醒,也许对师冕不必要,但是,于孔子自己,却是一种自然的关心与牵挂。这不是在思考了自己是否应该这样做之后的理性指导下的道德行为,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出于仁慈内心的第一反应,是后来李贽所谓的“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的“赤子之心”;也不是理性思考了这种关注于对方是否必要的问题,而是感性感受对自己是否必须的问题。简言之,这种关心,不是对方需要,而是我们需要:假如我们心灵中有自发的仁慈,这种关心就几乎是本能的,不加以关心倒是很令我们难受的,这种感受迫使我们对对方施加关心,甚至是不必要的关心。
生活中,我们也发现:父母对子女,似乎总是啰唆的,而子女总是厌烦啰唆的——因为不必要。可是子女一旦成了父母,马上又开始对自己的子女啰唆了。这种啰唆,乃是出于一种极为殷切的关心与不放心,而不是出于理性分析——事实上,经过理性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关心与爱都是“不必要”或无用的。但是,这些从实用角度看来“不必要”的爱与关心,于人生,于世界,于你我,真的不必要吗?
这世界,太多的关心,于事不必要,于心不可缺。“关心”一词,或许也可解释为:它不但关乎对方,而且关乎我们自己的心。
这个盲人乐师,虽然看不见孔子的面容,但是听着孔子温和关切的提醒,他的内心,岂不感知到一种温暖!不必要的提醒里,包含着人生不可缺的温暖!
两千多年以后,我们读到这一段,孔子对盲人无微不至的关照,一一指点的爱护,那种场景也还是如在目前,那种圣人的慈祥,也还令我们感动不已!
在这种感动中,我们不仅感知到了世界的温暖,还不知不觉地改变了自己。
其实,当场,就有一个学生被感动了。那就是子张。
师冕走了以后,子张问:“这就是与乐师讲话的方式吗?”
孔子说:“是的,这本就是帮助盲人乐师的方式。”
这就是“仁”在日常举止中的体现啊。
“仁”也就该体现在待人接物的日常举止中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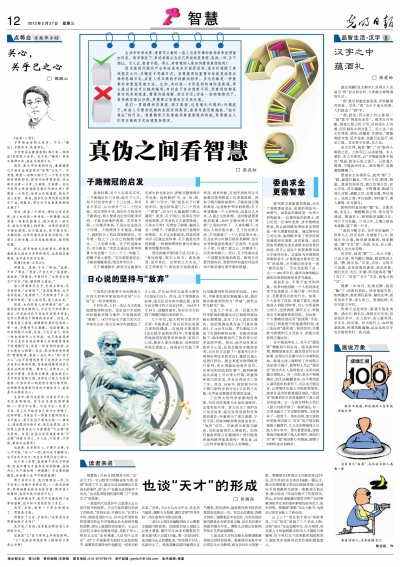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