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当年生活的西部乡村,离自然很近,离人很远。出门遇见的飞禽走兽较多,遇见的人较少。他说,有时看到一只鸟,它怎样动作和鸣叫,于是就知道今天天气怎样;有时太孤独了,就对石头说话,扒开蚂蚁窝对蚂蚁们说话。
阿来,一位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一个在群山与大地之间诗意栖居着的真实灵魂。不论他走到哪里,心中不变的是对那片圣洁土地最纯洁、最真挚、最热烈的爱。
语言是最初的障碍
“阿来的帽子”写作是偶然的开始尘埃落定前的挣扎写作相当于一湖水决堤而出,把所有情感的蓄积挥霍得一干二净《科幻世界》在他手里成为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我不能忍受自己对置身的环境一无所知”
阿来从小就很喜欢读书,有时甚至一个晚上就能看完一本小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阿来读的书都是从州府马尔康背回来的。他读的第一部历史书是《光荣与梦想》,第一部小说是海明威的,接下来读的是福克纳、菲茨杰拉德、惠特曼、聂鲁达的……那个时代,书并不多,但令阿来感到幸运的是,当他一开始接触到书这个物品时,很快就与经典结缘。直到现在,他仍然常感叹:那个时代,我们没有畅销书,所有的书都是经典;那个时候,我们看书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但看每一本书都非常珍惜。
其实,阿来的读书经历并不是那么顺利。因为语言障碍,曾让儿时的他一度很焦虑。在藏区上小学时,一年级的阿来并不会讲汉语。在学校里,第一年叫作“预备班”,老师不教任何正式的课文,就是教说汉语。刚开始学汉语的阿来很困惑,“汉语是很复杂的,我常常需要死记硬背老师说的都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当时根本就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回忆起当初学汉语的日子,他记忆犹新。“后来我每天学习汉语,词汇量到了一定程度,对汉语的把握也到了一个程度。我觉得自己大概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才真正进入汉语里,突然之间恍然大悟,平常焦虑的那些事情都不存在了,从课本上学来的那些只知道是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的事情一下都明白了。从此以后汉语世界的大门就对我彻底敞开,再也没有任何障碍了。”
“阿来的帽子”
1976年,原本梦想着去读大学,然后留在大学当个教授的阿来,遇上了“上山下乡”。
初中毕业的阿来成了“回乡知识青年”,回到村寨与父辈一同挣工分。阿来人生中第一次感到不公平的是,那会儿上山下乡,同一个班,同在一起上学的人,这里头就有了等级之分。城里头的人上山下乡,国家给他们补助,戴红花,去农村给他们安家。“但我们这些本来从农村到城里上学的孩子,内心里一直充斥着凄凉,而那时也没有人管我们。”回乡半年后,阿坝水电站到乡村抽调民工,阿来主动报名参加,成为建筑工地的一名合同工,当时阿来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拖拉机手。他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帮助他实现愿望的竟然是他的帽子。
有天中午休息,阿来就把帽子洗干净挂在那儿,怕人偷走,就在帽的里子上写了几个字,“阿来的帽子”。写了字也不放心,还是怕丢,于是就在那儿看着。水电站的领导,一个山西南下的干部,现在想想至少是工地指挥部的一二把手,看到了“阿来的帽子”后就问,这个字写得很好啊,谁写的?于是阿来上前重新写了一遍,领导看完之后便问:“小鬼,你还想不想有文化?想不想学点技术啊?”当时阿来在工地上当工人,年纪小,工作量非常大,每次抬花岗岩,一块有一二百公斤重,劳动强度很大,所以阿来想学点技术。这下好了,因为写得一手好字,深受领导欣赏,他成为了一名拖拉机手。
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消息传到阿来所在的偏僻山寨时,报名已接近尾声。求学心切的阿来,借了一辆自行车,连夜骑了几十里路,赶到了报名现场,但还是晚了。在了解阿来的相关情况后,工作人员动了恻隐之心,同意为他补报。这一破例,让阿来喜出望外,他盼望能够通过高考走出村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而当时他对外面世界的全部理解,来自曾经到村庄来勘探森林资源的地质队员。怀揣着当地质队员的梦想,阿来在志愿表上郑重地填上了两所地质学院。然而他未能如愿,只考进了阿坝州的一所师范学院。两年后,阿来毕业被分配到一个比自己村庄还偏僻的山寨做老师。
希望一点点破灭,然而这一刻,他选择了对文学的尝试。
写作是偶然的开始
阿来刚开始写作并不是因为对文字有很深厚的感情,只是上世纪80年代,在那个偏远的县城,阿来的周围时常会聚集一群志存高远的“文学爱好者”。他们写作的劲头,一开始还让身为中学老师的阿来感到费解。那时的阿来,还是一名优秀的教师。每天围绕着备课、看书、和朋友聊天,似乎没有想象过有一天会写作,甚至成为一名作家。
阿来说,那个时代的学习气氛很浓。周围的人很喜欢读书,阅读在他们心中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读过许多经典著作的阿来,并不害怕写作。他看完别人写的作品之后,并不太满意。刚开始,他觉得写作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决定尝试写点什么。当阿来写完第一首诗——《母亲,闪光的雕像》后,兴致勃勃地给老师、同事、朋友们传看,他们看后都感叹:你写的诗的确比我们好!
阿来投稿了。《母亲,闪光的雕像》“一鸣惊人”地为他赚到了人生中第一笔稿费。他兴奋,又似乎在情理之中。从开始写作那一刻起,他坚信会比同龄人写得好。他用第一笔稿费,请大伙儿撮了一顿。
阿来开始了创作生涯。那一年,他25岁。
尘埃落定前的挣扎
从1982年到1989年,阿来一直都在写作中度过。
1989年,阿来30岁,看似很年轻,但他的内心已与许多年轻人不大一样。突然间,他意识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于是,他重新思考写作的意义——为什么写作,写作究竟能干什么?
就是这一年,阿来放慢了创作的脚步,放下了笔,又一次重拾往昔的经典。就在这一年,他又读了许多中外名著、地方史研究等。阿来意识到,写作本身并不重要,写作是为了寻找生命的意义,为了寻找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停下笔来的这几年,他跟往常一样生活,只是每天他都在不断思考一些问题,一个接着一个的问题让阿来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他的思考变成了思想沉淀下来,他的疑问被之后的写作一一解答。
阿来说:“我写作的产量很小,写一本书的时间很短,但停下来思考、酝酿、沉淀的时间总是很长。有时3年,有时甚至6年……”
5年后,那是1994年的春天,忽然有一天,阿来觉得可以开始写点什么了,并且这一次,写的东西一定是和以前不一样。于是,他打开电脑,坐在窗前,面对着不远处山坡上一片嫩绿的白桦林,村子里传来杜鹃啼鸣声,多年来在对地方史的关注中积累起来的点点滴滴,忽然在那一刻呈现出一派隐约而又生机勃勃、含义丰富的面貌。于是,《尘埃落定》的第一行字——“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便落在屏幕上了……
5个月后,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完成。这次激情的创作是他情感的一次剧烈燃烧。阿来回忆说,停笔的5年对他创作《尘埃落定》有着重大的意义。5年里,他一直在求证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5年里,他一直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5年里,他解决了自己最初的困惑,那就是写作的意义是为了寻找个体与世界的关系,寻找自己在世界的位置。
《尘埃落定》的问世奠定了阿来在文学界的地位。很多人看到的是阿来《尘埃落定》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的光芒,但在这之前,阿来所经历的内心沉淀与挣扎鲜为人知。
写作相当于一湖水决堤而出,把所有情感的蓄积挥霍得一干二净
当《尘埃落定》引起的喧哗逐渐散去,阿来回归故土,久久凝望窗外苍茫浮云和远山斑驳的积雪。在他心中,《尘埃落定》是他对康巴故土的一个交代。在那片土地上,一直都深深印刻着他出发时留下的足迹。那片土地、那些足迹,当他一次又一次回到故乡,从头把自己书中歌咏的嘉绒大地走了一遍之后,童年的记忆、儿时的触感在他内心深处呐喊,他提起笔,继续写作。
继《尘埃落定》之后,2005年,阿来又推出了长篇小说《空山》。当年的《尘埃落定》用鲜血和死亡、用黑夜的意象象征一个时代的终结,如今的《空山》则用漫天大雪、用“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空山象征未来的不可预测和人对未来想象的无力感。
写诗出身的阿来,喜欢拿捏语言的表意尺度,力图用简洁精准的用词勾勒人心世态。这种诗性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擅长片段式表达,擅长在精致和细微处透视宏大,擅长在故事中营造特殊的“意境”,擅长从容而淡定的叙事腔调。同时,在汉藏两种文化之间徘徊的阿来,带着与生俱来的特殊气质。阿来自己对《空山》的满意度胜过《尘埃落定》。他认为《空山》不论在写作技巧,还是故事叙述方面,都比《尘埃落定》娴熟。他还开玩笑地说:“写作,当然是会越写越好,越写越有感情的。”
阿来说,他在中国文坛中并不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他不喜欢太快地写作,甚至有些讨厌没日没夜地面对文字,无情敲击键盘。2009年,一贯慢工出细活的阿来终于推出新作《格萨尔王》,这距他的《尘埃落定》已经11年。这些年,阿来始终以藏族题材为背景创作小说,他像一个国王在自己的疆域驰骋。
阿来的写作为何总是如细水长流般,慢慢地,慢慢地……他有个著名的理论:“就像轰轰烈烈谈过一次恋爱之后,马上又开始和另一个人再这么刻骨铭心地来一次,我做不到。小说写作对我来讲,不是这么简单的事。”阿来的内心里,对于文学创作的观点一直很坚定。他认为,文学创作必须融入个人深刻的情感体验,书写中自然就有巨大的情感投入。所以,每当他写完一部作品,都不能马上就进入下一部作品的创作。不是因为没题材,也不是因为身体太疲惫,而是经过前一度的写作,总会觉得情感上空空荡荡,再怎么努力,也没有表达的欲望。每一次提笔,对阿来来说都是一次情感的蓄积,这个过程,就如一潭山谷间的湖泊,慢慢被春水盈满。他认为,写作相当于这一湖水决堤而出,把所有情感的蓄积挥霍得一干二净。“下一本书,我得修好堤坝,等水再次慢慢盈满,再次破堤。一部长篇的写作,尤其如此。”
《科幻世界》在他手里成为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
1996年,阿来离开生活了36年的阿坝高原,来到成都。离开阿坝,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意味着更多机会。阿来并不喜欢一个城市的外表,后来他喜欢上了成都。他说:“我1996年从阿坝来到成都工作生活。起初,我也无非是觉得,对一个写作者来说,相对我老家,在这里工作机会更多。那时,大家都说,成都是可爱的。因为节奏比较慢,城市中有好多茶馆,城市的外围还有好多农家乐。但我觉得,一个城市有这样一些特征固然有其可爱之处,但如果只有这个,这个城市也让我厌弃。我喜欢这个城市,融入这个城市,是因为现在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一些人,和过去生活在这个城市的那些人,书写并表达了这个城市。因为这些书写,这个城市才具有了审美上的价值。”
阿来来到成都后,在《科幻世界》杂志做一名编辑。当时,正值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不久,中国社会、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刚到杂志社不久的阿来,便面临杂志社体制改革问题。体验一下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过程,也是阿来走出阿坝的目的之一。当时,他在这一过程中摸索着,一路走来。原本不懂“产业化”、“营销”等市场话语的他,很快便适应了正在经历市场化改革的杂志社。也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他便做上了《科幻世界》的总编辑。
阿来说,《科幻世界》的总编辑不好当。每月一期的杂志需要大量稿件,稿件筛选就是很大一部分工作;其次,在筛稿中还得有敏锐的观察力,善于发现好稿。要是没有好稿,只能苦苦去约稿。一提到约稿,阿来便觉得有苦难言。“我要去找一篇好的稿子,别人不会因为我是阿来,我是名作家,我写了《尘埃落定》,就把稿子给我。做杂志这事儿,关键在于经营,那是和写作没有太多关系的另一个领域。”1998年,阿来担任《科幻世界》总编辑、社长,在他做总编辑的这些年,他带领着《科幻世界》走上一个个新的高点。杂志发行量由当初的几万份迅速发展到几十万份,《科幻世界》在阿来手里由一本杂志衍生出五六种,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
阿来不仅是个成功的作家,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阿来说:“我最大的特点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甚至当年在阿坝当中学老师时,我也是当地出类拔萃的中学教师。”
对于阿来来说,写作并不是他的全部。“我从来没有把写作看作我的职业,因此我一直都在做着其他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是去旅游。文学作品的灵感永远都是来自于真实的生活。一份职业能够让你找到你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只有真切的感悟过生活之后,才能写出丰盈的文字。”
“我不能忍受自己对置身的环境一无所知”
一个网友发了这么一条微博:我在微博上关注一个作家,叫阿来,就是写《尘埃落定》的那位。你看他的微博,就觉得这个人跟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但不在一个海拔。因为他的微博上全是花花草草,他对世界上一切的花花草草都感兴趣,他走到任何地方,都会把这些不知名的花草拍下来,然后找明白的人把花草都认出来,发上微博。
从小生活在大自然怀抱中的孩子,早已成为了一位自然的记录者。
从小在藏区长大的阿来,对于传统的藏族文化并不在意太多,他太在意每一株花花草草的宿命,他从骨子里透出了一种对花草无尽的喜爱。他的朋友、著名作家迟子建在《阿来如花的世界》一文开头写道:“阿来与花,是否有着前世的因缘?至少,我没见过像他那么痴迷于花的男子!”
阿来对植物的观察与记录,主要是在青藏高原,那是他在寻访地方文化、人生故事,欣赏自然地理之余的一种调剂。在阿来的世界里,植物不是自己生长在那里,开花结果。植物同时和人发生关系,被人利用,被人引种,被人观赏,把这些方面发掘出来,就是一种文化。植物会把他带入它们自己的世界,它们生命的秘密世界,同时,也把他带到一个美的世界,一个有人活动其中的,文化意味悠长深厚的世界。
小时候,阿来和他的伙伴们在草原上和牛羊一起奔跑。天地之间,他们自由安静地生活着,陪伴阿来成长的,除了高原的阳光,还有草原上像星星般绽放的野花。阿来说:“我不能忍受自己对置身的环境一无所知。”有人认为这是狂妄的话,他却认为这是谦逊的话。每当阿来走到一株不认识的植物面前,他内心开始犹豫、挣扎,于是他仔细拍照,开始查资料、对比、询问,就为搞清楚这种植物的名称和特性。“既然我们身处如此开阔敞亮的自然界,为什么不试图以谦逊的姿态进入它、学习它呢?”于是,因为对植物的情有独钟,他的新著取名《草木的理想国》。
《草木的理想国》是阿来博客“成都物候记”系列文字的集结,记述了他2010年手术康复期间在成都拍摄、记录植物的经历和感受。2010年,阿来生了一场病,在做手术前,他在病床前放了很多书,想通过认真读书让自己分心,不去想身体被锋利刀刃划开的瞬间。但书籍并没有让他忘却手术的恐惧,反而是手术前夜在江边的腊梅暗香让他感受到了心安,那一夜的睡眠也变得安详。那次手术后,阿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能再上高原,于是他每天游走在成都市区观察蜡梅、海棠、玉兰、紫荆、丁香、栀子、紫薇、芙蓉等植物。他说:“我将它们一一拍下,回去检索资料,看它们在植物学上的意义,以前的文人怎么描绘它们,然后书写植物花事。这一来身心都愉悦了,这个瘾过得比有了好菜想喝二两好酒自然高级很多,也舒服很多。这是一个轻松、美妙、享受的过程。”
书中记录了他眼中成都这座城市的花木,这不是纯粹科普意义上的观察与书写,阿来在书的序中写道,这是一次反思,引领大家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在书中,阿来努力把科普、游历、城市人文这些看似不相干的事物熔为一炉。用这样一种方式,去写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与性格。阿来说,中国人都有宏大的关于爱的宣言,爱国家、爱民族、爱自己所出生或生活的城市或乡村。但这种热爱在各种表达中又略显空洞,说了爱,但不说爱的理由。没有理由爱就会显得空洞而虚假。阿来不反对别人轻易说爱,但他不允许自己这么干。
阿来觉得草木是一种美,这种美对于人心灵的净化与提升是非常直接而有力的。因此,一朵艳阳下的花,一株风中摇动的树,所作呐喊的宣示,凝聚我们心境的作用,远比时代的精神导师贡献的效果更鲜明、健康,也更加纯然。对于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阿来说:“一个人是可以没有那么多琐事的,只要你不对人与人之间的复杂曲折关系过于热衷或屈从,你就可以获得解放。就会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你就可以读一点有关审美的文字,看到周围事物的自然美态。”
(本报记者 牛梦笛)(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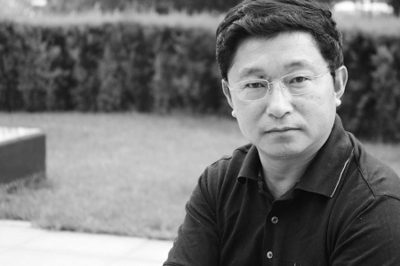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