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的长篇新作《红罪》是一部蕴藉生命质感和人性温暖的厚重之作,小说主要通过钟长水、赖全福、李双凤等背负“红罪”的革命者在历史悖谬中的革命追求和灵魂挣扎,演绎了一段“从未揭示却真实发生在红土地上的红军秘史”,作者以沉重的笔触在历史的粗粝处触摸生命的疼痛,以悲悯的情怀在命运的无常中谱写人性的悲歌。
赣南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历来是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重镇。从湘赣边界的枪声到井冈山上的星火,从安源工人大罢工到万里长征第一步,无数英雄史诗为赣南革命历史书写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创作资源。然而,与此前正面反映波澜壮阔的苏区革命历史风云不同的是,刘华在《红罪》中另辟蹊径,他把逡巡的目光投向宏大历史的背面,贴近赣南土地上最广大最默默无闻的一群,真实记述了峥嵘岁月一群特殊人物渐被尘封的往事,在坚韧而沉静的叙述中敞现风尘仆仆的历史沧桑,重构革命历史与乡土大众的血肉联系和精神纽带。
据史料记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240万人口的赣南有33万多人参军参战,除去10万多有名有姓的烈士和3万多参加长征的战士,还有大量默默无闻的无名烈士和失散人员。他们既不在烈士名单中,因此家属无法享受优抚政策;他们也不在长征队列中,所以长期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然而,与所有名载史册的英雄们一样,这些默默无闻的人们同样为了一种真诚的信念和朴实的追求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热血、情感,甚至生命,《红罪》中的主人公钟长水正是这个群体的代表。诚然,无论是从参加革命的动机还是革命过程中的表现来看,钟长水也许都算不上一个“典型”的革命英雄。他是在父亲钟龙兴和恋人九皇女的身心“夹击”下走入革命队伍的。身为乡苏主席的钟龙兴为了尊严和荣誉,把长水、长根、长发捆绑到三营当红军,而扩红模范九皇女却利用自己的身体和情感,让钟家的三位后生矢志革命。对于熟悉历史教科书的读者来说,也许从逻辑上难以理解《红罪》的这一革命叙事指向。然而,历史不仅是英雄豪杰博弈的舞台,更是平凡人们生活的空间。当我们从民间的立场走进历史的后台时,不难发现,其实正是这些既藏污纳垢又生气淋漓的生活细节和情感故事更接近历史的本相。
《红罪》在对革命先辈满怀敬畏的叙述中始终没有放弃对于每一个生命个体的悲悯和咏叹。为了兑现爱情诺言,钟长水甘愿背负“红罪”受屈终身。为了守护红军宝藏,赖全福甘愿引爆矿山牺牲生命。为了保卫红色政权,九皇女甘愿放弃爱情献出身体。当我为钟长水们缺乏庄严神圣的革命动机和行为感到“不合常理”时,却又不得不为他们誓死不渝的忠诚和坚韧感到“不可思议”。
刘华对革命、历史、生命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和体察。他以沉静的笔墨和丰沛的想象打捞并粘合那些散落在民间的历史碎片,用一组组既模糊又清晰的历史影像和生命群雕为赣南的红色记忆作出最质朴、最真诚的注脚:历史并非都是运筹帷幄或大义凛然,并非都是慷慨悲歌或泣血咏叹,在严酷的历史长河中也同样流淌着让人苦涩难言和隐痛难忍的平凡真实。刘华既不回避苦难,也不渲染苦难。他尽量放低自己的叙事姿态,尽可能贴近大地的鼻息,满怀敬畏地触摸粗粝的历史河床和温软的情感记忆。向来在散文和小说两个园地默默耕耘的刘华不但在《红罪》中保持少有的叙述耐心,表达对历史和传统的敬意,在革命历史的大背景下展现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伦理,让读者在生气淋漓的细节中触摸历史真实,而且具有清醒的文化自觉意识,在革命历史的叙述中努力开拓地域文化空间,在英雄人物的塑造时执著探寻深层精神支撑,让高远的历史天空与丰富的民间大地相融合。
在刘华看来,历史同样“有血肉有肌肤有气息有表情”。文化风习既是各种人物的“精神家园”,也是一方水土的“精神履历”。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十倍兵力、五次“围剿”,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屹立赣南五年之久,在诸多原因之外,应该与客家人血脉相袭的性格基因密切关联。
千百年来,客家人在寻找家园,开辟和保卫家园的生生不息的抗争中,铸就了顽强坚韧、重情重义、乐观豁达等诸多优良品格。正是这些品格,成为赣南人民在血雨腥风中的强大精神支撑。几乎对于每个赣南客家人而言,革命历史就是自己的家史,述说红色故事就像随时端出待客的擂茶和米酒。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钟龙兴绑子参军,九皇女舍身扩红,钟长水忍辱护矿。当然,更值得重视的是,文化风习在《红罪》中已不再单单是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和人物活动的场域存在,而是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参与到小说的叙事中来。《红罪》的叙事构架主要由革命历史与文化风习支撑,革命历史的主体红军战士与文化风习的载体赣南后生合而为一。在小说中,抢打轿、喜帖子、添丁炮、祭野鬼、夜啼郎、上梁赞、长命锁、献花形、拣金等赣南客家风习和方言口语与扩红、参军、战斗、挖矿、护矿等苏区革命历史互为表里,相得益彰。这些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赣南客家风习大大拓展了作品的叙事空间,增强了轻盈的生活诗意,使得充满了血与泪、纠缠着罪与罚的革命历史叙事,在沉重的苦难与轻盈的诗意之间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张力。这种融文化风习于革命历史的叙事策略,正是刘华开拓新的革命历史叙事空间的一种自觉努力。
在中国当代文学进程中,关于“革命历史”题材的书写具有特殊的文学审美功能和现实政治意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为代表的“红色经典”,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下,以史诗性的笔触,塑造坚忍不拔的英雄形象,叙述宏大的革命历史进程,既为新社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作出证明,也为转折时期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红高粱》、《白鹿原》、《活着》等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从民间的角度重新打量历史进程,在宏大历史时空背景下,展现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试图质疑历史史诗,解构宏大叙事,颠覆英雄传奇。革命历史小说的两种叙事路向既是时代文化语境使然,也是作家写作策略选择。历史既是文明的进步史,也是人类的生活史,其间既有伟大人物的英雄业绩,更有普通民众的生存焦虑。以英雄为主体的革命史诗在进行宏大叙事过程中必然会遮蔽诸多丰富的生活细节和复杂的情感内涵,以民间为场域的新历史主义在呈现日常生存图景时则可能陷入历史迷雾的纠缠与戏说。因而,如何在革命历史叙事中既彰显人文关怀,又不迷失历史理性,既追求情感厚度,又不放弃思想高度,这些应该是当下革命历史书写寻求突破的新路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华的《红罪》为开拓革命历史新的叙事空间提供了新的可能。
(作者为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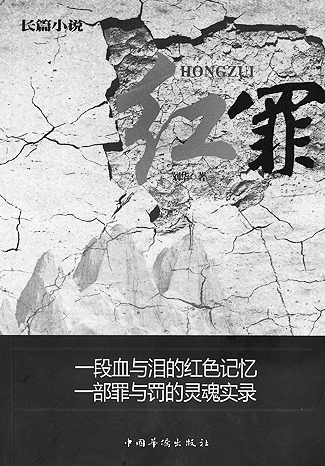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