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为政》的这一则是大家熟悉的: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是孔子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言语之间,颇有自得之意。
如果一个人,一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克己复礼,学而不厌,老年之时,升座崇高境界,那种成就自我的感觉,无疑是美好的,也是他该得的奖赏。
但是,《论语·子罕》中,还有一段话,也是孔子晚年总结自己平生而发的感慨。不过,这段话里透露出的,除了自我的肯定,还有一丝寂寞: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能够一起学习的人,未必能一起达到道的境界;能够一起达到道境界的人,未必能一起立身于道中;能够一起立身于道的人,未必能与他一起不拘泥于道。
孔子这里说了四种层次:一起学习的人;一起学到了道的人;一起立身于道的人;不被道拘束的人。
每上一层,就会淘汰一批人,自我提升的同时,也是自我对人群的自绝。最后,踌躇四顾,可能只剩独自一人。于是,堂皇之时,不免彷徨;自得之间,不免自失。
曲高自然和寡。德高自然孤独。
学识越深越伶仃。
孔子独处高绝的道德学问之巅,寂寞深深。
人类的很多文明创造,似乎都是为了排解人类的寂寞。作为个体的人,一生中的很多活动,也是为了把自己从寂寞中解救出来。于是,就有了家国,就有了社会,就有了族群,就有了团体,就有了朋友,就有了圈子。
这一切包裹我们,使我们隔绝世界的寒凉,感受人间的温暖,并且,在这个危机四伏尔虞我诈的世界上,通过对族群的认同,获得安全感。
但是,有一种寂寞,却是人性完美的象征,只有完美的人性,才能拥有这种寂寞,才配享受这种寂寞。
《论语·宪问》:
子曰:“莫我知也夫!”
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当孔子感慨:“没有人了解我啊”时,好像有一丝寂寞,其实是大欣喜。
子贡看到了老师的寂寞,但他没有看到这种寂寞背后的欣喜。
其实,“莫我知也”者,不是遗憾之言,而是得意之言。为什么?因为“知我者其天乎!”
一个人,假如上达天命,下行天道,履行自身的人间使命,完成自我的人格塑造,此种境界之上,只有与天地晤对了。
只能与天地晤对,当然有寂寞。
能与天地晤对,则是人生的大境界!
孔子知天,天知孔子。
《孟子·万章下》: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喔!一个人,放眼天下都找不到对等的友者时,这是何等的寂寞!又是何等孤绝的境界!
何人能攀登如此绝顶,背负青天,莫之夭阏;俯视人寰,满眼慈悲?
他是人间的圣者。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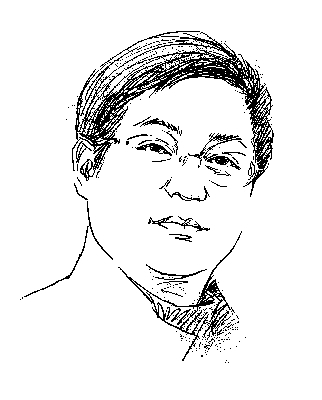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