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絮轻扬,乃自然现象。轻扬,是为了飞越关山去传宗接代。这与轻薄、不自重,无涉。
历代文人墨客,对杨柳轻扬这一自然现象,所付诸的文字数不胜数。其中也有不少人,只注意到了它随风飘扬的那一面,以为它不稳重没分量,而忽略了它为生存所付出的牺牲精神和不懈努力。
人世间的诸多事物,也有类似现象。
人对事物的第一印象一般都并不可靠。所谓,一眼便看透你了之类的结语,往往会把事物的本质搞偏或颠倒。就如把杨花柳絮硬是与轻薄女子等同起来,是有失公允的。所谓水性杨花这一类比喻,与事物的本性往往并无自然联系。
五一节携妻女赴北京北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郊游,不料与纷纷扬扬的柳絮照了个对面。此时,野风四起,轻扬的柳絮雪花般飞舞起来,热情与你亲密接触。对此,人们当然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温和地面对它突如其来的亲热,用手抓得一粒,细细看,掂量掂量,而后微笑着重又放回风中去。有的人,则显得很反感很无奈,连连躲避并大叫:“真烦人!烦死人了!”是啊,譬如人家美少女,穿戴时尚,乌发飘动,是一道流动中的风景,而柳絮一这么‘折腾’,还有什么好心情而言呢?这是事物的一面。
而事物的另一面,是我们少了一些宽容之心,也忽略了柳絮轻扬的初衷。柳絮,不是因为淘气而颠狂,人家是为了传宗接代嘛,并非小事。何况,它们的轻扬,时间也很短,不是常年累月总是来缠着你。按着自然界的生存规律来行事,何错之有呢?
问题在于,我们这些现代人,尤其城市人,太过骄横、太过自我、太过挑剔,容忍度极浅,动不动大加杀伐。按理,飘一点杨花柳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不至于那么厌烦,那么口出不逊吧。更有些城市,干脆把杨树一律砍掉让它销声匿迹,给柳树注射什么不孕剂等等,好不冷酷,好不绝情。然而,我们忘记了自己也是自然人,我们的行为,有时也不合乎生存规律,或有损于其它生物的日常生活。它们也不是不厌烦我们,但人家比我们显得大度、宽厚。
我们对自然之物,太过亲疏有别,冷暖不一。我们一边诅咒着杨花柳絮,一边去赞美同样乱飞的银杏叶,口中还念念有词:“吹落黄花遍地金”。我们可以让熊猫住豪宅、出入有专机,而对兔子却冷漠无情,吃肉剥皮。更令人唏嘘的是,这种价值观和好恶情绪,不是基于真善美的基础上,而是出于,顺眼不顺眼,好玩儿不好玩儿,或者,会不会顺从,会不会讨你欢心这个极单一的理念之上。譬如,宠物狗,何其得宠?人对它们的宠爱,有时优于亲人。又譬如,我们夸耀牡丹花为国色天香,而对迎春和二月兰,则贬褒不一。我们总是喜欢为万物也分个等级,排个座次什么的,显得十分俗气,十分浅薄。这显然是一种病态心理。
柳絮是什么?是柳树的种子,被白色绒毛所拥裹着的种子。每当四月五月,它便飞向天地间任何地方,十分悲壮地去完成它的使命。民间有“沙里栽杨泥里柳”之说。杨柳生性质朴,对于生存环境不甚挑剔,沙里泥里都可活,属于百姓之物,寒门之物。我们不该责罚它,轻蔑它。
诗圣杜甫有很深的同情心和普世价值观。然他也有失误和持偏见的时候。他有这样的诗句:“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苏轼却不一样,他说柳絮的好话:“梨花淡白柳深情,柳絮飞时花满城。”他把满天的柳絮和满城的花连起来写,成为美好事物的象征。南朝庾肩吾则写:“桃红柳絮白,照日复随风。”他把柳絮和桃花当作新春的信使来描摹。可见,人世间的一切事物,给人的感应也是千差万别的。
童年的时候,看轻扬的柳絮看得上瘾,聚精会神目不转睛,惟恐看丢了它们。羡慕它们能在天上自由自在地游荡,也为它们的未来忧心:不晓得它们远飞天涯,可否还能找回自己的家?
这样看着看着脖子梗了,脑袋不能转动,才吓出一身冷汗来。母亲一边骂我傻,一边用热毛巾给我搓揉。我就问母亲,它们终究都飞到哪里去了?离家出走,会不会饿死?母亲说,不会,它们的妈妈给它们带足了干粮。或许,你追看的那一个,明年春天就在我们的小河边长成了小树,就看你还认不认出它来?
于是我安心,安心在于它们不会饿死。在这样一种远虑近忧中,慢慢进入了梦乡。
人太明白了,也无趣。明白了柳絮轻扬是自然属性而已的时候,遐想空间少了,柳絮的神性也没了。柳絮轻扬究为何往,那种美丽的无知和童趣再不会有了,心中便生出一些空洞来。像山水画面上的空白处,永远地空留在那里。
查干 蒙古族,1940年生于内蒙古扎鲁特旗嘎海吐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灵魂家园》等多部诗集。亦有散文诗、散文等散见于全国报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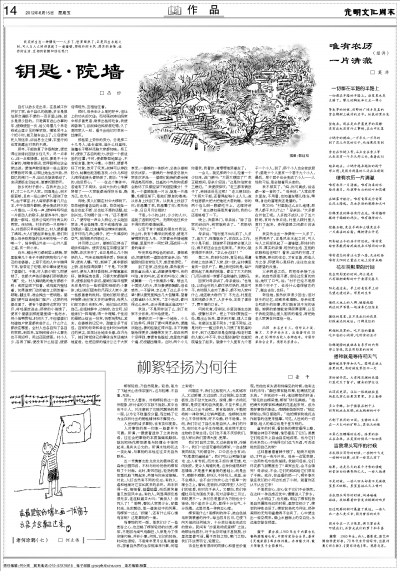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