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夫妻朝夕相处二十多年,彼此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把心里所要说的话,不用嘴巴地说出去。所谓心心相印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所谓貌合神离说的也是这么一回事。事物的两个极端往往就是这么相交相联的。
春节刚过,妻子便开始失眠,清明节前后达到高峰期。
算起来,春节离清明节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么一段时间里,妻子失眠的变化是惊人的。先是上半夜睡一觉,一觉睡醒就不能再睡觉了,大睁两眼等候着天亮。而后是整夜不能睡觉,吃安眠药也不起任何作用。好像清明节是一个分水岭。清明节过后,妻子改成上半夜不能睡觉,下半夜睡觉。再而后妻子的睡眠就渐渐地恢复正常了。妻子的失眠,每年发作一次,每一次发作前后要得三个月时间。周而复始。跌宕起伏。周期性的。季节性的。
妻子不知道失眠的原因,去市人民医院看医生。医生说,春天是一个特别的季节,一部分人容易犯困,一部分人容易失眠。犯困的人,就要想办法刺激大脑的兴奋。失眠的人,就要想办法抑制大脑的兴奋。怎样想办法抑制大脑的兴奋呢?比如说,晚上少看电视,少看小说书,少胡思乱想,多做家务,多散散步,多听音乐,越是枯燥无味的音乐,越是不喜欢听的音乐,你就越是去听。其目的就是要听觉疲劳,神经疲劳,身心疲劳,从而抑制兴奋,顺利地抵达温柔的梦乡。医生说,睡觉前可以拿热水泡脚,在热水里适量地加几味中草药,泡过脚接着按摩脚心,脚心的穴位对应着人的整个身体,不断地搓揉脚心,就能睡好觉。妻子说,你说的是中医,中药疗效慢,有没有什么西药?医生说,治疗失眠没有特效药物,实在睡不着觉,就吃安眠药。妻子从来没吃过安眠药,产生不少惊恐的联想。妻子两眼恐惧地睁大,战战兢兢地问,一次吃多少片,不会出事吧?医生说,吃一片不够吃两片,吃两片不够吃三片,最多一次不能超过吃六片,超过这个剂量,你第二天早上醒不过来,就不能怪我没有说清楚了。
治病要早,吃药要跑。春节一过,妻子跑一趟医院,开一瓶安眠药回家,就开始调整生活习惯了。比如说,妻子过去喜欢晚上看电视连续剧。古装戏,言情剧,谍战片,妻子像一个好胃口的食客,不偏食,不忌口,哪一种类型的电视剧都能看。现在妻子坚决地不看电视,恶狠狠地连电视机的电源插头都拔掉了。妻子的这一举动告诉我,她晚上不看电视,我晚上也不能看电视。妻子照着医生开出来的药方,去大药房抓回不少泡脚的中草药,还专门从超市买回一只泡脚的木盆。晚上烧刷洗弄后,别的什么事都不干,烧上一木盆热水,中草药加入其中,浸泡数分钟后,妻子就把一双脚丫放进热水里。妻子一边洗脚,一边听音乐。一只MP3是闺女淘汰下来的,一副耳塞是新买的。闺女上大学不在家,妻子和我都不会从网络上下载音乐,去找同事帮忙。这位女同事比我家闺女大不了几岁,也是个“80后”孩子。同事问妻子,你喜欢什么歌曲?妻子说,你应该问我不喜欢什么歌曲。同事说,你不喜欢的歌曲下载干什么?妻子说,我治病。妻子跟同事说出医生的交代,要听最不喜欢的歌曲,治疗失眠的毛病。同事问,那你说你不喜欢什么歌曲?同事这么一问,真把妻子问住了。是呀,我不喜欢什么歌曲呢?妻子努力回忆这些年凌乱而无序的听歌经验,竟然说不出喜欢什么样的歌曲,也就说不出不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妻子反过头来问同事,你说你不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同事是个爱听音乐的女孩子,整天耳朵里塞上耳麦,不时地跟着音乐节奏摇头晃脑的,一副陶醉其中的样子。惯性思维与逆向思维相遇有一些别扭。同事想一想,能说出喜欢谁的歌曲,一时半会儿的也想不起不喜欢谁的歌曲。
妻子决断说,你给我下载周杰伦。
妻子想起前些年,周杰伦火红时,闺女上初中。有一天,妻子下班回家,看见闺女在客厅,头上包裹一条丝巾,一边手舞足蹈地耍弄着两根筷子,一边“嘿嘿哈哈”地哼唱着。两根筷子中间用一段线绳连接着。闺女的样子很像一个疯丫头,装神弄鬼地跳大神。妻子吓出一身冷汗,急忙问闺女,你这是干什么呢?闺女说,班级“十一”唱歌,我在练习周杰伦的《双节棍》。这是妻子第一次听说周杰伦的名字。闺女身边摆放着一台复读机,周杰伦的歌曲就是从那里播放出来的。当时妻子不明白,这个名叫周杰伦的港台歌星,干吗哇里哇啦地不去好好吐词,干嘛又蹦又跳地不去好好唱歌。我们这些60年代出生的人不喜欢周杰伦是正常的,就像80年代出生的孩子喜欢周杰伦是正常的一样。关键是妻子不应该在同事面前表露出不喜欢。同事说,阿姨,我给你下载几首红歌吧。所谓红歌,就是几十年前流行的经典老歌。妻子说,那你给我下载几首,这些歌曲我喜欢听。这个时候,妻子已经忘记下载歌曲的真实目的。妻子回家一听,不是她听到过的红歌,而是网络版的红歌,是对经典老歌的篡改与解构。一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里,填写着这样的歌词:“革命军人个个爱老婆,你要我要哪有那么多,好好干活一人发一个,不好好干活发个老太婆。”……直到这时,妻子才知道同事用这种软绵绵的方式,回敬了她不喜欢周杰伦。
妻子自己想办法,找出闺女淘汰的复读机,听英语磁带。这样耳机传进耳朵里的就是稀奇古怪的语调、连一句都听不懂的英语课本了。
这之后一连好多天晚上,妻子都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面对没有画面的电视机荧屏,一边泡脚一边听复读机。有耳塞阻拦着,复读机播放的英语,我一句听不见,倒是随着水蒸气散发出来的中药味,四处弥漫,无孔不入,我家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里都充满浓郁的中药味。妻子一副安闲的神态,倒像十分喜欢中草药的气味,倒像十分喜欢复读机里的英语。妻子泡脚能持续一个多小时,暖瓶装满开水摆放在手边,木盆里水温下降,就加一些开水。开水一冲,淡下来的中草药气味又一次升华开来。我讨厌中草药气味,只好躲进书房里,紧紧地关上门,看一看书,或提早睡觉。妻子失眠期间,她睡卧室,我睡书房。这么一来,妻子失眠不用影响我休息,她失眠也就心安理得了。
有一天早上,妻子说她从昨天晚上开始服用安眠药了。也就是说,不看电视、中草药泡脚、听枯燥无味的英语,都没能改善她的睡眠。我问,你一次吃几片安眠药。妻子说,我吃一片。我问,效果怎么样?妻子说,一点效果都没有。这段时间妻子失眠最厉害。我说,那你今晚就莫吃安眠药了。药物毕竟是药物,吃多对身体不好。妻子说,我夜里睡不着觉,对身体不是更不好?我说,吃药没有效果还吃干什么?妻子说,我加大剂量。
妻子在失眠的这些天里,精神萎顿,脾气暴躁,像是提前走进更年期,每天无精打采地过日子,疲于应付工作,疲于应付家务,除此什么都不去做,什么都不能去做。妻子白天两眼迷迷糊糊地睁不开,像是随时随地都能睡着觉,到晚上两眼发亮放光,像是服用过兴奋剂,一点困倦的意思都不见。我想改变妻子的这种状况,却时时觉得无能为力。我出主意说,我俩利用双休日找一个地方,短途旅游一两天,换一换环境,散一散心,怎么样?妻子说,我蔫头耷脑地在家能活着就算不错了,哪里还有精力去旅游呀?是呀,出门旅游要有一副好心情,妻子这样怎么想去旅游呢?在妻子眼里,一个天是黑色的,一个地是黑色的,哪里还有一处光亮所在。我的原则是,妻子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去招惹她,也不敢去招惹她。
失眠如白蚁溃堤,任何人的坚毅意志都难以抵挡失眠的侵袭。
这一天晚上,妻子半夜三更喊醒我,说你过来跟我一起睡在卧室里。半夜里,灯光下,妻子的表情很复杂,有那么一丝兴奋,有那么一丝焦虑,有那么一丝超脱,有那么一丝恐惧。妻子说,今天晚上,我吃下去七片安眠药,你得看着我睡觉,万一早上我醒不过来,你送我去医院。我“扑棱”一下从床上坐起来问,你干吗一次吃这么多片安眠药?妻子说,昨晚我吃六片安眠药都没能睡着觉,你说今天晚上我该吃几片安眠药?我惊恐起来,困意“哗啦”一下消失去。我说,现在就送你去医院。妻子说,现在就去医院我还吃这些安眠药干什么?这一刻我在心里痛恨妻子,痛恨她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我质问她说,你现在的生命不是属于你一个人的,也属于我跟女儿,你怎能这样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妻子说,是安眠药拿我的生命开玩笑,我一下吃六片都睡不着觉,这药还叫安眠药吗?我问妻子,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是袖手旁观不问你的事,还是立刻把你送进医院里灌肠洗胃?妻子说,你就是送我去医院,也要和我睡一觉吧?这时候,妻子对睡觉的渴望,大于对生命的渴望,大于来自死亡的威胁。
我心里有数,七片安眠药暂时应该不会危及妻子的生命。我打定主意,一旦妻子睡着,一旦我喊她不理我,我就打120电话喊急救车。
妻子睡在卧室的床上,我坐在卧室的床头。卧室的门外黑咕隆咚的。卧室的窗外黑咕隆咚的。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俩。好像我们俩只存在于一处孤岛上。妻子说,我们家的存折密码你该记得吧?我问,我要记得存折密码干什么呀?妻子说,万一我去医院住院,你拿不出来钱怎么办?我敷衍妻子说,你放心,我记得。妻子喜欢去银行,我们家的一点余钱都是她去银行办理存储手续的。妻子说,你骗我,你一张存折的密码都不记得。妻子爬起床,拿笔拿纸,一笔一笔记下来。妻子掌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每年除去家里的吃喝花销,除去女儿上学的学费生活费,多少剩余一点钱,就已经很满足了。妻子是那种很容易得到满足的女人,不是那种奢望大富大贵的女人。
这一天晚上,妻子交代过存折密码,接着交代我第二件事情。妻子问,我那两件金银首饰,你该知道我放在哪个地方吧?我说,就算你住院总用不着我去典当金银首饰吧?妻子说,万一我去医院醒不过来怎么办?我心里猛然一“咯噔”。妻子希望吃安眠药好好地睡一觉,却又担心药力发作睡着醒不过来。妻子活得也太沉重了。我劝慰妻子说,你就少胡思乱想,安心地睡一觉吧?这个时候,我不痛恨妻子,我同情妻子,我希望妻子真的能安安稳稳地睡一觉。妻子说,金银首饰包裹在一只塑料袋子里,塞在厨房的碗橱子里面。我不解地问妻子,金银首饰干吗塞在那种地方呢?妻子说,这样为了防止贼进屋,放在床头柜,放在抽屉里,放在箱子里,小偷进来不是一找一个准?
妻子不怎么喜欢金银首饰,或者说没有经济条件去喜欢金银首饰。一对戒指,是我们结婚后父母从老家送过来的,一条白金项链是我们结婚二十周年,我送给她的纪念礼物。人进中年,我们身边这个年岁的同学朋友闹离婚的层出不穷。妻子有一种危机感,说你得给我买一条白金项链。套用一句文词来说,白金项链象征着纯洁的爱情,妻子买一条戴在脖子上,像是挂一条婚姻的护身符,图一个吉利。我说,脖子上戴着白金项链去离婚的女人多的是。妻子说,脖子上戴着项链总比脖子上空荡荡地去离婚少吃亏一点吧?妻子认准上海老凤祥黄金店,我们这座城市当年没开分店,我们俩专门去一趟省城。我记得当年白金价格是四百零四块钱一克,妻子挑选的一条白金项链不足二千块钱。一枚戒指妻子没戴过几回,一条白金项链妻子也没戴过几回。后来我才知道,项链是要配坠子一起佩戴的,一条光秃秃的项链不美观,戴起来也不方便。我问妻子,要不要配一个项链坠子。妻子说,不配!没有坠子的项链就不是项链了?我知道不是妻子舍不得花钱买坠子,而是妻子真的没把一个坠子放在心里边。
夜色渐渐地白亮微明起来,有公鸡的报晓声从远处依稀传来,时断时续的像是一种久远的乡村回忆。我跟妻子说,你再不睡觉的话,就天亮啦。妻子说,我俩说一说话,不比睡觉值得吗?有好多年我俩都没有在一起说过这么多话了。一对夫妻朝夕相处二十多年,彼此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把心里所要说的话,不用嘴巴地说出去。所谓心心相印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所谓貌合神离说的也是这么一回事。事物的两个极端往往就是这么相交相联的。妻子说,我还要跟你说一件事。妻子两眼放光,一脸兴奋与幸福,一丝困倦都没有。我说,只要你不想睡觉,只要你吃下去的安眠药不见药力,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这个时候,我也是一点困意都没有。妻子问,你可记得当初我俩谈恋爱的时候,我说我俩脾气不适合算了吧,后来我俩又接着谈,这一谈我就嫁给了你,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我说,二十多年过去,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我怎么会记得住呀,再说当年谈恋爱,你是主动,我是被动,你说谈我俩就谈,你说不谈,我俩就不谈。妻子笑起来说,你就那么好讲话吗?
妻子问,你可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俩沿着铁路行走,我不记得我俩说什么事说岔了,我哭起来,你慌忙陪不是,我掏出一条手帕擦眼泪、擦鼻涕,擦过眼泪鼻涕,我伸手把手帕扔在铁路边,当时我俩正好走在一座涵洞的桥上,手帕掉进桥下面。你问我,好好的一条手帕干吗要扔掉它。我说,手帕脏,我不想要了。就是扔下手帕后,我提出跟你分手。你一句话没说,就表示默认了。第二天,你找到我,还我给你的几样东西,有两本书,一只水晶球,几封信,其中就有我前一天晚上扔下铁路桥的手帕。你说,手帕是因为跟你生气扔下的,今天早上你去捡回来洗干净交还我。就是你的这一举动打动我。我脾气不好,你是我遇见的第一个能包容我坏脾气的男孩子,我不能没有你。
天亮了,妻子起床做早饭。早饭过后,我要去上班,她也要去上班。我说,我下楼去买早点,你躺在床上静养一会吧。妻子说,今天早饭我一定要亲手做,我要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做早饭与尽责任有什么关联呢?妻子执意要这样做,我不好去阻拦。我起床去卫生间刷牙洗脸。妻子去厨房叮叮当当做早饭。油炸馍,煎鸡蛋,冲牛奶,妻子一小会儿就把这三样早饭准备好,端进客厅的餐桌上。我坐在客厅里吃饭,妻子说去卧室叠被子。我吃过早饭,见妻子在卧室还没出来,就喊一声,你吃饭吧。妻子不搭理我,我赶紧去卧室,妻子躺在床上,盖着被子,和衣睡着了。看来是安眠药的药力发作了。
床头柜上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不要叫醒我,请让我睡一会儿!
曹多勇
1962年生。在各大刊物发表多部中、短篇小说。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安徽省文学院专业作家。现居安徽合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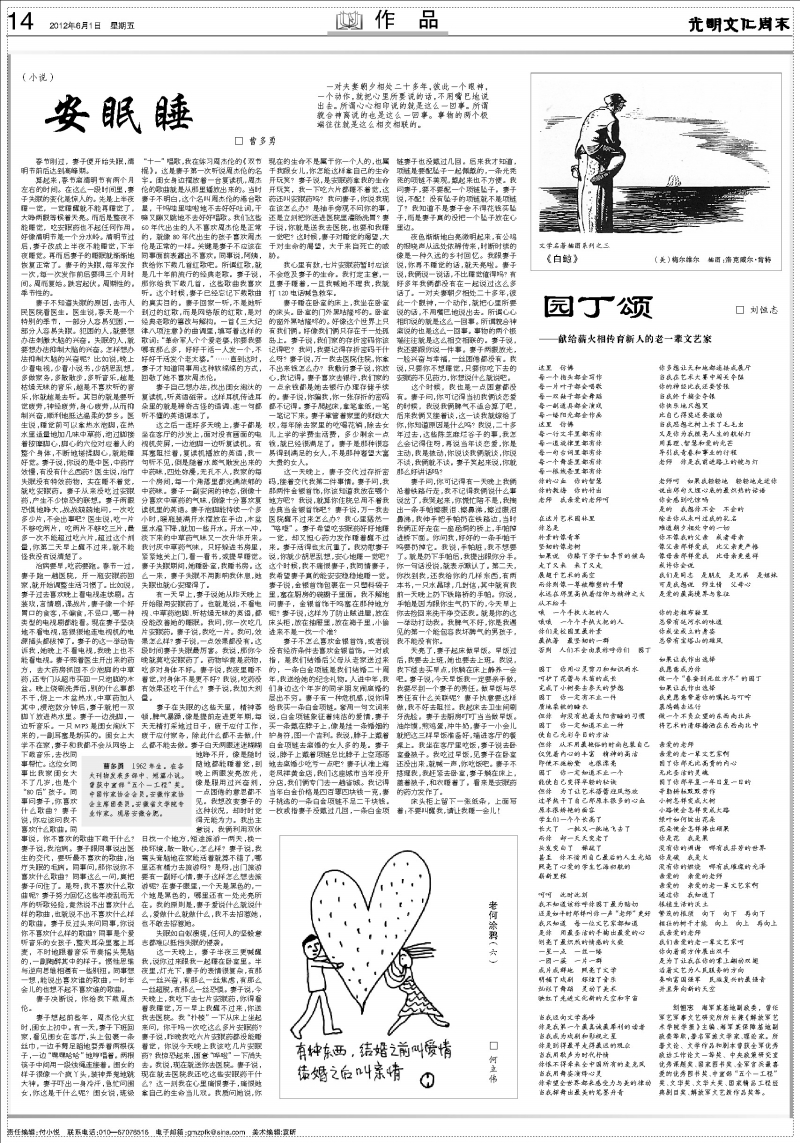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