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来,我曾五次进藏,三次抵达阿里。在阿期间,一次次被土生土长的阿里人、边防军人、在藏干部、援藏干部所感动,他们在喜马拉雅山和冈底斯山之间的荒漠、雪原、戈壁之上,奉献着青春、年华、生命,甚至子孙。
有人对我说,毕淑敏眼中的阿里是三十年前的阿里,马丽华眼中的阿里是二十年前的阿里,希望你写出当下的阿里。我不知道能否写出令读者满意的阿里,令自己不汗颜的作品。我只知道,此刻,打开我的回望阿里之门,阿里故事,像冰瀑布一样,逶迤而来。
杜文娟 女,大学文化。著有长篇小说《走向珠穆朗玛》,小说集《有梦相约》等。鲁迅文学院十四届高研班学员。两年前,受中国作家协会派遣,作为首批定点深入生活作家,赴西藏阿里深入生活。现居陕西安康。
阿里的汽车兵
1984年,十八岁的张良善,从山清水秀的陕西安康来到新疆叶城,在步兵连当了一名炊事员,每天做40个人的饭,外加喂8头猪,10头驴。
在新藏公路零公里处,立着一块巨大的牌子,上面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走上高原走向阿里。牌子周围总是集聚着车辆和长途汽车司机,有时候,部队的汽车兵也参与其中,聊得最多的是新藏公路上的奇闻趣事。
回到连队,张良善主动请缨,到汽车营当驾驶员,连长点个头,他就走了。
第一次上高原,自然有师傅陪着,穿行在大片大片的棉田中间,粉红色的花朵铺天盖地,迎风招展,叶城的天空瓜果飘香,南疆的大地牛肥马壮。师傅见他乐滋滋的样子,淡淡一笑,什么也不说。
树木逐渐稀少,河流逐渐变窄,雪山逐渐凸显,喜悦逐渐恬淡。库地大阪、麻扎大阪、小黑卡、大黑卡、康西瓦、奇台大阪、死人沟、界山大阪、红土大阪、狮泉河大阪,一路而行,终于到了阿里军分区所在地狮泉河镇,快要蹦出胸口的心脏终于平静下来。
到了狮泉河镇,师傅把他领到烈士陵园,献上哈达,点燃香烟,洒上白酒。并对他说,新藏公路上,也牺牲过我们的战友。
第一次上高原的军人,都会到康西瓦烈士陵园和狮泉河烈士陵园拜谒,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
从阿里返回叶城的路上,张良善陷入了沉思。要求到汽车营的时候,有人就对他说过,汽车兵刚开始都热情高涨,体会了翻车、死亡、饿得头晕眼花,就乐不起来了,三个月以后,有的垂头丧气换了岗位,有的干脆复员,一走了之。
回步兵连,还是当汽车兵?恐惧在周身蔓延,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师傅握紧方向盘,专心开车,他则把目光投向路边。积雪少一些的地方,横七竖八地散落着动物的骨头,在阳光的照耀下,发出莹白的光芒。汽车飞驰,路边的骨头没有减少,反而增多,公路延伸到哪里,白骨就铺展到哪里。
不会是人的骨头吧?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就吓出一身冷汗。
当汽车兵没过多久,他就随师傅一道去札达县山岗边防连,接运烈士周治国的遗体。
周治国生前是山岗边防连的一名报务员,盛夏的一天,连队巡逻来到帕里河,雪水如脱缰的野马,从山上急泻而下。周治国怕电台被溅起的水花淋湿,就从马背上下来,把报话机紧紧抱在怀中,不料被激流连人带马卷入漩涡。牺牲的时候,他喊了一声——保护电台。三天前,他才过二十岁生日。
从山岗边防连出发的时候,天色已晚,下小子大阪陡坡的时候,发动机突然熄火,车灯不亮,手电筒没电,打火机打不着。借着月光,打开车头盖摸索着检查,一切正常。师傅和他对望一眼,同时爬上车厢,周治国的遗体包裹着白布,用绳子捆绑在木板上。由于颠簸厉害,此时的周治国连同木板一起搭在车厢围栏上,稍微再颠簸,就会掉下车去。
两人一边捆扎好尸体和木板,一边念念有词。治国,好兄弟,不会丢下你不管,好好的,咱们一起回家。烧了纸钱,洒上酒,说了更多的好话。
再启动,发动机轰鸣,车灯明亮,刚才的一切似乎是一场梦。
1987年10月,向阿里运送物资,出发前,他把自己车上备用的配件借给了另一名驾驶员,返回叶城经过多玛130公里,距红柳滩230公里的无人区时,车上的齿轮坏掉,没有配件,只好让副驾驶搭乘另外一辆下山车取配件,自己留下来看车。常年奔波在新藏线上的官兵,都知道这样一句口头禅,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红柳滩到多玛。
一等就是15天。
临别时战友给他留下两天的干粮,干粮吃完以后,只能到十几公里外的小湖边,用铁锹打鱼,然后用喷灯和高压锅将鱼煮熟,高原鱼皮有筷子那么厚,没有调料,难以下咽。被困的十几天里,每天的事就是打鱼、煮鱼、吃鱼、睡觉。后来几天看见鱼,就恶心呕吐。救援的战友看见黑瘦的他和一大堆鱼骨头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1991年4月,叶城的石榴花,红似火艳如霞,张良善踏上雪域昆仑,担负着运送17名新战士到普兰哨所的任务。途中遇到雪崩,把前面200米长的路堵死了。他就带着副驾驶挖雪开路。为了安全,他始终在前面开道,副驾驶紧跟其后。挖一段要吼几声,试探是否继续雪崩。
新战士要求替换他俩,张良善不同意,初上阿里的人,体力消耗过大容易导致休克。他也开始头疼,用绳子勒紧脑袋,坚持往前开道。两名新战士自称身体素质好,夺过铁锹,挖了不到五分钟,就瘫倒在地。
忽然,再次发生雪崩,他被雪块掩埋,副驾驶带着17名新兵把他从雪堆里扒了出来。新战士第一次见识这种情景,吓得目瞪口呆。大伙把剩下的两个馕饼让给他吃,他把两个馕饼分成小块,强迫新兵一一吃下,并告诫他们,驻守边防,首先要保住性命。
连队来了救援分队,新战士激动地大声喊叫,老班长,我们有救了。17名新战士哭成一团。他也控制不住激动,泪流满面。只是,背对着新战士,不让他们看见。
这个时候,他有了一位聪慧灵秀的妻子,来自陕西老家的何桂丽。妻子像众多的军嫂一样,住在叶城留守处,一次次送走精神焕发的丈夫,一次次迎回披星戴月的夫君。
1992年10月,即将分娩的何桂丽因重感冒住进医院。当时,向阿里运送油罐的车已经装好,张良善按时出发。
车队刚到红柳滩,留守处就把电话打到兵站,让他连夜赶回。车到狮泉河镇,留守处把电话打到阿里军分区,说他妻子即将分娩,难产。
卸完油,连夜开车往山下赶。到了多玛兵站,留守处的电话追到兵站,问他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他哽咽着说,都要保,都要保,实在不行,就保大人。
他驾着车就跑,5天的路程,他用了1天1夜就赶到了。回到叶城,孩子已经夭折,妻子因为大出血生命垂危。他在病床前守了15天。妻子弥留之际对他说,以后,跑山上的路,要慢一些。
仰望昆仑的女人
“请你在高原为我采一朵雪莲,让我吻一吻那圣洁的花瓣。请你在高原为我许下一个心愿,让我能够望见那梦中的雪山。”保玉琼炖好排骨汤,走出房间,为院子里的辣椒浇水,然后走到一株石榴旁,仰望昆仑,轻轻吟唱。这首网络歌曲在叶城十分流行,几乎每位军嫂都耳熟能详。
晚风轻轻吹拂,石榴飘溢着清香,彩霞在天边无限美好。保玉琼走进厨房,闻到了排骨汤变凉的气息。摸出两对碗碟,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擦拭一下灶台,用的却是洗碗布。在原地转了两圈,终于想起来要干什么。
举起锅铲,敲击暖气管,隔壁的军嫂发出了同样的敲击声,说明邻居的汽车兵丈夫也没有回来。再一次走到石榴树旁,昆仑已经模糊,呈现出黛色的模样。借着月光,走到新藏公路零公里处,徘徊良久,依然不见丈夫的影子。
按照惯例,车队最迟下午四点前就能返回营区。可是,月亮升起来了,还是不见车队的影子。军嫂们纷纷走出家门,集聚在一起,急切地打听车队的消息。新藏公路上没有手机信号,根本无法知道车队的情况。
第二天,没有车队的消息。
第三天,没有车队的消息。
第四天,军嫂们表情严肃,交头接耳。
有人说可能遇到泥石流,车队无法前行。有人说可能遇上暴风雪,车队受阻。有人说,可能到更远的边防哨所送物资去了。
第五天中午,终于传来了消息,人车安全,男人们正在库地沟修路。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保玉琼一把抱住石榴树,一只红艳艳的石榴落在胸脯上,她却毫无察觉,不管不顾地失声痛哭,鸟儿惊慌而逃,发出迷茫的叫声。
丈夫回来以后,轻描淡写地告诉她,车队走到库地沟时,突然遇到洪水,公路被冲毁,连续几天都住在四星级的东风宾馆里。后来,保玉琼才知道,所谓四星级东风宾馆,就是四个轮子的东风汽车车厢。
同保玉琼一样,邻居们全是军嫂。阿里驻军家属,从全国各地来到南疆,随军不随队,居住在千里之外的叶城。女人村里的军嫂们,大部分没有走过新藏线,没有到过藏北高原的边防哨所,但她们总是有意无意地仰望昆仑,想象昆仑那边的阿里,思念阿里高原上的丈夫。
景慧慧,是一个特例。
那个时候,景慧慧还是一位纯情少女。大学毕业那一年,她决定到高原寻找自己的人生信仰。来到叶城,没有找到前往阿里的长途汽车,便搭上了开往阿里的军车。
在得知开车的汽车兵和自己是同龄人时,清秀的景慧慧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汽车兵皲裂的皮肤,沧桑的面容,使她一度怀疑这位老兵早过了而立之年。翻越界山大阪时,头疼脑胀,恶心呕吐,繁密肥硕的雪花,重重地落下来,加剧了她的高原反应。她愈加慌乱,心神不定,昏昏欲睡。
汽车兵递给她一片红景天,用温和的声音与她交谈,防止她一睡不起。好听的男中音,仿佛从遥远的家乡传来,又仿佛从苍天翩然而至。美丽的少女感到了清凉,说不清道不明的美好。
当她醒来的时候,漫天飞雪依然,却有丝丝缕缕的温暖。一件破旧军大衣不知什么时候披在她身上,老兵手握方向盘,专注驾驶,却在瑟瑟发抖。大雪阻断了道路,车队在界山大阪被困三天,景慧慧患上了肺水肿,到达狮泉河镇后,汽车兵把她送进了部队医疗站。三天以后,病情基本稳定。缝补好大衣腋下袖口的破洞,抱着油腻腻的军大衣,寻找它的主人,被告知车队已经出发,给一个遥远的边防连队补给物资去了。
两年以后,景慧慧辞掉了家乡优厚的工作,来到叶城,成为一名新娘,亲爱的夫君,正是军大衣的主人。
有个旅伴叫老龚
2009年7月,从拉萨前往阿里,搭乘丰田4500越野车,高原路,路难行,颠坏了我的戴尔笔记本电脑。2010年8月,从阿里返回拉萨,乘的也是越野车,防止电脑再坏,上车以前,将电脑用围巾和哈达包裹严实,随时抱在怀中。为了方便上下车,坐在车窗边。冷风吹得肩膀和腰身生痛。半夜时分,行至神山脚下,停车方便。女人躲在车尾方便,男人站在车的两边,就地解决问题。夜色黯淡,雪花纷飞,飘落在屁股上、脸上、头上,针刺一般,疼痛而冰凉。
快速方便完以后,发现坐在中间位置的男人还没有上车,一个念头突兀冒出,如果坐在中间位置,就少了寒冷。健步如飞,跨上车来,一屁股坐在中间位置,抱住电脑,假装睡觉。那个男人没有言语,只好坐在靠窗的位置。
天亮以后,车内气氛活跃起来,大家说说笑笑,互相打听对方哪方人士,何种职业。
被我抢了座位的男人说他是四川邛崃人,老婆在拉萨批发哈达。他在阿里承包了电信公司一个工程,没挣到几个钱,晚上他想睡在车上。
当天晚上在萨嘎县城住宿,住宿前要吃晚饭。小餐馆里只有几张桌子,不约而同,我和他坐在了同一张方桌上。他望了我一眼,没有说话,就点了三个炒菜。我有些纳闷,一晚上三十元钱的住宿费都掏不起,三盘菜,起码得上百元。如果他邀请我一起吃饭,不好推脱,但这钱就得我付。如果这样,走为上策。
屁股一抬,扭身去了另一家餐馆,十五元钱吃了一碗红彤彤的面条。第二天上车,我说昨晚的面条里,肯定放有地沟油,那颜色,好似六月艳阳天。男人接过话茬,大声骂了起来。妈拉个巴子,以为你跟我一起吃饭,点了三个菜,到处找不到你,害得我肚子撑得难受。
我说,你不是连住宿费都掏不起嘛。
男人靠近我,解开棕色棉袄扣子,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叠红色百元大钞。
我惊呼道,哇,你还真有钱啊。
他低声对我说,这只是两千元现金,我还有十万元钱在卡上。说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蓝色银行卡。
我觉得他是个单纯的男人,就跟他开玩笑,说自己有眼不识泰山,并问他怎么称呼。
他说,你就叫“老公”吧。
司机解释,这位老板姓龚,他想捡你便宜。
老龚发现我没有生气,就问我是哪里人,在阿里干什么工作。我说闲人一个,无业游民。
他说,你不像无业游民,听你说话,好像还有一点点文化,是不是阿里军分区司令的老婆,或者行署专员的老婆。
我说,如果我是他们老婆,肯定不会跟你挤一辆长途汽车,还受你欺负。
他说,那你是电视台的,或者老师。
见我没有答复,就说,可能你是干那个的。
我笑着问他,干什么的啊。
他说,说了你别生气。
我说,不会生气,你说吧。
他说,你是坐台小姐。
同车人喜眉笑眼,却不言声,我哈哈大笑。然后告诉他,你高抬我了,哪有我这种既不年轻,又不漂亮的坐台小姐。
他说,年轻漂亮的小姐都到内地大城市坐台去了,像你这种既不年轻,又不漂亮的女人才在阿里坐台。
我连声夸他有头脑,善思考。
车过拉孜县的时候,有了树木和绿色。他推开车窗,大声喊叫,妈拉个巴子,好压抑啊,老子两个月都没有看见树木和青稞地了。
我在拉萨下车,无意间看到一蓬开得正艳的粉红色玫瑰,和穿着裙子的女孩,愣怔了好长时间,才反应过来。真好啊,拉萨的花真娇艳,拉萨的女孩子正过夏天哩。
2011年春天,在拉萨的街上游荡,忽然想起老龚。到大昭寺附近的哈达批发市场寻找,的确见到一位邛崃哈达批发商店。三十多岁的女店主,用戒备的眼神和语气,问我为什么找她丈夫。我说去年从阿里乘同一辆车回拉萨,想看看他。女人不情愿的递给我一张名片。走出店铺,打他手机。电话那头的男人,非常热情,让我在原地等他。
五分钟以后,一个男人兴冲冲的来到我身边,也姓龚,但不是我要找的老龚。男人说,你要找的人可能在珠峰伟业商场批发哈达。
在珠峰伟业商场,果然见到了老龚的妻子,个头不高,但精明能干。我向老龚的妻子刚说自己是陕西人,女人就笑嘻嘻的说,知道,知道,老龚跟好多人都说起你,只知道你是陕西人,不知道你是干啥的,说你喜欢开玩笑。
老龚的妻子领我到他们租住的房间去参观,不大的房间,异常简陋,每月房租150元。一张床,一个破旧的电视机,一堆色彩缤纷的布条。女人白天在商场批发哈达,晚上边看电视,边用布条编成小工艺品,卖给游客。
女人告诉我,老龚还不到四十岁,名叫龚永波,自从2010年8月,从阿里回到拉萨,肾病加重,只能回四川邛崃治病,每周都去医院透析,在阿里挣到的十万元钱,花得只剩三万了。
打通老龚的电话,他说,没想到我会跟他联系,有人关心,会好受一些。
再后来,他经常在透析的时候打来电话,说自己对生死看得很淡,今天死跟明天死,没有什么区别。几十年里,最幸福的时光是在西藏度过的,千里迢迢到拉萨摆地摊,蹬三轮车,从一个农民,发展成一个小老板,都是西藏赐给他的福,一个人,有西藏的经历,死而无憾。
每次听到龚永波微弱的声音,辛酸之情油然而生。危难中的人,格外渴望慰藉,希望呵护和关心,向往温暖的手与他相握。
就像我八年间,五次进藏,三次抵达阿里的过程中,遇到危难,就很脆弱。渴望得到帮助,幻想有双大手,将我牵出迷茫,走向光鲜。
后来,渐渐明白,那双大手是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叫西藏。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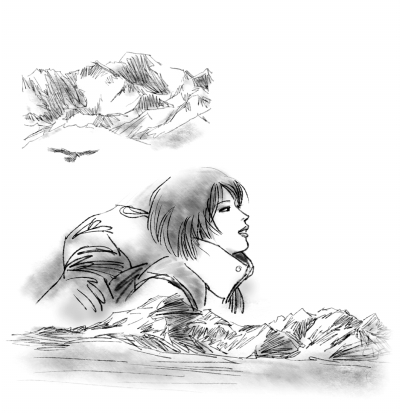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