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妈俩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抱着走。”那是她那一个时代,农村妇女的共有命运。然爹娘终生厮守,终生信任,终生和睦,共同生活了72年。
“哎,吃饭嘞——”
这拖长了尾音的喊声,常在伏天儿的晚饭时刻响起。
爹是一个“吃凉不管晌儿”的松心人,晚饭之前爱串门儿。娘就站在大门外边,向街的左右喊。
“哎”,是爹妈之间长期共许的,她对爹的称谓。
邻家也听出来了语音,催促:“别大沉屁股了,快回吧!”爹这才站起身,笑呵呵而归。
爹妈俩同一个“兔”属相,同一般大的年纪。爹的面孔红,妈的皮肤白。爹为生产队赶马车,妈在家忠心耿耿做九口人的饭。
妈是12岁时登我家门儿,“童养媳”。暴露了这个身份,您别以为俺家庭历史有问题:过去,不只大户人家,循照此例;穷苦人家也有。知根知底,上下连村的穷苦人家相准了,这家将早晚“脸朝外”的闺女打发走,少一个“吃饭”的“累赘”;那家添了一个早出力的“帮手”;并形成契约。俺们就属于后一种人家。
孩童时,即在同一口锅里淘饭,同一个屋檐下长大,感情自然会深厚。临到白了头发,爹妈在一块儿,让外人看,不单是夫妻,而更像兄妹、姐弟。一个脾气“轴”,一个性子“顺”,一辈子他俩却没闹出大意见。“夫妻相儿”挽在了一起,十分地夫唱妇随。
看多了的,爹赶大马车给生产队拉庄稼时的神态。那么多七股八杈的庄稼秸秆儿,那么高的秸秆儿垛,他码放得顺顺溜溜,不颠不撒。稳坐于车辕上边挥鞭杆儿,他乐乐呵呵。
看多了的,妈妈坐在香椿树下的板凳上,纳鞋底儿,搓麻线。一把锥子,一把剪,一绺儿麻,是她使用的材料和工具。一双鞋,千千线。她不时地将大号针蹭一蹭鬓角,然后一针一线地纳过去。鞋子做得结结实实。
父亲是一个独生子;父母却生育了我们四个弟兄,还有一个姊妹。他天生面相好,大耳,大耳垂儿,伸出10个手指,他还常以“九斗一簸”的指纹自诩。对于四个儿子相继跳出“白薯锅”,他将全部功劳归于自己。人傻实在;别人当面揶揄:“秧儿不济,结好瓜……”他竟听不出其中的味道来。
娘却不然。见爹乐癫了的形态,当着人面从不抢白。待邻人走了以后,慢条斯理地跟爹一人讲:“是儿女们个个儿争气……”
父亲口讷。母亲的评语仅四个字:拙嘴笨腮。并另有描摹:榆木脑袋。受人欺负时,他虽拳头攥紧,却只会喘粗气……
而娘会讲道理。她总讲:“说倒人,比打倒人强。”她用民谚的形式解说事理,一折折娓娓道来:“儿的生日,娘的苦日。”“宁使身子受苦,不使脊背儿受热。”“宁让家贫,别让路窄。”“宁给穷人一口,不给富人一斗。”“人给咱一根豆角,要还人一条黄瓜……”
父亲太过于老实,一辈子没主动与人争吵。有时,做儿女的都替他憋气,嫌他“窝囊”。然而,集体交给他的单独任务,任何时候生产队长都放心。晚年,他赶车给煤矿疗养院送补给品,米面、白糖、水果、糕点……凡吃食都有,而我家却连一把瓜子、花生都未见着。
老娘她终生恪守妇道,平素不串闲门儿。任何的飞短流长,进了我家的门,都会沉了底儿。而别人来家里借东西,凡是有的什物,即不吝惜。热心肠的娘,不但会让人拿走了针,还会将一绺儿线舍去。她常说给我们听:人张口容易,闭口难……
父母亲都行孝道。这一方面,在我的老家,有口皆碑,已是定评。对于我们的祖父母,父亲的进孝形式,是听话。从我记事起,就未见他有过“忤逆”。都一把年纪的人了,祖父母说啥还是啥。正所谓“乐其心,不违其志”是也。母亲在祖父母面前的表现,总是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样,从未见过她赌气,摔盆子摔碗儿。吃饭时,先给祖父母端上来;吃下去一碗,再盛上一碗。并不支使儿郎。
祖父母去世以后,年年的三十晚上,他俩先一通儿忙。并互相嘱告:给爹娘的烟带了没?酒装没装上?到坟前说个啥……直到爹嗫嚅而去方止。爹自墓地回来,才真正是大团圆坐下来的时刻。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抱着走。”这一句话,俺老娘讲过。那是她那一个时代,农村妇女的共有命运。然爹娘终生厮守,终生信任,终生和睦,共同生活了72年,——这一点,让我好生羡慕。
老爹识字不多。解放初,仅上过“扫盲班”。他能够背诵的,就两本书上的几句话。《三字经》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那开头儿的几句。《百家姓》中,他记准了的,是有我家姓氏:“熊纪舒屈、项祝董梁”,那一趟儿。
老娘呢,跟他比,这还不如。新社会“奖赏”给她的名字,“杨淑兰”仨字,她一个不识!
姑 家
她是背着“王董氏”的名字,离开人世的。血脉相传。尽管姑姑去了,但我也割舍不下那里的亲情、那个家庭里的温暖。
“姑舅亲,辈辈亲。砸断骨头,连着筋。”
祖父母生育了一儿一女。这名女儿,必然是我们的姑姑。
她嫁在距离我村8里路,向东去,平原上的一个中等村庄。村名“窦各庄”。
去她家,要翻过一道叫“老虎圈”的野山坡。一条羊肠小道。经过时,常看见野兔卧在路旁。人惊醒了它,它并不跑远,蹦跶了两下,站住,回过头向你张望。那意思,好像让你再逗一逗它玩儿。
年岁太小的时候,是爷爷领着认的门口儿。我认识路了,上学了,常在寒暑假两个假期里,背着书包带着作业本儿,独自前往。
我爱去姑姑家,不仅因为知道有血缘关系;更主要的,是她待我们弟兄好。
其中,“形而下”的因素,不容忽略:她家境比俺家强。
我们家,很少见到用整粮食喂鸡。奶奶、妈妈饲养鸡,是用剁碎了的野菜掺麸皮的混合饲料当食。鸡儿们,见不到精品。
而姑姑这里,却截然相反。“要吃蛋,粮食换。”她申明自己的主张。“咕、咕、咕咕……”,就见她端着少半瓢的玉米粒儿、好麦子,撒开来喂鸡。我看着都心疼。
在她家,我能吃几天的净米净面。尤其那从小菜园里水井旁边揪来的黄花,打卤,拌投过水的手擀面条,吃起来特别香。我再不用见着餐桌上的蒸白薯而发愁了。
小孩子馋。我喜好吃什么,姑姑都知道。她天天给我吃煮鸡蛋。将氽子舀进半氽水,插入炉口,放进两个鸡蛋,不一会儿,氽子就“咕嘟咕嘟”地烧开了。在我等得心急的时候,鸡蛋也熟了。姑姑将氽子里的水滗掉,又将鸡蛋放入了冷水碗儿,浸了浸,递给我手。
刚剥了壳的煮鸡蛋,还烫手,有一股蛋腥味儿。左右手倒替着,捏开了凝成亮瓷样的鸡蛋清,里边的蛋黄,金黄金黄,内心儿还有深红色,仿佛着了油彩,吃起来沙沙腻腻的,——香!
除了鸡蛋解馋,还有花生,还有核桃。也比我家里强。“谷黍上场 ,核桃满瓤。”暑假里,吃上鲜核桃。鲜核桃的仁儿,甜津津的,爽口。就是有一个缺点:砸开了青皮时,青皮的水儿太染手。两只手的手指、掌心染了浆,变成了黑色;斑斑点点,十天半月,洗不下去。
我们弟兄四个,都爱往姑姑家跑。有时单独,有时搭伴儿。
有一回,我就和哥哥一起去了。哥哥自小与我性格不同。他爱干净,自己的衣服自己洗;会揉搓板儿。还会使用针线,钉个扣儿,缝个补丁,都行。我娘常常夸他:“比拙媳妇儿都强!”而就在那一回,他使用针时将一根针弄断了。不知姑姑说了句什么,他起了急,赌气说:“弄折了你一根儿,我买一包去!”当时,都以为他说的是气话,结果他还真去了供销社,买回来了一包针。他将针递给了姑姑,就向外走了;姑姑急喊,急追,他竟连头也不回。追到村外,姑姑站在了地埂子上止步。我见她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儿,双眼闪着泪光……
我见到过,她和姑父一起回娘家时的一个情景。虽说我父亲为独子,但董氏家族叔伯弟兄很多;这些“舅爷儿”常与姑父开玩笑。我姑父这人,粗通文墨,然不擅言语,在众舅爷、众妗子面前,总是在话语上面吃亏。口齿灵俐的姑姑,自然会为他开脱、百般维护。姑父其人,身高体大,饭量也强。看他大碗连续端饭,能说会道的舅爷就看准了对象,即开始语言“轰炸”。这时刻,姑姑却不做过多袒护,而站到了众弟兄的阵线上,抿着笑口而说:“——老牛,全凭吃!”
一句话,引来了大家哈哈一笑。
记得姑姑生前,每年“清明”都回娘家给祖父母上坟。年轻时,由姑父骑自行车带着她;年老了,姑父蹬一辆小三轮车,送她来。晚年,她也和我母亲一样,自己走不动了,才不来上坟。
她是背着“王董氏”的名字,离开人世的。血脉相传。尽管姑姑去了,但我也割舍不下那里的亲情、那个家庭里的温暖。我几乎年年去看望年迈的姑父。我认为,看姑父,就是对姑姑最好的怀念。
丈母娘
我锦心绣口的乡亲们丰富了民间的谚语库,将老版本“实顶实”的歇后语,进行了修订,其新版句式为:“丈母娘疼姑爷——石顶腰!”这话把儿,留在了乡村,已至我胡子白。
“小兔崽子,给我出来!你拿唾沫儿沾媳妇……”
这个站在我家大门口的,四十几岁妇人,手抡一根葛针条,气力十足地一迭声叫骂。
骂语中,顺了口,不留神将我奶奶对我的昵称“二羔子”,也一块儿喊了出来,引得过街人和围观者一片笑。
此叫骂者,即是与我已私订终身、她大闺女的母亲。
那一场于门前突如其来的叫骂,惊吓得我胆小如鼠的父母不敢出屋。
我也于后院自己的小屋内胆怯。同时又觉得她骂的很对:我爹妈同龄,属“兔儿”,而我也属“兔儿”,不是“兔崽子”又是什么?再者,因为家穷,在谈情期间,未曾给她女儿买过任何物品,这不是用“唾沫儿沾媳妇”,又是什么?这般骂的实际,我一点儿不委屈。
论家庭,她家境比我家好。我内心早已经确定的岳父,是一名老工人,有比较高的工资收入,而其三儿三女都已在生产队挣上工分。年终结算,也能从生产队拿回钱来。而最要命的,辈份儿上不合,论乡亲,那骂上家门来的人,属“奶奶”一辈儿。
心中有这般顾忌,最初连怎么尊敬地称呼都成问题。
她家与我家不属于一个生产队,而居住距离却不足二百米。我去田间干活,若抄近路,从她门口过最近。可我有怕在先,常舍近求远,就为避开碰面。那一回不知为何转错了脑筋,经她门口,值夏天歇晌时分,街巷空无一人,正暗自庆幸之时,恰遇老人家从院里边出来。躲也躲不及,僵立稍顷,遂壮着胆前行。见面总要问候,遂省略了主语,问她“干啥去?”未听答音,却见弯腰低头;我正为之诧异,一块石头朝面门投来。惊慌失措地躲闪,那块石头砸在了我腰间的筐上,“嘭”地一声弹响之外,还有余音:“——你小兔崽子,往哪儿跑!”我被吓得魂飞魄散,掉过头来就跑,背筐里镰刀被甩丢在了大街上。
其后,口头文学有了新内容,我锦心绣口的乡亲们丰富了民间的谚语库,将老版本“实顶实”的歇后语,进行了修订,其新版句式为:“丈母娘疼姑爷——石顶腰!”
这话把儿,留在了乡村,已至我胡子白。
亲事已定,大局难回。岳父母就也只得顺应现实,允我登门认亲,下聘礼。按乡俗,备六盒礼:二筒儿茶、二条烟、二瓶酒、二斤糖、二十斤挂面,——上为双数。另有一块带肋骨的鲜猪肉,其意表示为母女骨肉相连,女儿离开了娘怀。
初次因亲事登门,改变称呼,太紧张。嗓子眼里滚出来的“爹”、“妈”二声,比蚊子盘旋展翅的声音还低。
答谢“姑爷”,我接受的赠礼是:一双白塑料底、灯芯绒面的松紧口鞋,一件中山装和一条“的确良”深色单裤。
自以为离其家门很近,用自行车步行接亲即可,不料岳母发脾气,以风俗古训制止。为求得岳母满意,这七十二拜之后的“一哆嗦”,即恳请我的堂叔帮助,动用了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手扶拖拉机”,迎娶新娘。
我的岳父母,是两种不同性格的人。岳父性情温和,天性善良,而外表懦弱,其为新中国第一代煤矿工人。他最精通的技艺,是将煤块儿和煤矸石,一眼分开。家里的事情,他不做主,下班休息在家时,只憋在屋子里面抽烟,或干一点儿零碎小事。他对岳母的要求,是保证他能够上好班,吃好饭,并将准备要带走的饭菜,装好饭盒。岳母的风格,则是雷厉风行;主持正义,性格刚强,不惧怕农村的强大势力。然而,对丈夫、对公婆,却又十分地贤淑。
岳母常年在生产队劳动。田间里的任何农事,从重体力的粗活儿,到菜田的精细技术,样样儿拿得起来。并且,干活儿麻利,起带动作用。
就因为她自尊心、集体事业心忒强,就看不惯别人偷懒。见别人出工不出力,干活儿泡蘑菇,她生气。有时,她锄地早到地边,还有数人在地中间缀着,便提锄插腰斥责,羞得他人赶紧加快了干活儿的速度。就她那样儿,比生产队长还操心。
就是由于离娘家门口近,我们有了儿子以后,为了不误上班,儿子刚出满月,即给岳母大人送去。从吃奶粉,到会吃鸡蛋黄儿,到学步,到上小学、中学,我们是将他全日制整托。只在工厂休息时间,我妻子才有半个小时的探望。我则是多凭写稿,换回营养费和交学费的钱。两位老人对待我儿子是真心疼爱,儿子生病了,老人家抱着去医院,是赶天赶地的急,扯心扯肺地痛。他学会骑摩托车了,老人家不放心,刚打着了火儿,就近身嘱咐:一路要多加小心……
老人家的过度疼爱,反而使父子感情疏远。学校在村中,儿子放学必由我家门口经过,遇休息日,我在大门口专等候他回家吃饭。我截留了几次之后,便不肯再来;后来发现,他是从我家的对面,别人家的房后胡同遁离。被我见着了,他的小书包紧贴着小屁股,呱呱地快跑,怕我留、怕我追……
儿子长大,接受了姥姥姥爷的品质:心地善良,而且正直。只是雷公脸儿的脾气,时常让我接受不了。他对二老的一片孝心,达到了我的愿望。
我见过许多次岳母在“自留地”里的劳动,她抡平筢打畦埂儿、挎斗箕撒麦籽,一直视她为强悍能干的榜样。然不经不由间,却也发现了她加快的衰老:头发变白、变稀了,腿脚也慢了;背一筐棒子秸,竟也显十分吃力……此时被我看见,免不住一阵心酸。
老人家的并发症先始于眼疾,双目白内障。我俩接她来我家调养。只要我在家,她不在一起坐,只独处一室的小天地,一个人默坐床沿儿。听客厅里我们大小人儿说话,她偶尔带着笑声,搭一两句言,那么仁义。我妻子每日早晨给她冲一碗鸡蛋汤,她接受;而再要提供其他类营养品,她却不允。她的神情,像是给我俩“添了累赘”似的,让我看着心伤。
她偶尔独自下楼,去县城的街上换换心情。我就很奇怪: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返回,凭何记准了楼号和楼层……
岳母去世,我于极度悲恸之中,撰写一联,悬于挽幛之上,道是:
打也是爱,骂也是爱,终教姻缘结成双;何期再世做东床
生也刚强,死也刚强,不使疾病累儿郎;留得家门日月长
——令睹者唏嘘。
董华 北京市房山区坨里村人。农民出身。“老三届”初二学历。创作以农村题材散文为主;目前已出版《还是乡情》《乡里乡亲》《大事小情》等多部作品。现为中国作协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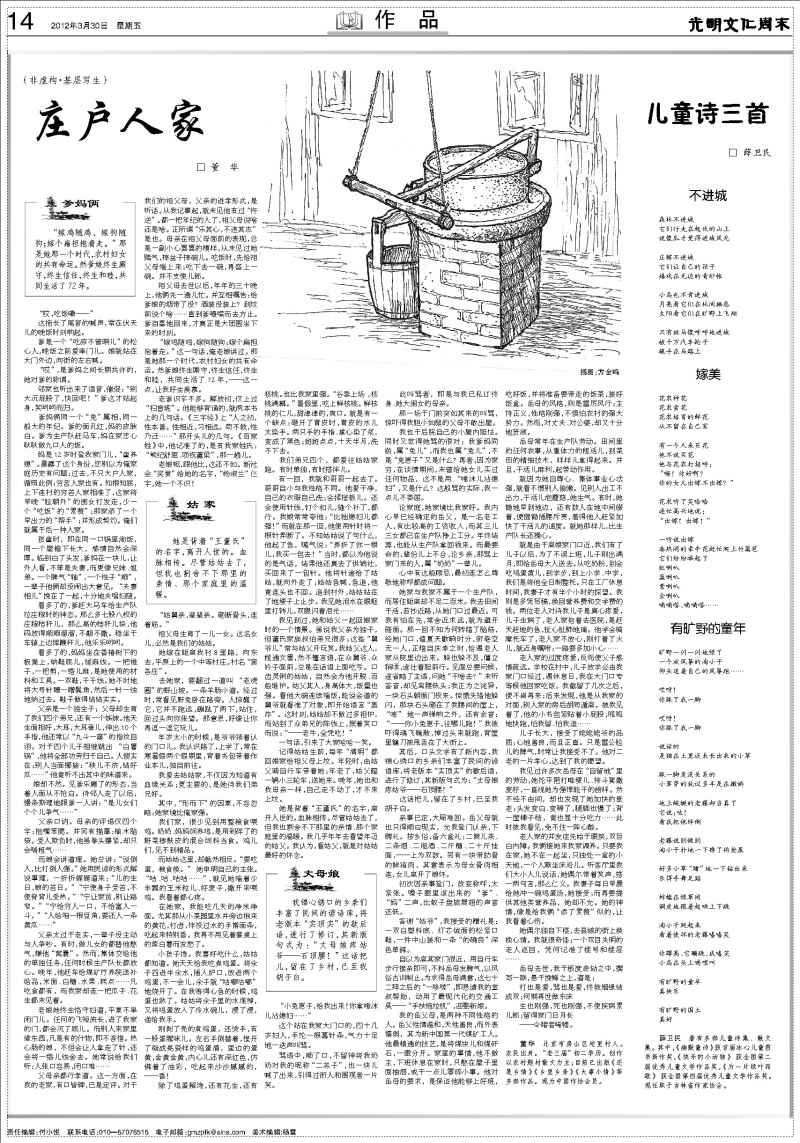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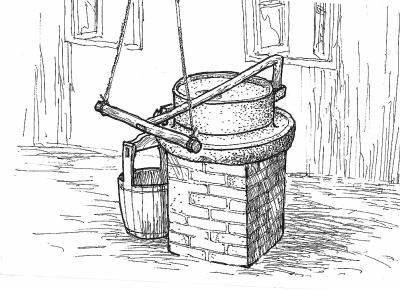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