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里,孙犁逝世似乎是两三年前的事情,可实际上已经将近十年了。大约是人过中年的缘故,近年来愈来愈感觉时光的飞逝,古人说的“无情岁月催人老”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在孙犁辞世将近十年之时,我读到了他的女儿孙晓玲撰写的《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三联书店2011年6月版)一书,让我们更多更深地了解了孙犁,在众多回忆、描述孙犁的书中,这是无可代替的一本。
因为作者是孙犁的女儿,所以她有着天然的优势,有机会观察家庭生活中的孙犁,而且她又是孙犁几个子女中和父亲在一起生活时间最长、来往最密切的一位。孙犁的一些经历,和亲属、朋友、同事的许多交往,她都在现场,许多事件她是唯一的见证人、目击者,她的所见所闻,自有其独特的价值。如书中写到的谢晋拜访孙犁、铁凝对孙犁的探视,特别是孙犁与妻子的相濡以沫,妻子去世后孙犁对妻子一往情深的追思、怀念,以浓郁的父女之情写孙犁夫妇饱经忧患的伉俪之情,读了让人动容,催人泪下。
但并不是有了客观条件的优势就可以写成一部好书的,我们已经在坊间见过太多的回忆亲属的回忆录让人难以卒读。该书的成功首先在于作者“不美化、不讳饰”的理念。她没有想把父亲写的如何伟大、完美,而只想写出真实的父亲。书中固然写了孙犁与吕正操、梁斌、方纪、刘绍棠、谢晋、铁凝、贾平凹、徐光耀、宗璞、叶文玲、曾镇南等著名人士的交往,同时也写了他与无名的青年作家、不相识的读者、周围的普通人的交往。书中写了他在“文革”的苦风恶雨中遗世独立,傲骨铮铮,也写了他日常生活的孤独寂寞、庸常琐碎。他对人们对他作品的高度评价固然不会沾沾自喜,但听到人们用“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来评价他时,他也会开心地讲给没有读过书的妻子听。评论家曾镇南用一首优雅的五古把“耕堂劫后十种”的书名嵌进诗里,称颂他“十集成一帙,功如泰岱崇”,他“喜而录之”,写成书法送给女儿。他虽然写起作品来妙笔生花,让人称奇,但老家来了客人,他却不会做一顿家常饭,只能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去小饭馆吃饭。他虽然与许多作家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市长来访却让他局促不安。作者就这样写出了一个本真、立体的孙犁,给读者的印象非常深刻。
读了该书,让读者对孙犁何以成功会有更深的理解。孙犁的成功自然与他敏感的天性、持续的积累、严谨的创作态度分不开,这些已经多有论列,兹不多赘。笔者认为最关键的一点是和他有一位贤惠的妻子分不开的。他的妻子虽然没有读过书,但聪明、美丽,最可贵的一点是贤惠,集中了东方女性的传统美德。她虽然不懂文学,却明白人情事理,知道尊重丈夫,懂得读书人的宝贵。不管丈夫的事业是顺是逆,她一门心思相夫教子。她不会因丈夫带来的灾难、坎坷说一句怨言,只会为丈夫的成就发自内心地自豪。她几乎承担了一切家务,为丈夫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方便,从精神到物质,应有尽有。在她的身上我们再次见识了中国妇女“平凡的伟大”,是所谓“百姓中的圣人”。
作者能够写成该书,是和父亲对她的影响分不开的。数十年的耳濡目染,再加父亲晚年的点拨,她自然受益匪浅。通过书中的文字,可以看出她是真正理解父亲的。她在《大道低回,独鹤与飞》中写道:“远离‘官场’,‘懒’于做官是由于父亲对‘官场’有自己的看法,他也缺乏做官的素质、本领。只有文学才是他生命所在。……正是远离了官场,远离了官场的是是非非,耄耋之年潜心创作,父亲才写出了凝聚心血智慧的十本小书。”而这不是容易做到的。孙犁自己说过:“虽是同行,也并不是容易理解的;即使是亲人,理解也不是那么全面的。”(《论理解》)
至于该书的写法,也深受孙犁有关传记文学的观点影响。孙犁说过:“写传记,首先是存实,然后才是文采。先求历史家欣赏,再求文艺家欣赏。”(《关于传记文学的通信》)作者在后记中也说“史实第一,文采第二”。我们读完全书,应该说她确实做到了,完成了一部佳作。我们应该对她的劳作表示感谢。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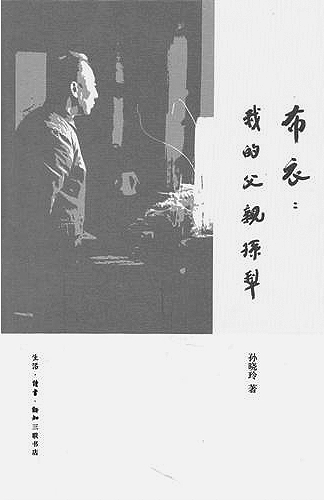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