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933年,西方国家经历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在这场危机面前,各国政府束手无策,继而政策失误不断,终于使危机进入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场危机暴露了已有经济学理论的苍白无力:古典经济理论认为经济运行中不可能出现经济资源非充分利用的情况,因而无法预测和解释经济周期性波动和大规模经济危机的爆发。大危机的现实促使人们深刻反思,经济理论需要创新。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通论》的产生改变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标志着以研究经济资源的总体利用程度为己任的宏观经济学的正式产生。凯恩斯在《通论》中否定了价格机制自动保证市场出清和市场机制总能使经济资源充分利用而达到充分就业状态的“萨伊定律”。凯恩斯认为,由于价格调整存在各类障碍,所有市场处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状态只是一种理论抽象,一种特例,市场经常性地处于供求非均衡状态才是一般状态,才是通例,这便是《通论》得以命名的原因。
《通论》将经济研究的对象从经济资源配置转换到经济资源的总体利用程度问题上,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三大定律会造成社会总有效需求不足,由于经济体系本身并不存在自动趋向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因此凯恩斯极力主张政府在危机时出手,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有效需求,发挥需求的“乘数效应”,实现充分就业。
《通论》的出现是颠覆传统经济理论的创新,是一场革命。凯恩斯之后,在众多凯恩斯主义者的努力下,凯恩斯理论得到了长足发展,宏观经济模型不断完善,微观基础也得以建立,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正统理论,并成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行动指南,上升为一种政府需求管理理论。在实践中,西方各国政府在经济周期波动中积极运用凯恩斯理论来对付经济萧条和失业,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凯恩斯式的总需求管理之下,战后的经济周期曾一度被“熨平”了。
然而,学界对于凯恩斯经济思想及其政策的争论却从未停止过。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以严谨的理论模型、扎实的微观基础和实证计量分析对《通论》的命题进行了批判,尤其是对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和挑战。1973年的石油危机使西方发达国家出现失业与通胀并存的“滞胀”现象,被上述反凯恩斯主义学派视作政府长期执行凯恩斯政策的恶果。
确实,面对“滞胀”,凯恩斯学派一度“失言”。随着原计划经济国家纷纷展开市场经济导向的经济转轨之后,市场经济理论进入发展高潮。相反,凯恩斯理论被视为国家干预主义的一种思潮,逐渐退入一个相对低迷的时期。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奠定了《通论》的重要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重新回归:所有东西方政府几乎都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模型,运用财政刺激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积极刺激有效需求,使得全球经济在2010年之后有所复苏。这说明凯恩斯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他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内对经济复苏是有很大作用的。
事实上,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就其实质来讲,是全球实体经济非均衡所致。全球化极大拓展了全球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空间和市场容量,全球总供给能力得以迅速扩大。但全球化的红利分配机制却存在根本性缺陷: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与资本在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的同时,其普通劳动者却因为产业转移面临收入下降或失业增加的局面。同样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通过本国要素(劳动、土地、环境)价格的扭曲参与全球化,虽然得到了产业链底端的生产和就业,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收入回报。其结果,一方面是全球总需求消化不了全球总供给,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贸易不平衡也不断积累,美元等外汇储备在新兴经济体中不断积累。为了更好地消化全球庞大的总供给,同时新兴经济体的巨大外汇储备给发达国家提供了充分的流动性,一场以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资产泡沫不断发展,居民通过财富效应扩大需求,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非均衡“闹剧”越演越烈,泡沫的破灭不可避免。
本轮危机爆发后,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实施避免了1929年危机的重演。短期来看,凯恩斯主义政策不容置疑是一剂良药。但诚如凯恩斯本人在《通论》中所说:“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并不能改变当下全球经济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的现状,这一失衡今后必须得到调整。此外,政府短期政策的代价是巨大的,它会造成对市场机制的破坏。比如,危机治理三年来,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注资和救助,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全球发达经济体财政赤字和债务的不断积累,政府债务危机频发,处理不当仍可能导致全球经济二次探底。政府的短期注资和干预,只是将各类经济主体的资产与负债关系暂时掩盖起来,各类结构性失衡并未得到合理矫正,这势必给全球经济的长期健康增长埋下隐患。从这个意义上说,凯恩斯主义的“功”与“过”仍需要重新评定。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上期重读《国富论》见11月18日本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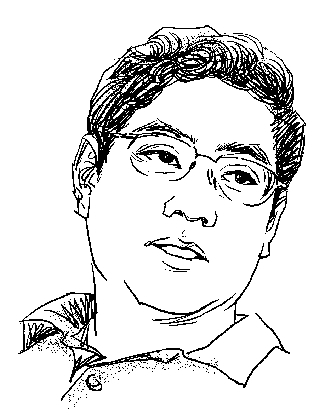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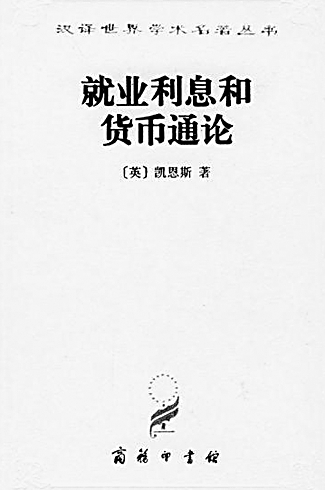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