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我们党成立90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就是一部在学习中奋进、在奋进中学习的历史。在这方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爱书、读书、相互荐书的佳话,毛泽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当前,全党正在大力开展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活动,重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读书故事,继承他们的学习态度和好学精神,对于我们进一步树立正确的学习观,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有所助益。本文梳理了毛泽东读《反杜林论》的相关问题,从细节上展现了毛泽东的好学精神和科学的读书方法,相信能给读者带来思考和启迪。
《反杜林论》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反复读过的重要哲学著作。在长征行军途中,毛泽东克服重重困难,把这本书一直带到了陕北,在自己的重要著作《矛盾论》中还引用了该书的两段原文。1963年,毛泽东提出学习30本马列著作,其中就包括这本书,并专为印马列著作大字本问题写信给周扬,嘱咐像《反杜林论》这样的著作要印成四本或八本,减轻每本的重量,以便于阅读。所有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对这本书的高度重视。但是关于毛泽东首读此书的时间,它是不是毛泽东确定的“干部必读”等问题,仍旧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观点,现根据相关史料略加考辨。
毛泽东在什么时间首次读了《反杜林论》?
现在通行的说法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读过《反杜林论》。然而现有证据表明毛泽东在1932年4月就得到了《反杜林论》。据时任漳州中心县委秘书长且亲自陪同毛泽东去找书的曾志回忆:“我同他一同去龙溪中学翻书,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找了好多书,恐怕有好几担书,是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的。他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找到《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和经济之类书的。”
逄先知在《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文章中对这件事情是这样写的:一九三二年四月,红军打下当时福建的第二大城市漳州,没收了一批军事、政治、科学方面的书送到总政治部,其中有一些马列著作。根据彭德怀和吴黎平(即吴亮平)的回忆,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即《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同样也认为在打漳州时确实得到了《反杜林论》的中译本。
既然1932年就得到了《反杜林论》,为什么直到长征途中才阅读该书,这与毛泽东宁可不吃饭也要读书的性格有些不相符合。仔细查找相关史料可以看到,实际上毛泽东在得到《反杜林论》之后到1932年11月之间,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读了好几遍。根据《反杜林论》的译者吴黎平的回忆文章:他于1932年11月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一看我就说:‘你是吴亮平,《反杜林论》不就是你翻译的吗?’我说,是。他说:‘这本书我看过好几遍了。今天碰到你,很高兴。’然后,他又讲了《反杜林论》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本书。这说明毛泽东念了很多书的。红军打下漳州时,毛泽东看到了一些书籍,其中就有《反杜林论》。”这个回忆说明毛泽东在打漳州得到《反杜林论》之后,马上就“看过好几遍”。
1957年毛泽东曾感慨地同曾志谈起:“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是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这里虽没有提起具体书名,但由于是与当年一起到漳州找书的曾志谈话,所提“马恩列斯的书”完全可能包括《反杜林论》在内。
有学者曾提出毛泽东既然在1932年就看过《反杜林论》,那么,他为什么在1933年给彭德怀荐书的时候没有推荐这本书呢?我觉得这实际上与毛泽东学以致用的读书习惯有关。毛泽东读马列,总是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来读。正如逄先知先生所概括的:“他读马列著作的特点是,有重点地读,认真地反复地读,密切联系中国实际来读。”当时毛泽东正在集中思考“左”倾错误对中国革命的危害问题,所以他在给彭德怀推荐《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时重在点出“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引导彭德怀深刻反思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1938年1月,毛泽东将《反杜林论》一书推荐给梁漱溟读。主要是因为他通过阅读梁的《乡村建设理论》,看到梁在改造和建设中国方面走的是改良的道路而不是革命的道路,在与梁的多次谈话中发现他太看重中国的特殊性,而忽略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共同性,片面地强调“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却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重要作用。为此他推荐《反杜林论》一书,目的在于引导梁在做中西社会对比时采用科学的方法。由此可见,毛泽东向别人荐书并不止是考虑书是什么样的书,而且还注重把合适的书推荐给需要的人,以此来解决实际问题。
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究竟是否读过《反杜林论》?
根据毛泽东长征途中的警卫员陈昌奉的相关回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行装有“一个灰色的九个口袋的公文包。主席用的地图、文件、书籍把这个公文包装得满满的。”“主席晚上很少睡觉。吃过晚饭就点上小灯,打开那个九个口袋的公文包,拿出地图、文件、纸、笔就开始工作。主席看书、写字,我就在旁边坐着。”但是由于他“参加革命的时候一个字也不识”,所以,他能够记起的只能是毛泽东的公文包里装满了书,通宵达旦地看书,但是具体看了什么书在回忆中却没有记载。
张闻天夫人刘英曾回忆说:“毛主席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书上打杠杠。有时通宵地读。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饿肚子,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这里也没有提到《反杜林论》。是当时没有看到还是在回忆时省略了?不得而知。刘英是在1935年4月到8月期间作为中央队秘书长与毛泽东、张闻天等一起行军的,此前和此后毛泽东在行军中的细节她或许也并不太熟悉。
逄先知在《毛泽东读马列著作》一文中写道:“另据吴黎平回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读过《反杜林论》。”这是依据吴黎平《〈反杜林论〉中译本五十年》的回忆:“毛主席对这些马列著作译本非常珍视,在长征行军中,毛主席丢弃了好些衣物,但马列著作译本却一直带在身边。记得在长征胜利结束到达陕北后,毛主席有一次对我说,‘你看,我把这本书(指《反杜林论》)带过来了。’”
这些记载可以确证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一直“带着”《反杜林论》,到目前为止,这是确证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读过《反杜林论》的主要证据。当然“带着”就等于“读过”吗?这只能从当时的情况来作出推理:当时毛泽东手头的马列著作并不多,因此“带着”按照常理是应该“读过”的。
《反杜林论》是“干部必读”吗?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提出的5本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12本马列著作中,都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部著作。因为这部著作是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根据《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内容(《引论》的第一章、第三篇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编而成,有学者据此说《反杜林论》被列入了“干部必读”,实际上这是不准确的。
恩格斯在改编时对《反杜林论》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多达28处补充和修改,而且《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国外和国内都出版了单行本,显然是一本独立的著作,而不是《反杜林论》一书相关章节的简单汇编。况且列入“干部必读”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由博古在1943年重新校译的,而不是由吴亮平翻译的1938年列入“马恩丛书”第三种的那个版本。由此不能简单说《反杜林论》被列入了“干部必读”。实际上,直到1963年,毛泽东提出学习30本马列著作的意见时,才把《反杜林论》包括进来,而且特意附上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为什么《反杜林论》没有被列入“干部必读”呢?我想主要有两条原因。第一,毛泽东向全党荐书在用不在深,在精不在多。《反杜林论》是一部很专业的哲学著作,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将近30万字,并不适合在战争时期推荐给党的干部来读;第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被马克思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列宁也认为这部书同《共产党宣言》一样,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经典著作,是“每个有觉悟的工人必读的书籍”。并且读这本书不用花很长时间,所以在确定“干部必读”的时候,选择与《反杜林论》有着深厚“血缘关系”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而不是它本身,也在情理之中。而在解放社公开出版的“干部必读”中,还将《共产党宣言》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合印为一本书,充分显示出后者的重要地位。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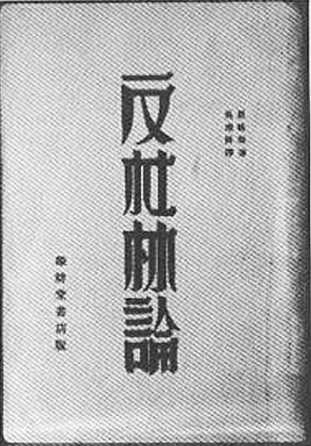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