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适者,犹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则劳而不至,惑者胜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向,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庄子·外篇·天地》
知道自己犯傻的不算太傻,知道自己看不准拿不稳的不算太糊涂。真正的愚痴糊涂是一辈子也明白不过来的。三人同行,有一个人糊涂,也许人们还可以走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因为糊涂人是少数;两个人犯傻,就不好办了,因为糊涂人成多数了。如今这世道,整个天下都糊涂啦,我虽然有点见解,有点救世的用心,照样起不了作用。太可悲了!
庄子居然早就对于多数少数问题有所思考,他提出了多数的愚蠢的可能性,客观上通向多数的暴政的可能性,多数与智商并非成正比的问题,这里有点易卜生主义的味道。他抨击对于多数的迷信,也有尼采的光彩,尼采曾经宣布:“我是太阳。”
大声不入于里耳,折杨、皇荂(fū),则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胜也。以二缶钟(或作二垂踵)惑,而所适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向,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释之而不推。不推,谁其比忧!厉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
——《庄子·外篇·天地》
宏大的音乐对于市井里弄之人来说并不入耳,而折杨、皇荂一类流行小调,人们听了就能咯咯地笑起来。所以说真正高超的言论不能在人众心中留下位置,至理名言也不能流传广远,倒是俚俗的说法热热络络。把两个瓦罐一个铜钟放在一起敲打,钟声就被干扰,听不到理想的乐声了。如今糊里糊涂者是以普天下计的,我虽然有观点有愿望,又怎么能达到目的呢!明知其不可还要强使劲,这不也是一大糊涂吗?算了吧。不要妄想去推行推广了,放弃了对于大道真理的推行,也就没有谁与你一道发愁了!丑八怪半夜里生个孩子,急忙取火烛来照映,诚惶诚恐,唯恐孩子长得像自己。这又有什么用呢?随他便不是更好吗?
一上来讲最好的音乐并不如通俗小曲,易于被人众接受,令人想起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关系问题。毛针对的是从上海亭子间来到解放区的文学人,他鼓励他们与群众结合,而不要自命不凡。但毛主席在他的晚年,也常常讲到真理可能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是讲他自己,他晚年所主张的某些“继续革命”的理论,难于为大多数同志所接受。
这里的庄子,与老子的和光同尘说、知白守黑说有点不同,他实际上承认了自己的特立独行与独树一帜。他认为他是那个三人行中的唯一识路者,是被两个瓦罐扰乱了的那个铜钟。他还不无怨忿地大讲又一惑也。与世俗对着干,岂不是糊涂上加了糊涂!讲起这些问题来,此处的所谓庄子,有几分气儿。
丑人怕孩子丑的说法极具黑色幽默色彩,自己已经丑八怪了,只好认命,还管到孩子后代那边去,岂非更加自寻烦恼?人的烦恼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管得太宽,操心过度。庄子发完牢骚再自我安慰,美就美,丑就丑,糊涂就糊涂,明白就明白,明白人帮不了糊涂虫,糊涂虫也灭不了明白人,丑人变不成美女,更管不了孩子长成什么模样,也就不劳操心选美活动的进展。明白人打不开糊涂人的脑筋,也就不必关心人众的智力开发,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有删节)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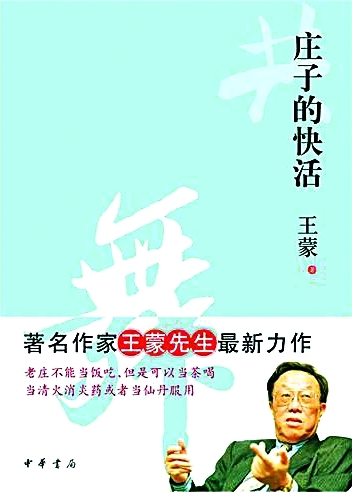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