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中国苏轼学会请他担任顾问,老人点点头说:“担任顾问,不承担具体工作,只是发表意见。”
得知一家出版社要为他所做工作支付报酬,老人摇摇头:“不要,做这种事情,我是不要报酬的。”
“我很对不起中华书局,承诺中华书局做《三苏》修订,现在书稿找不到了……”
“找老郭,多要两部样书……”老人的话语已经有些含糊不清,意思却让刘尚荣听得真真切切。
此情此景,成为孔凡礼留在当了他50多年学生、40多年责编的刘尚荣眼前的最后景象。就在刘尚荣离开医院回单位的路上,老人进入弥留。
孔凡礼,中国高校在编教授中没有这个名字;中国在编研究机构高级研究人员中也没有这个名字。甚至,他连中学高级教师的职称也没有得到。但是,著名的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出版的40余部学术著作的作者栏中却赫然写着这个名字;50年来,宋代文史多项重要研究成果的获得者是这个名字,学问得到著名学者李一氓、钱锺书、赵朴初、启功高度评价的,也是拥有这个名字的那个人。
成果写入当代学术史
孔凡礼在学术研究中初露头角,就不同凡响。1958年2月9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发表了他的《陆放翁的卒年》一文,学界争论了七百多年的陆游卒年,由此一槌定音,被学界奉为定论。
当年八月间,孔凡礼就陆游研究向钱锺书先生请教,很快接到钱先生以朋友口吻作平等学术对话的长达千言的复信。
1959年8月3日,孔凡礼将自己的第一部书稿《陆游评述资料汇编》交给中华书局。中华书局取其与稍后送来的同样内容的齐治平书稿各自之长,改名《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出版。出版后,学界评价颇佳。
1982年,孔本《苏轼诗集》面世,以信息量大,资料翔赡,校订精审,收诗最多成为苏轼研究史上难得的精品。“我们出版界有一个共识,一时畅销的不一定是好书,要看这书是否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和销售期,有些书年年印,年年卖,几十年长销不衰,这就是传世之作。从1959年开始,孔老在书局出版了多部专著,基本都在重印。《苏轼诗集》就重印了8次,发行3万多册。”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说。
继之,孔凡礼又投入《苏轼文集》整理。《苏轼文集》前人从未全面校勘过,其工作量远较整理苏诗艰巨。考疑、辑佚工作更是常人难以承受之浩繁。孔本《苏轼文集》荣膺苏集定本之誉。《苏轼佚文汇编》附《苏轼文集》后行世后八年,成《苏轼佚文汇编拾遗》二卷,再后近十年成《苏轼佚文汇编拾遗补》一卷,孔凡礼书海搜寻,披沙拣金,去伪存真,终成就明万历茅维之后苏文辑佚的最大成果。其中,《艾子是苏轼的作品》一文,被学界以为是苏轼研究史上一重大贡献,自宋以来久无定说的《艾子》是否是苏轼所作终于定论。以花甲之身,积年之力,孔凡礼相继完成了作为国家“八五”计划、“九年规划”重点图书的8册、164万字的《苏轼诗集》,6册、180万字的《苏轼文集》。“近百年来苏轼研究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海内外学界就此形成共识。
1982年,孔凡礼在《文学遗产》第二期发表《关于汪元量的家世、生年和著述》,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李一氓就此约见孔凡礼,并委托其整理汪元量的作品。对孔凡礼的整理成果,李一氓在其刊于《人民日报》的《古籍整理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这样评价:“孔凡礼的《增订湖山类稿》,不为汪元量的《汪水云集》或《湖山类稿》所限制,从《诗渊》和《永乐大典》新辑得元量诗词,用编年的方法,同原集打散整编为五卷……书后附《汪元量事迹编年》,和汪元量作品互为发明。迄今为止,可算是汪元量诗词集的最丰富、最有科学性的一个整理本,成为研究宋元史和宋元文学史的要籍。”
1998年,孔凡礼历时24年四易其稿的《苏轼年谱》由中华书局出版,迅即得到学界高度赞誉。有学者称它是自成体系、超越古今的新型年谱。有学者誉之为20世纪写得最好的一部年谱。次年,《苏轼年谱》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在《苏轼年谱》付梓前,孔凡礼已经启动《苏辙年谱》编纂。四年后的新世纪元年,50万字的《苏辙年谱》交由学苑出版社出版。有评论说,《苏辙年谱》谱主形象丰富多彩;资料详实,论据充足;考订严谨,辩证细密;详略适宜,写法新颖,是全方位描绘谱主风采的成功范例。
苏氏兄弟年谱面世后,孔凡礼即着手苏洵年谱的编纂,此书交稿之后,尚未付梓,他又应北京古籍出版社之托,编纂三苏年谱。在前三谱的基础上,孔凡礼用4年时间,对三苏生平、交游、著述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往再次全面考察,重新写了一部《三苏年谱》。孔编《三苏年谱》甫一面世,好评如潮,被视为“迄今为止三苏行实研究最高水平的成果”。始自1977年的28年中,孔凡礼以苏轼为主体的三苏研究,成就著作5部22册700余万字,以新颖、详尽、扎实、可信,奠定了自己在“苏学”史上重要的地位。
由陆游研究起步,经三苏研究的磨砺,孔凡礼翱翔在学术研究的自由王国。他的研究领域扩展到范成大、晁补之、朱淑真、赵令畴、汪元量、郭祥正等一批宋代作家的行实考察,并由此发展为对整个宋代文史的关注。他的郭祥正研究,成为800多年来对郭祥正的第一次全面认真的考察,澄清了长期的误解,恢复了郭祥正的历史本来面目。他的《范成大佚著辑存》,被誉为“近百年宋代文史著作”六大辑佚成果之一。他的《全宋词补辑》,收《全宋词》遗漏的140多位作家的430多首词,其中约百位词人是孔凡礼的新发现,“为研究宋词提供了新的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是近百年宋代文史著作辑佚又一显著成果。他编成的《宋诗纪事续补》,较清人厉鹗《宋诗纪事》、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增收宋代诗人1700人。一经出版,立即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受中华书局与其他出版社委托,孔凡礼还先后点校整理宋人笔记30多种,“几乎部部都有独到的发现”。2007年中,孔凡礼为中华书局点校整理了宋人叶寘《爱日斋丛钞》、周密《浩然斋雅谈》、陈世崇《随隐漫录》等,而这一年,孔凡礼已是85岁高龄。
孔凡礼的学术影响也早已蜚声海外。日本著名汉学家小川环树对其研究成果深表敬佩,认为孔校本涵盖了日本某些寺院秘而不宣的诸多苏集珍本三苏善本所独有的异文。孔本著作已成为日本、美国汉学家和我国台湾学者在广泛使用的底本。
学者却始终是个编外
在计算机无处不在,改变了几乎所有学人治学方法和生存状态的今天,孔凡礼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治学状态。孔凡礼认为,学界很多人冷落图书馆,通过网络搜索来做学问,并引之为时髦,是完全错误的,很容易导致以讹传讹。50多年来,论在图书馆中度过的时间,老人恐怕在学者中要名列前茅了。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处处留下他的足迹,许多多年无人问津的古籍,孔凡礼成为惟一的读者。他是国图明代“穴砚斋钞本”《家世旧闻》的发现者,也是解放后惟一的读者。旧书摊、碑刻所在也是孔凡礼常去之地。直到80多岁,老人依然奔波在京郊大兴乡间居所到国家图书馆的路上。老人2007年8月27日的日记记录了这一天去图书馆的行程:
“早5点多起床,6点45分,走一里地,到达通三环的679路公共汽车站,……到达国图善本室,已是10时17分。……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几乎站不住,把握不了。……到了借阅大厅,正是10时25分。……到快餐厅,买了一包饼干,喝了一点水。到服务台提出预约的书,复印了一些。到敦煌室找了一点材料。2时30分,出国图,坐319路公共汽车……回到海子角住地,已经是6时了。坐下来都不能动,两条腿几乎不管用……不过,累,值得。我得到了我需要的资料,这些资料用到书上,可以提高质量,我可以问心无愧了。”写到这里,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
孔凡礼选择的是乾嘉朴学的治学方法,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研究中,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22册,他至少通检了50遍,每一遍都有新收获;影印的《永乐大典》202册,他起码通检了20遍……正是在这巨量的阅读中,他因新的发现,把研究不断向历史深处扩展,使认知接近历史真相,也使自己的著述充满智慧的光辉。
在图书馆,孔凡礼写下了20多本读书笔记和无数学术卡片,总量有几百万字,这当中,记下了孔凡礼无数拂去历史尘埃,始见瑰宝的心花怒放之时。1977年他在北图善本室意外发现目录卡上赫然写着明钞本《诗渊》25册,多出此前邓广铭先生所用《诗渊》16册。《诗渊》成书与《永乐大典》年代相差不多,收诗五万多首,其中十分之二三不见于古今刊印的古籍,也不见官修大型类书《永乐大典》;收词七八百首,其中大部分不见于《全宋词》、《全金元词》。从中,孔凡礼一举辑得《全宋词》失收的词作400余首。可以说,孔凡礼的每部著作,都是这样上下搜索,集腋成裘之作。
数十年中,孔凡礼沉潜精专之作颇丰,一个个古籍整理项目常人看来独木难支,靠他所说的“笨功”又费时费力,时日老天不假,从何而来?
孔凡礼是在而立之年开始学术研究的求索的,当时,他刚刚从安徽一所乡村中学调入北京三中任教。1963年,病中的他选择停薪留职,既减去不能担负教学而拿取报酬对三中的愧疚,又可全身心投入陆游研究。从此,除了以往几百元的积蓄和第一笔千余元稿酬,每月一家人的生活就靠中华书局支付的40元生活补贴维持。“文革”中,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全面停滞,孔凡礼重返教职而不得,在三中做了数年教学辅助工作,每月收入仅16元到30元。1979年,“文革”后首次提工资、评职称,孔凡礼也刚刚重新走上三尺讲台,重新开启中华书局委托的整理三苏资料的学术研究,考虑到自己年近花甲,教学、研究难以两全,孔凡礼婉拒了中华书局调他当编辑的邀请,毅然提前退休。孔凡礼与时间赛跑的赛程重新开始。1982年,孔凡礼再次谢绝李一氓请他到古籍办工作的邀请,为自己争取了宝贵的研究时间。
“洗得发灰的蓝布中山服罩褂,领口已经破了,衬褂是洗毛了的白老布,衣领上缀着厚厚的补丁。当我站在敞开的门前时,他正佝偻着高大的身躯,‘咝咝咝’地喝着稀饭,桌上是一摞翻开的书稿,旁边是一碟不知名的咸菜。我的天,今天是中秋节了,现在正是月圆之夜!”黄山书社一位编辑看到的,不是孔凡礼生活中的一刻,而是常态。这常态,为孔凡礼赢得了时间和精力,使他得以潜心去做惠及子孙后代的研究。他靠克己与牺牲,赢得了学术研究并不舒适但却自由的空间。
晚年,老人在家乡一所高校的讲台上,面对后辈学子语重心长:“我这个人,有一点特殊性,一方面我是北京一所普通中学的普普通通的教师;另一面,我又是有着多方面学术成就的致力于宋代文史研究的学者,这种情况,在北京市不多见,在当代中国也许是个特别……我为《全宋诗》、《全宋词》这两部代表一个时代学术水平的总集,做出了别人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或许可以说,有我的参与,这两部书就显得更有光彩;如果没有我的参与,这两部书可能就要暗淡一点……”老人的话,点燃的是世人对学术文化的信心。老人离去后,顾青在缅怀前辈时说:“当前学术文化事业实用主义盛行,很多人急功近利,抄袭现象大量存在,导致公众对学术界信心减弱,也失去了对学术应有的崇高感。孔老的学术成就和生活经历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应当保有这份信心。”
心灵的回声
翻开《孔凡礼文存》,在石钟扬所写的《无冕学者孔凡礼》一文中,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几十年中,我先住在‘东倒西歪’的两间东屋,后来又住进‘骄阳飞汗雨’的斗室,然后又住进荒鸡夜唱的村舍。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出版了近40种书,发表了三百篇文章,还有一部存稿,字数共约在一千三百万。……人们亲手把教授的桂冠要戴在我头上,我婉谢了;有人要给我房子,我婉谢了;我过着四十五年的单独生活,为了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我献出了一切。我鞠躬尽瘁,问心无愧。
这杯本来是清醇甘美的酒,在进入八十岁以后喝起来,却越来越苦涩。有谁能知道其中的真味呢?只有我自己,我只有慢慢地喝着,细细的品味着,因为这酒是我亲自酿造出来的。”这是孔凡礼在与他的传记作者书信往来时的内心独白。当问及其治学中最遗憾的事时,孔凡礼的回答让石钟扬潸然泪下。老人说,我多次幻想拥有一间窗明几净的书房,两侧排列着书柜,按经史子集分开,我徜徉其中。如果具备此条件,我的成果可能还要多一些。转而他又说,其实,这也不是遗憾,因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在这方面知足。进而,老人又反复说了一个不可抗拒的遗憾:自己年龄太大,时间永远不够支配,还有许多工作等着他去做。“我现在要是六十八岁,该多好啊!”发出这生命呼唤的时候,老人已是86岁高龄。
两年后,他在病榻上离开了他眷恋了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那一刻,他有多少遗憾,多少不舍,多少无奈?
让我们从老人当时的心境回望,探究他生命的历程,重温他学术研究的追求。
作于1963年的一首诗中写道:“东倒西歪屋两间,斜风细雨送床前。我自如山山不动,剑南理罢又骚篇。”
1992年,又一首诗是这样的:“郐曹临上国,造化赐机缘。出入文津道,留连厂肆廛。五千唐宋卷,百万管蠡言。苏陆明窗读,豪情尚欲燃。”读先生的七十抒怀,读出几多豪情?
下面一首,名为《七十八岁初度》:“日丽风和卷霹雷,蓬门长闭躲书堆。齑盐三顿清如水,骏马千蹄志不回。薄有刍言传域内,愧无冠冕启方来。人生得失如何计,漫把封缸尽一杯。”诗中千滋百味,令人肠断。
老人的倾诉与呼唤,令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生出无限感慨,郁积满腔痛惜。扪心自问,当老人发出这呼唤时,如果听到,我们是否会做些什么,给老人赢得更多的时间,让这样一位稀世人才能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添加些许当代人的贡献?在老人带着遗憾、不舍离去之后,我们痛定思痛,是否应当为还在学术研究之路上艰难跋涉的张凡礼、孟凡礼们做些什么,以使今天的时代大师辈出?我想,这才是记者写这篇报道、本报发表这篇报道时的期望。
本报记者 庄 建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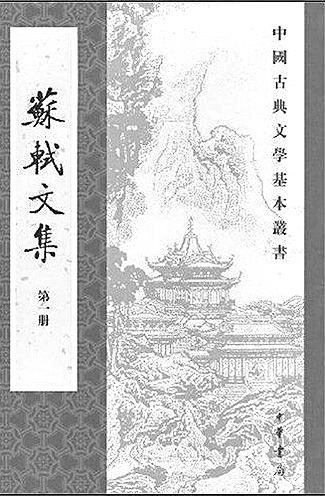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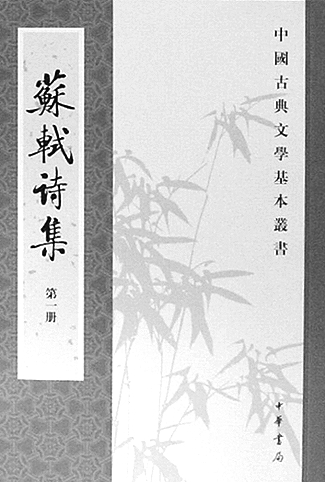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