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罔罟(gǔ)之所布,耒耨(lěi nòu)之所刺,方二千馀里。阖四竟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乡曲者,曷尝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
——《庄子·外篇·胠箧》
从哪里知道这个真相的呢?从前的齐国,一家连着一家,一村靠着一村,邻里间互相看得见,鸡狗之声互相听得见,方圆两千多里,到处都是捕鱼的网罟和耕作的犁锄(形容非常繁华兴旺)。在自己的四境之内,又是建立宗庙社稷,又是定规矩制度把一家一户组织成邑屋州闾乡曲的建制,何尝不是想按圣人的教导行政,来他个长治久安、铁打的江山?但一旦田成子(原齐大夫陈恒)其人杀掉了齐王,盗得了齐国,他夺到手的岂止是一个国,还盗来了圣人治国的法度智谋。这样,田成子有盗贼的名分,人们会说他是窃国者,同时他享受着尧舜一样的安稳。小国不敢对其有什么非议,大国不敢对其用什么刀兵,他世世代代据有齐国。这不正是不但盗走了齐国,也盗走了齐国采用的圣人之智谋法度,用来保护他的盗贼之身吗?
这可坏了,却原来,知识、智慧、法度、谋略、圣人、道理、体制、学说、说法、理念都是既可以为A服务,也可以为B、C、D……服务的。庄子在这里碰到了一个复杂深刻的问题,即智力与知识的价值中立问题。当然不可能绝对中立,得民心者的智力应对,是失民心者所无法效仿的;胸怀宽广者的智力发挥,也是心胸狭窄者所一辈子学不到手的;与人为善者的态度、举止、风范,更不是仇视人类的与人为恶者所可以汲取的。但同时,有一些东西,有一些部分,又确实是有可能通用的。
尤其是我们国人所谓的“御民之术”,即驾驭人民的帝王之术。这个“术”太“伟大”,太需要包装,要讲许多高端的道理与原则,要让被驾驭者看了听了想了心甘情愿地被御,要让御人者——帝王们理直气壮地去御人。这样,一接触这样的话题,从圣贤到诸子百家都要往高深伟大里使劲。好的,驾驭人民,确实高深伟大、出神入化、感天动地、至尊至上;所有的伟大崇高又有可能至少在特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变成一种术、权术、机变、谋略、窍门、手段,而术——手段就像工具或武器如手枪一样,谁拿起谁用,谁掌握了就服务于谁:能为圣人所用,也能为盗跖所用;能为唐尧、虞舜所用,也能为夏桀、商纣所用。夏桀、商纣完蛋了,并不是因为他们拒用帝王之术,而在于他们用得太过、太笨、太片面、太粗糙或太缺乏自信,最根本的,则是他们遇到了对手、克星,遇到了道高一尺、术高一筹的商汤与周武王。而田成子用了这样的术,并且取得了成功。
这里还有一个核心秘密:在中国叫做“胜者王侯败者贼”,在英语中叫做“Might is right”——有权的人总是对的,谁有权(威力)谁有理。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圣人之道几乎也是由胜利者、权威者书写的。远在先秦时期,庄子已经看透了治国之道其实是为胜利者、权威者、权力者效力的。他干脆抨击一切道道、道理、学说、说法,尤其是在治国平天下上最为致力,从老庄的观点来看是相当烦琐、矫饰的儒家学说。他们以为用无为、齐物的观点把治国平天下的学说空心化、虚无化、零点化,才能拯救世界。当然,这更是幻想。
同时,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不是一切权力运作都畅通无阻,百战百胜,有的权力系统被例如农民起义或宫廷政变所摧毁、所颠覆。权力受挫、权力败亡的教训也是值得总结的。所以儒家致力于构建一套修齐治平的理念体系直到道德规范,去确定君君臣臣的道理。他们断言,君符合某种道德要求了,臣也符合某种道德要求了,就可以天下太平,权力就可以运作顺畅,这叫做邦有道。相反的情况叫做天下大乱,叫做国将不国,叫做气数已尽,叫做邦无道。我们可以用权力,用might来说明理念,也可以用理念、权力的运用是否right(正确),来说明权力的兴衰、行市与命运。所以在历史上末代皇帝差不多都是昏庸恶劣愚蠢之辈,而开国皇帝都是伟大明君。
庄子居然敢于说出这样另类的话,他在为君君臣臣的一套,为儒家的一大套道理祛魅。问题是他祛完了魅,并没有货色可以代替,《论语》《孟子》的地位仍然是高于他的《南华真经》。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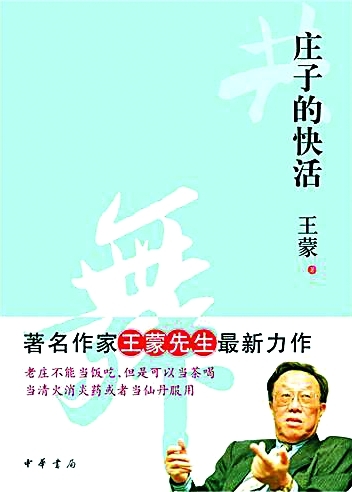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