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踶(dì)。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而马知介倪、闉(yīn)扼、鸷曼、诡衔、窃辔。故马之知而态至盗者,伯乐之罪也。
——《庄子·外篇·马蹄》
这个马,生活在陆地上,吃草喝水,高兴时互相用脖子抚摩,生气时背对背尥蹶子。所谓马的智力不过如此罢了。可人要给马匹加上辕木、笼头、套具、口嚼,于是马也就学会了如何折断或摆脱辕木、笼头、口嚼、套具的束缚,如何对抗逃逸。所以说,马学会了对抗人类的各种招数,这都是伯乐的罪过呀。
然而这是从马的角度上看,从人的角度上看呢?人是要用马的膂力的,没有那些工具,马当然舒服了,但是也就不为人用了。还有,这里的问题是驯马过程使马也产生了被使用的需要,只有被使用,才能得到饲养,得到存活繁殖。使用与被使用,这正是文化的起源,也是对于自然的冒犯的开端。奴役者本身也是被奴役的,任何对于自然的使用,其实也在使用自身,使自身的存活繁衍大大地复杂化、人为化、困难化了。人们毁坏了原木,制造了典礼上使用的高级酒尊,从此必须在典礼上行礼如仪地饮酒,或只剩了作饮酒状行饮酒礼,越来越多地失去了自自然然与情人、家人、好友饮酒闹酒的乐趣,却得到了参与典礼的满足感与虚荣感。
文明有文明的代价,无文明有无文明的代价。文明的代价是纯朴自然的失落,是烦琐,是走形式走过场、虚与委蛇乃至骗局伪善的出现,是以文明以价值为理由引出的愚蠢而且残酷的纷争。无文明的代价是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挨打受欺,被淘汰而灭亡。庄子,有时还包括老子,只谈一面的代价,但确实谈得精彩,令人耳目一新。
另一方面的意义是:这里表面上谈马,实际上是谈治与“治于”(如所谓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即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庄子的说法是:被统治的草民,本来如未遇伯乐的野马一样地纯朴简单,问题是伯乐,也就是伟大的君王与大臣太智慧也太啰嗦,制定出各种招数来统治民人,制造出各种衡扼、月题(横木颈与马额上的装饰),如今之所谓辕木、笼头、口嚼、套具……来巧为控制马儿;与此同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无政府主义是对于官僚主义的惩罚,草民们也发明了各种阳奉阴违、腹诽、口是心非的招数,伺机破坏捣乱,直到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与“彼可取而代之”的造反有理论等对抗之。从此天下多事,治人是越来越难、越来越危险了。
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正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
——《庄子·外篇·马蹄》
在那个上古赫胥氏的时代,民众安居而不知所为,没有什么一定要做、急着要做的事,出门也没有什么地方一定要去,有东西吃就很开心,吃饱了就悠游自在,大家都是这样生活的,大家要做的能做的事止于此。等到圣人出现,费尽心力弄出些礼呀乐呀来匡正天下的行为举止,标榜仁义来安抚天下的民心,于是民众开始奔竞用智,争逐私利,而不能休止。这些都是圣人的过失啊。
十分有趣的思路。大家浑浑噩噩,婴儿一般,饿了吃,累了睡,得空就玩,其他什么也不知道,这是理想吗?好像缺点什么。人活一辈子,还想发展自己的脑力、体力,想求知求美、求幸福求光荣、求意义求价值,并期盼这些追求的充分实现,甚至还想在各种比赛中一显身手,虽败无憾,不能不与闻人生竞争之盛况。而且,人还有智慧与灵魂,不但要知道生存诸事,还要知道点形而上,知道点开始与结束,永恒与无穷,我之外的你与他,有形之外的无形,肉身之外的灵魂。
于是有了人类的与中华的文明文化、圣人先贤……有了信仰、价值、观念、科学、技术、各种文化的精神的与物质的成果,有了历史,有了文明的积淀……与此同时,歧义、竞争、虚伪、阴谋手段、盗窃与歪曲也在发展,世界愈来愈复杂,生活愈来愈复杂,纷争愈来愈复杂,罪恶愈来愈发展……
“踶跂好知,争归于利”。“踶跂”是自矜,是得意,是臭美;“好知”是好动心眼,是搞手段。为什么好知不能是好学不倦、诲人不厌呢?为什么智慧不是首先带来文明与进步、幸福与快乐,而是首先带来了阴谋诡计呢?这是值得深思的。培根讲知识就是力量的时候,不会有这样的思路的吧?而如今对于科学主义的批评,能不能够从老庄那边找到源头呢?
“争归于利”的说法则比较实在。概念愈复杂,价值愈强调,说法愈发达,争执就会愈多,争来争去其实是利益的争夺,人与人、家庭与家庭、族群与族群、地域与地域、国与国的多少抽象的争论均牵连到具体的利益,争于义的实质是争于利,这话够直截了当的,也够令人叹息的啦。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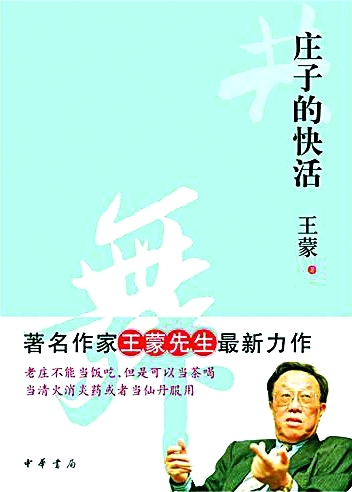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