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
——《庄子·外篇·马蹄》
我认为真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并不这样。他们认为,老百姓自有本身的稳定的天性,要穿衣就要织布,要吃饭就要种田,这是他们共同的本能,这叫共识、共同利益、共同的规范。在符合自身天性的活动中,他们彼此一致,却不需要结党成伙,这就叫自然而然,纵性放任于天地之中。
呜呼庄子!他抨击那些烦琐苛政、严刑峻法,他抨击当时的为政者扰民乱民、坑害百姓反而得意洋洋、吹嘘叫卖、欺世盗名。他讲的伯乐、陶匠、木匠的故事既有趣又发人深省,令人击掌叫绝。但是他的民有常性,只要按常性做就万事大吉的设计却未免天真幼稚,失之于幻想。民有亿万,性有什千,地域、族群、血统、文化、观念,尤其是利益之分别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但民与民能够发生矛盾冲突,人与人能够发生龃龉斗争,同是一个人连自己也有找不到自己的常性的时候,陷于选择上的困惑与两难。再说,有所管理,有所主张,有所维护,有所坚守,也是人之常性,正像无为而无不为、无可而无不可、与世无争等也是常性之一种。你依常性而治,你搞常性乌托邦主义,按谁的常性呢?按庄先生的常性吗?孔先生、孟先生、墨先生、师先生、离先生等都与您常性不同,咋办?没有社会没有家庭,个人难于存活;有了社会家庭之累,就有人际关系的种种麻烦。庄子关于常性的说法很漂亮,但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风凉。庄子的治国之论非常高明,高于常人常理,但是缺少成功践行的实例。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
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
——《庄子·外篇·马蹄》
所以在大德昌盛的时代,人们做事缓慢持重,眼神也都比较专一,不怎么东张西望。(或理解为:做事的状态、看人的神态,都是自然而得意的。)那时候,山岭上没有栈路也没有隧道,水面上没有船只也没有桥梁;万物共生,比邻而居;鸟兽一群一群,草木也是自由自在,连成一片地茁壮生长。所以,想牵上什么鸟兽一起游玩也就一起游玩,想攀缘到哪里去看鸟鹊之窝,也是随便。
在这样的至德之世,人和鸟兽混居,与万物并存,何从区分什么君子与小人呢。
写得真好!“填填”、“颠颠”,我宁愿取前面的解释,即持重和专一。虽然解释为自然、得意,与对于放的向往较易衔接。因为庄子喜欢的放,并不是当今奔波迅捷、竞争浮躁之放,而是远古无为无欲、无争无言之放,是在大臭椿树下睡大觉之疏放,是乘大葫芦而游江湖之豪放,正好与缓慢持重、专一踏实相衔接,也正好与当今人们普遍诟病的浮躁相比对。这样的庄子的放,应该能够把持重、专一与自然、得意统一起来。至于老子,并不那么讲放,相反他要讲“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第十五章):小心翼翼,好像冬天过冰河;醒觉警惕,像要提防四面之敌;还要正儿八经,像做客一般。
事物的发展与变化,文化的丰富与精微,社会生活视野的无限扩大,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财富的核能爆炸般的增长,欲望因其不断实现所产生的无限膨胀,使人们的心态比古人浮躁得多,现代人要更心慌意乱,更顾此失彼,更疲于奔命,更丢三落四,更晕菜得多。这种信息爆炸、任务加码、动静失衡、生活混乱的痛苦,是值得研究研究、分析分析了。想想庄子的有关说法,说不定对我们大有益处。
毛泽东有言,差异就是矛盾。庄子的思路则是尽最大努力抹平一切区别、一切差异,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齐物。庄子提倡的是“平心”,这与西方思想家拼命提倡的平等各有千秋。
当然事情没有这样简单。时到今日,要牵上一只猴子蹓马路应非易事,但是我在不丹王国的经验使我相信,《庄子》的有关说法不完全是乌托邦。在不丹,由于所有的狗受到全民的爱护喂养,于是狗没有私有被私有的意识,没有对立与警惕的意识,没有恶意的吠叫,它们在大街上任意躺卧休息,对于任何人都是友好的。你即使躲来躲去还是不小心踩上了它的尾巴,它也只不过是“哼”一声,缩一缩继续睡觉而已,不会怒目相视,不会发出恶声,更不会龇露牙齿。这太惊人了,也太值得深思了,却是我亲眼见到亲身经历的。
不丹的狗似乎是所谓的先王之世的狗,是无为而无不为的狗,它们没有主人也就没有敌人,没有任务也就没有执著,没有期待也就没有操心。当真是一种理想啊。
(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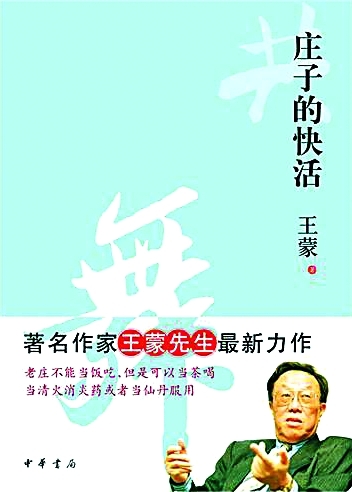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