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吴方先生的《追寻已远——晚清民国人物素描》,不禁长叹。在这本书里,吴方一共写了30多个人,虽然只是素描,淡淡写来,却颇让人怅惘。正因为晚清、民国有这么一些人立于其间,遂使这个时段变得有声有色起来,让人不能忽视、不敢掠过。
人物比较难写,尤其是这些丰富、复杂的人物,要把他们写出神采,不是易事。有才华的人的禀性都是迥异于俗常的,尤其是文人,书生自有嶙嶒骨,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谁也不要想左右他。这些人物置身于这么个世运多舛、世事迭变的空间里,比在世道隆兴中人更有切肤之痛、之快。如龚自珍,诗章中多次以“剑”、“箫”意象,看起来似乎处在不惠不夷中,实际上已是满腹苍凉,危险逼近。读龚自珍的《病梅馆记》不难看出,这么多人喜欢病梅,映衬出世态已进入沉沉的病疴之中,不仅是世道之病,更是精神之病。林琴南则不同,既有维新的经历,又有保守的心愿,同时清高倔强、坚硬孤傲,颇似严复与辜鸿铭。他们坚守的方向是十分分明的,对时势的态度是一回事,有自己独立的处置方式;人格的独立又是一回事,是必须持守传统的人格精神和道德价值的。正因为如此,诟病他们保守也罢,但在人格上决不会流于屑小、猥琐,依旧可以圈点。
书中的人物吴宓是我喜欢的学者之一。他不是政治家,只能耍耍笔杆,和陈独秀、胡适的文学革命打打笔仗。他策划的《学衡》有一个大旨是我一直认为要持抱的,其旨曰:“讲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完全可以为学人之座右铭。而周作人这个人物似乎不太好写,一会儿在台上,一会儿又在台下;一会儿是演戏的,一会儿又成了看戏的了,角色不断转换,让人难以估量。当然,吴方还是把他当作文人来写,写他的“困境”,写“困境”中他的种种表现——这些人的政治生涯和文学生涯应该分开来说才理性一些,我欣赏周作人的一句话:“古来圣人教人要‘自知’,其实这自知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真是一个过来人由衷的感叹。
和上述人相比,有些人似乎会显得轻松些。如洁来洁去的梅兰芳,红氍毹上的万种风情,戏迷们随着剧情的起伏而唏嘘而开颜,台上台下,感动和痴醉。丰子恺的人生会令人想起他的画,真有那么童稚之趣吗?在他的随笔里,平常中渗透着滋味,看似琐屑、寻常人事,却是最底层的真实,也是丰子恺本人给后人的真实写照。还有在历史不易把握中搁笔转向的沈从文,他不从文了,而去从事文物研究,显然不能用幸与不幸来言说——一个人不跟上时代走向,有时真是一种大幸。我在咀嚼这些有着喜剧色彩的人生时,最终还是落入伤感中——时代提供给他们的精神生存条件,真是太苛刻了。
弘一大师是这幅人物长卷中最独到的一位——一个出家人,长久地被文人所记取、所仰慕,成为一种标志。出家是常人难为之事,因果不明,铮然而变,让人永远猜度不透其中的玄机,只看到出家前后判若二人。入得深了,佛门生活也充满了情调,也是需要精诚、尊严、自律、升华,力戒流俗、虚伪、矫饰。我们对于弘一的仰望,也就是精神的难以抵达——一个出家人做到了,更多的非出家人反而做不到。
吴方笔下的这些人,现在真是很少了,我不是指人的学问,而是指这些人的脾性、风度、格调。那么我们追远,究竟什么值得我们追寻呢,这是值得深思的。
末了,我觉得应该谈谈这本书的作者吴方。他去世已15年了,只活了47岁。扉页有一张他的照片,叉着手坐在栏杆上,眉目神情像个稚气可爱的大男孩。真让人可惜。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8月 北京第1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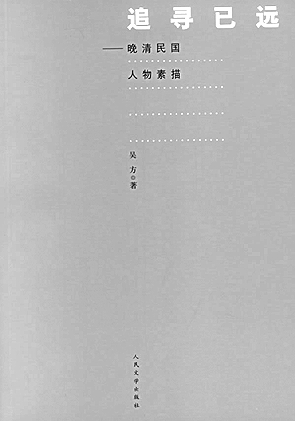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