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作家东君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瞩目。他区别于其他作家之处,不仅在于独特的写作风格,还有自成一派的艺术观念。擅长写作短篇小说的东君,对于一篇作品的篇幅与结构有着独到的计算与构造。看起来优美的文字之下,实际上有着细密、精确的骨骼。东君最新的小说集《某年 某月 某先生》已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收入《某年 某月 某先生》《夜宴杂谈》等9篇近年作品,并有两篇文谈随笔。东君的创作谈并不多见,但出手即令人惊喜。这篇文章可视作作者对自己创作的重要补叙。
•Ⅰ•
一个作家写作一部小说之前,他通常会对作品的结构有一种超乎寻常的预见。他不仅能隐约知道它的长度,还能明确分布其中的章节,而这种结构往往与神秘的数字有关。《百年孤独》分20个部分,这个数字刚好与玛雅历法中的20制进位相对应。《发条橙》分三部分,共21章,作者特地解释说:21是人类成熟的标记,在西方社会一个人到了20岁就意味着他将拥有选举权。君特•格拉斯的《狗年月》分三篇,我从中发现,第一篇从第一个早班写到最后一个早班刚好是个早班。这与但丁《神曲》的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神曲》也分三篇,每篇分33首歌。正如中世纪的音乐家与诗人大都把自己的作品建立在“三”这个数字上,昆德拉的小说也大都以数字“七”为长度标准。昆德拉曾为四件乐器钢琴、中提琴、单簧管、打击乐创作了一个乐曲,结果他竟惊讶地发现:这个为四种乐器所作的乐曲竟是由七个部分组成的。而他的小说也逃脱不了七这个数字的宿命。他的《笑忘录》和《生活在别处》刚好分七个部分。在他写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部小说时,他试图打破这种结构。可他写完第六章之后,发现第一章还可以一分为二,其结果是这部小说又变成了7章。我宁可理解为,这是昆德拉有意要让数字7所包蕴的吉祥色彩与小说中的悲剧色彩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昆德拉后来在《小说的艺术》中曾这样解释自己对数字七的迷恋:“这既不是借用魔术数字来做迷信式的卖俏,也不是什么理性的计算,而是一个深刻的、无意识的、不可理解的必需,是我无法逃避的形式原型。”有意思的是,《小说的艺术》这本书刚好也分七个部分。
•Ⅱ•
能让我读上三遍以上的长篇小说并不多,萨拉马戈的《修道院纪事》就是其中一部。我不仅着迷于它那文字的魅力,还着迷于数字的魅力。圣奥古斯都曾在某处说过:美以数字呈现它的魅力。《修道院纪事》就向我们呈现了这样一种魅力。小说的开头就运用了数字:“在国王名单上排第五位的唐•若奥今晚要去妻子的卧室。”接着就写到了荷兰运来的床,这张床是国王花了7万5000克鲁札专门订做的。然而随着人体发出的热量,宫廷或者城市里的臭虫开始侵入这张床,为此国王不得不向圣亚莱索50列亚尔,目的是让皇后和众人免受害虫和奇痒之苦,但仍然无济于事。作者似乎要在第一章以一连串数字向我们表明:这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但到了男主人公“七个太阳”和女主人公“七个月亮”出现之后,小说就变得越来越虚幻了。萨拉马戈愈是把数字写得精确,故事带给人的虚幻感就愈加强烈。他没有在下面描述修道院的庞大规模,而是以数字说明一切:这座修道院有4500扇门窗,114口钟,宽220米。近5万人工作了几十年,造成了1383人死亡。这就是萨拉马戈运用数字的高明之处,他用简洁的数字语言来表述一个必须动用众多修饰语才能表述的场面。他那样做不是把文字数字化,而是把数字文字化。他有时会给石匠工资300雷依斯(繁忙季节500雷依斯);有时会给拉巨石的车夫派10对或者20对的牛;他有时还可以代替国王下令,为马拉芙修道院的开工仪式拨款20万克鲁札,有时还会不厌其烦地为一块石头丈量长度、厚度以及重量。我们大可不必去了解那些度量单位(比如拃,我弄了很长时间才明白,它相当于拇指与中指之间的距离),但我们可从数字中间找到作者的用意。在第16节,数字运用达到了极致,作者从数字3一口气谈到了数字13。然而,我们一路读下来并未觉得啰嗦。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也喜欢使用数字,而且带有一种夸张色彩。其中有一段历数了奥雷亚诺分别和十七个姑娘生了十七个私生子,发动了三十二次武装起义,遭到了十四次暗杀、七十三次埋伏和一次枪决。(这段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博尔赫斯小说中的阿尔莫塔辛:“这是阿巴锡达王朝第八个国王的名字,他赢得了8次战争,生了8男8女,有800名战俘,一共统治了8年8个月零8天。”)与马尔克斯这种在数字上粗手大脚的人不同,萨拉马戈对待数字近乎苛刻,仿佛他已经从一名作家变成了谨小慎微的会计师。萨拉马戈这样不厌其烦地列举数字,并不是为了考察物与物之间的数学关系。我们只要读一下第12章和第16章就会明白:连数字都充满了文字所无法表达的意蕴,而不是简单的序数组合。在第25章,数字向我们传达的是一种悲哀与执着。七个太阳失踪后,七个月亮在9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男人,最初她计算自己走多少瓜菜,但后来数字变得混乱了,衡量一切的尺度变成了上午、下午、下雨、烈日……小说写到这里,作者突然玩起了冷幽默:七个月亮找七个太阳既不看年轻的,也不看年老的,只看45岁的,因为他失踪时就是这个岁数。在故事的结尾,她终于找到了七个太阳。作者做了这样的交代:她曾经6次经过里斯本,这是第7次。那时她看到有一群死囚被送上火刑台,处以极刑的共有11人,其中一个
博览群书 2016/10正烧着的男人没有左手。于是七个月亮布里蒙达说了一声:过来。七个太阳巴尔塔萨尔的意志就脱离了肉体向她飞去。假如我记得没错,这是她收集到的第2001个意志。在《修道院纪事》中,萨拉马戈就像圣经中描述的上帝一样,用数字、重量和度量创造了一切。
•Ⅲ•
在西藏,一位诗人朋友告诉我,传说西藏的彩虹一端有一块如意宝,但一个人必须以粪便涂身,然后骑着一条也涂着粪便的狗去追赶彩虹,这样就将得到一块如意宝。其实,西方也有类似的传说,只不过,他们说的彩虹一端系的不是如意宝,而是黄金。这样的异闻,要是遇到一位自然科学工作者,也许就会被指斥为无稽之谈。济慈说牛顿研究虹的光学性质时,把它的诗意也赶跑了,“一道彩虹被分解得只剩下水蒸气……”
布莱克写过这样一句诗:刹那即是永恒。永恒究竟是多长时间,没有人计算得出来,但有人却可以算出“刹那”就是0.018秒。如果把布莱克的诗译成“0.018秒即是永恒”,精确度是有了,诗意却早已荡然无存。同样,把李白的“白发三千丈”改为“白发三尺长”,这首诗不但少了气势,而且不能成其为诗。诗人写诗时,可以毫不顾及时空概念。有位学者指出,李白诗中的“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还”,把昭君出塞的路线弄错了,杜甫的“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把织女星的方位也弄错了。我们若是按照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去解读一首诗,那么,很多诗都犯了常识性错误。然而,这种理性分析实际上是把诗的伪陈述转换成科学的陈述,把所有引发美感的东西变成机械的,可以组装、拆散的物品。
有人读梵高画时,发现漩涡图案中居然暗藏着数学和物理学的公式,并且自鸣得意地将公式罗列出来。我看不懂那些高深莫测的公式,但我以为这是一种很叫人败兴的解读。早期的立体画派(这个称呼原是批评家在上个世纪初的某一段时间里用来骂人的)出现之时,有些批评家就认为,那些新派画家不是在搞绘画创作,而是在搞几何学研究,因此就干脆奉送他们一个称呼:几何派的画。立体画派的代表人物毕加索、布拉克都曾致力于客观物象的几何化表现。诗人阿波利奈尔作为立体画派的拥护者,受毕加索作品的启发,创造了一种图像诗,试图让诗歌通过视觉形象来表现。但他表示,他不准备做一个几何学家。我们现在去看立体画派的作品和阿波利奈尔的图像诗时,谁还会去探究他的几何学原理?毕达哥拉斯有一句著名的格言:一切都是数。也就是说,万物之间都存在着数学的精确关系。
毕达哥拉斯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道:数学支配着世界;天籁归于神,在星球的运动中响彻着数学。比如他提到的音乐,在音乐的和谐里也可以考察出精确的数学关系。但我们欣赏一首美妙的乐曲时,谁还会去思考数的生成规则?
(作者介绍:东君,原名郑晓泉,1974年出生,乐清柳市人,温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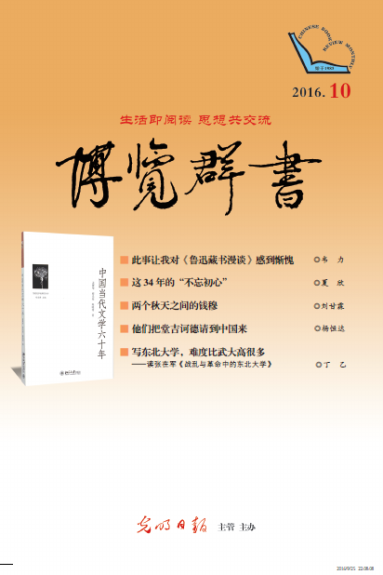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