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一批新兴的省会书院相继创建,其创建的初衷是以经史之学去挽救沦为科举附庸的书院事业,实现重振世道人心的目的。创建者着意推古求新,繁荣学术,培养人才,潜移默化之间,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所书院是广州学海堂、杭州诂经精舍、上海龙门书院、江阴南菁书院、武昌经心书院、长沙校经堂、成都尊经书院。在这些新兴省会书院中,只有成都尊经书院僻处西南一隅,远离当时文化教育的发达地区,然而,在其创办的28年间,成材甚众,名人辈出,不仅成为四川地区新旧交割的重要一环,而且折射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轨迹。一些重要的近现代人物,如杨锐、廖平、宋育仁、吴虞、张澜、吴玉章等,都曾在这所书院肄业,同时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维新变法、保路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也有这所书院的师生们组织和参与其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尊经书院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动荡的同光政局与尊经书院的创建
历时十三年之久的太平天国战乱,不仅给晚清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同时也开启了一番新世局。在朝廷,辛酉政变打破了统治集团的政治格局,内政外交重新调整,权力利益重新分配。一些与肃顺过从甚密的人物受到政治牵连,被扣上“肃顺奸党”的罪名,仕途中断,返回原籍。其中就包括后来尊经书院的两位著名山长王闿运和伍肇龄。在地方,湘军、淮军的实力派人物受到倚重,独当一面,成为推动经世之学兴起的重要媒介。从地域学术的消长来看,人文鼎盛的江浙一带惨遭兵燹,元气大伤,不少世家望族的后裔流寓内地,为偏远的四川地区注入了一股江浙学术的新风。另一方面,不少川籍将领在战乱中立下军功,他们凭借这些军事、政治上的资本,为川省换来大量的学额。随着学额激增,人才培养的规模也随之扩大,客观上要求创办高水平的学校,扭转士林风气,提升川省的文教质量。这些新的动向为尊经书院的创建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兴文县(今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在籍侍郎薛焕代表全省士绅投牒于四川总督吴棠、学政张之洞,请建书院,以通经学古教育蜀士。薛焕出身蜀中望族,历任苏州知府、江苏巡抚。咸同之际,因在上海组织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和办理通商事务,他与李鸿章交往密切,并结为姻亲,他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李鸿章的兄长李瀚章的两个儿子。
薛焕以自己显赫的身份和地位倡议修建书院,立即得到四川总督和学政的积极响应。他们联名上奏,请建书院,最后得到朝廷许可。书院于光绪元年(1875)春正式落成,院址设在成都文庙西街石犀寺西面。书院最初拟名“受经书院”, 用西汉文翁派遣蜀士张叔等18人至长安受“七经”的典故,表达了创建者意图效法文翁兴学,重振蜀学的愿望。这一愿望也就是张之洞在《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中归纳的“绍先哲,起蜀学”六字建院宗旨。不久,因为有人指出受经应该在京师,外省不可用“受经”字样,于是更名为“尊经书院”。
尊经书院创建伊始,即向当时一些学术名流发出了热情的邀请,希望他们前来出任山长或主讲。这些名流包括俞樾、张文虎、李慈铭、王闿运等,但都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未能成行。在此期间,学政张之洞为尊经书院的创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不仅为书院制订学规章程、购置图书、开设书局,还编写了著名的学术入门书籍《书目答问》和《輶轩语》。此外,他还慧眼识英才,选拔杨锐、廖平、张祥龄、彭毓嵩、毛瀚丰等青年才俊就读尊经书院,号称“尊经五少年”。张之洞之于尊经书院,虽无山长之名,却有山长之实,而且他以学政的身份入川兴学,被誉为“文翁再世”也不为过。
尊经书院实际的首任山长是薛焕,但是,他在山长任上的时间非常短暂。尊经书院建成的当年八月,他就离任赴云南协助亲家李瀚章处理“马嘉理事件”去了。“马嘉理事件”以次年七月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告终。按照《烟台条约》的规定,英国人可以开辟印藏交通,这对于川藏地区的边疆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光绪二年(1876)九月,湘军大员丁宝桢出任四川总督,准备经营西藏,应对英、法、俄等列强的侵犯。为此,丁宝桢特地从湖南请来了精通“帝王之学”和“纵横之术”的王闿运为其出谋划策。“强收豪杰作才人”的王闿运自视甚高,不愿屈居幕府,于是丁宝桢重金聘请王闿运出任尊经书院山长,以此作为权宜的安置。王闿运掌教尊经书院长达七年,在他的精心培养下,产生了一大批四川近代史上重量级的人物,使蜀学名声大噪。尊经院生张祥龄论近代蜀学的兴起,认为:“吾蜀学术思想,实启于南皮(张之洞),成于湘潭(王闿运)。”
尊经学术与尊经学人
尊经书院的创建,在理念上以“文翁兴学”为指向,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则模仿诂经精舍、学海堂的章程、制度,在学术倾向上也偏重乾嘉汉学。这种倾向从尊经书院最初向江浙一带的俞樾、张文虎、李慈铭等人发出邀请就已反映出来。俞樾等人因故未至,继而又聘浙江海宁钱保塘和嘉兴钱宝宣为主讲。二钱都有汉学的家学渊源,尤其是钱宝宣,乃浙江名士钱仪吉之子,因太平天国之乱举家流寓蜀中。正是二钱将尊经书院早期的学风引上了江浙派的路数,光绪四年(1878)尊经书院刊刻的第一本课艺集《蜀秀集》,“所刊皆二钱之教,识者称为江浙派”。
光绪初年,朝廷有江浙派和湖湘派两大对立的政治集团,四川总督丁宝桢是湖湘派官员的代表,经常带头与大学士翁同龢为首的江浙派势力较量。在丁宝桢主政的四川,“江浙派”自然不受欢迎,浙江籍的二钱因此遭到排挤,而尊经书院的学风也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转向了经世致用的“湖湘派”。
王闿运入川执掌尊经书院,是尊经学术的转折点。与江浙派重考据、辞章不同,王闿运继承了湖湘派自嘉道以来“以礼经世”的学风。关于王闿运精通礼学,《世载堂杂忆》有一段有趣的记载:“王壬秋最精《仪礼》之学,平生不谈《仪礼》,人有以《仪礼》问者,王曰:‘未尝学问也。’黄季刚曰:‘王壬老善匿其所长,如拳棒教师,留下最后一手。’”然而,黄侃所言,也不尽然,王闿运的《仪礼》之学在尊经书院的教学中其实有大量的展现,并未留下一手。《湘绮楼日记》中留下不少王闿运与尊经弟子们一起研讨《仪礼》,并操练释奠礼及饮酒礼的记录。由于王闿运对礼学的重视,尊经书院的礼学大盛。如果将王闿运所编的《尊经书院初集》与《蜀秀集》比较,不难发现,尊经初期编撰的《蜀秀集》中,关于三《礼》的课艺题目仅4道,而《尊经书院初集》则有26道之多。在王闿运的影响下,尊经院生廖平治《公羊》《榖梁》《小戴礼记》,戴光治《尚书》,胡从简治“三礼”,他们或精于《春秋》,或长于礼制,与诂经精舍、南菁书院、学海堂等推崇训诂考据的治学风格大相径庭。其中,廖平所著的《今古学考》,以礼制区分汉代今、古文经学,与顾炎武发现古音、阎若璩证伪《古文尚书》,并称清代学术的“三大发明”。后来,廖平的学说又直接影响到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成为维新变法的重要思想来源,同时在思想文化上,也开启了中国近现代疑古思潮的大门。
张之洞说过:“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理在学。”学术与政治休戚相关、血脉相连。尊经学术由考据辞章转向经世致用,培养出来的人才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建树十分可观。例如,光绪十一年(1885),院生孙鸿勋在广东任州判,协助张之洞收降刘永福黑旗军。光绪二十年(1894),院生宋育仁出使欧洲,任驻英法意比四国使馆参赞。适逢甲午战事起,宋育仁潜谋购英国水师,乘虚直捣日本京都,后因中日和议已成而作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晚清两大政治运动(“维新运动”“保路运动”)的发动者和中坚力量大多出自尊经书院,除了众所周知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位居“早期改良主义者”之首的宋育仁,还有邮传部参议、督办川汉铁路事宜的李稷勋,川汉铁路公司总理曾培,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副会长张澜,四川通省师范学堂监督周凤翔等,皆是尊经书院的学生。他们关心国事、积极参政的意识,与尊经书院的经世学风是分不开的。
尊经书院的裁撤与尊经传统的延续
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新式教育的兴起,尊经书院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开始走向衰落。清政府为了兴办新式学堂,需要筹措大量的经费,而旧式书院已无力再继续维持下去。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03年1月27日),四川总督岑春煊下令裁撤尊经书院。据档案记载,裁撤的原因是创办高等学堂、聘请洋人教习、东洋留学等教育开支耗费巨大,库帑奇绌,“万不得已惟有遵改书院为学堂之谕旨”,将尊经书院裁撤,“以其所有经费概并入高等学堂”。
明治三十七年(1904),日本人山川早水受聘为四川高等学堂日文教习,他在游记《巴蜀》中记录了尊经书院裁撤后的情况:
光绪初年,张之洞任四川学政,为蜀生作了《輶轩语》以及《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以鼓励学习。那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城中还是没有保存有好书。不仅如此,如今连能证明张氏曾经有所提倡学习的痕迹都找不到了,不能不感到意外。
然而,山川早水的观察并不准确。尊经书院虽然没有逃过裁撤的厄运,但是尊经的传统仍然在延续。1910年,尊经院生范溶、陈纬、顾印愚、王兆涵等投牒于四川学政赵启霖,请仿照张之洞在湖北武昌设立存古学堂的成例,在成都建四川存古学堂。在赵启霖的帮助下,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川督赵尔巽的支持,不久学堂建立。其师资大部分来自裁撤的尊经书院主讲和优秀院生,吴之英、伍肇龄等尊经学人都视四川存古学堂为尊经书院的学脉传承。辛亥革命后,四川省政府首创国学院,以研究国学、弘扬国粹为宗旨,并计划整理地方文献,同时以存古学堂为基础成立四川国学学校。1918年8月更名为“四川国学专门学校”,这是公立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的前身,至今四川大学的文史学科仍保留着尊经书院的传统和底蕴。
此外,尊经书院建院28年间,造就人才无数,他们散布于各地,仅成都一地,民国初年社会声望最高的“五老七贤”中,尊经书院肄业者就占一半以上。其中,尊经院生骆成骧是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中,四川唯一的状元,随后他以状元的身份留学日本,引介西方思想文化,推动了“新学”在中国的传播。尊经书院建院二十八年间,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历史时期,不少尊经院生及其后学投身到时代的激流中。《革命军》的作者邹容,师从尊经高材生吕翼文,其激昂的文字和激进的革新思想由此启蒙。在新文化运动中被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也是尊经院生,师从吴之英和廖平。他把廖平经学中“尊今抑古”的精神转移到社会批判中来,主张以新道德取代旧道德,完成了尊经学术与“新文化运动”的合流。钱基博认为:“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廖氏),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以汇合于蜀(吴虞)。”廖平的另一位弟子蒙文通由经学入史学,实现了传统经学向现代学术的转型。程千帆指出:“他(蒙文通)是把廖季平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用现代学术加以表现出来的。”
由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尊经学术的终点,其实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起点。尊经书院承载着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诸多要素,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象征和典范之一。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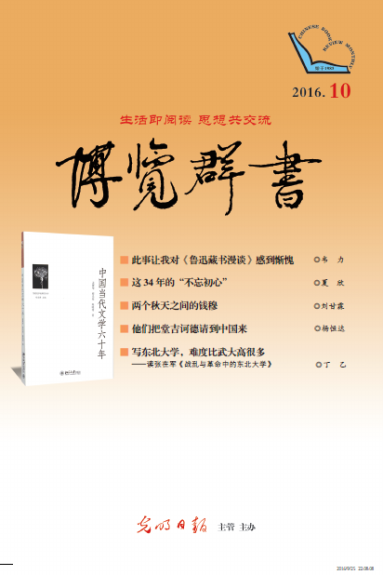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