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工作都离不开基本的素材,正如没有砖瓦等建筑材料,就无法造就宏伟的建筑。史学研究同样不例外,没有史料,就谈不上对历史现象的研究,只能脱离事实,借助苍白的理论,泛泛而论。学有卓识的历史学家都高度重视史料的作用,很多历史学家不惜毕生之力搜集整理史料,造福于中外学界同仁。纸质图书并不是史料的唯一载体,记录史料的载体是多种多样的,甲骨、简牍、碑碣、壁画等都是史料的载体。当然,这类非图书形式的史料要成为史学工作者们随手可查的文献,就必须经过辛勤的整理劳动。自从清末以来,中国史学工作者们在融合近代史学理论方法的基础上,积极从事非图书形式史料的整理工作,如王国维和罗振玉整理居延汉简,撰成《流沙坠简》。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经由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董作宾诸位甲骨学大家的细致研究和整理,使得史学家们面对殷商历史,有比较可靠的史料基础。孔子面对距当时不远的殷商历史,备受史料缺乏的困扰,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慨:“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 ”显然,孔子把殷商历史研究的希望寄托在可靠史料的发掘上。而甲骨文的发现和整理,使得殷商历史不再是迷离荒诞的神话传说。由此可见,史料的发现和整理极大地推动着史学研究。
碑碣和简牍、甲骨文一样,属于非纸质图书类史料,相比便于手持的简牍和甲骨文,碑碣这类石质史料文献具有难以移动和体量较大的特点。从先秦至今,在中国地上地下留下了大大小小的碑刻,记载了关于政治、文化、经济和其他社会活动的文献。褒扬人物的有记功碑,简述生平的有墓志铭,记录科举名单的有题名碑,修建祠堂、庙宇、水渠等事务亦有碑刻。甚至民间诉讼的处理过程和结果也有碑刻记载,从确切意义上说,碑刻还带有契约文书的功能。由此可见,碑刻虽然笨重,但是其史料价值绝不逊于纸质图书史料。
河南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无论是史前时代还是文明时代,先人们在饱经黄河滋润的河南大地上留下了无法计数的文物,有三座城市——洛阳、开封和安阳荣列于中华古都之中。可以想见,碑刻在河南数量之巨大。河南碑刻历来驰名中外,至今为书法家重视的隶书范本——《龙门二十品》就铭刻于洛阳伊水之滨的龙门石窟。东汉灵帝熹平年间,学术大师蔡邕整理了儒家经文,铭刻于洛阳太学所在地,即著名的熹平石经。每天都有学人前来对照碑文,核对、订正、补充自己手持的经文……直至清代,虽然河南已经不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但是仍然是碑刻大量出现的时代。如果能充分利用这些碑刻,对于研究清代河南历史变迁具有不可估量的推动意义。然而,令我们忧心的是,虽然清代距今不算甚远,但是许多碑刻由于遭受风雨侵蚀和自然风化,已经严重残缺,其碑文难以辨识。更为严重的是人为的毁坏,许多碑刻在无情的锤凿之下,变成修筑道路水渠的碎石。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会有大量碑刻史料来不及和史学家们接触,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于人间。所幸的是,由河南大学历史学教授王兴亚先生主编,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代河南碑刻资料》为我们保存了这批珍贵的史料。把分布于河南各市县的清代碑刻史料从石头上移到纸上,集中于厚厚的八大册里,极大地便利了相关研究工作。这的确是功德无量的史料整理工作。
这部《清代河南碑刻资料》收录了6300余方碑刻,不仅包括现存于博物馆、文物管理所或田野、庙宇、祠堂里的碑刻,也包括现已不存或难以寻觅,但在方志、家谱、公私文集里记载的碑文。换言之,已存或已经灭失的清代河南碑刻,已经尽可能地被容纳进这部文献集里了。
收集的清代河南史料数量是如此惊人,我们可以想见,王兴亚先生和他带领的团队所付出的艰辛劳动。他们走遍河南各地,既要在书斋里枯坐冷凳,又要在田野里踏破铁鞋,耐心而细致地抄录、核对、订正碑文。在不晓内情的外人看来,这种文献整理工作是极其枯燥乏味的。然而,这种坐得下,走得出,耐得住寂寞和枯燥的意志恰恰是我们所不可缺少的治学素质。
清代是河南社会极大的时期。河南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由明清更替的残酷战争,步入康乾盛世,进而被西方列强的炮火残酷无情地推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清末,铁路工程极大地改变了河南的交通格局,纵贯南北的卢汉铁路(今京广铁路北段)和自东而西的汴洛铁路(陇海铁路雏形)构成了十字形的铁路干线系统。河南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逐渐瓦解,大批农民告别乡村,走进工厂矿山,成为工人。宜阳的《河南府刘大老爷批准窑户送煤碑》让我们看到当地采矿业的艰难发展。安阳《禁止启土开窑碑记》使我们在既充满严苛又不乏焦虑的官方文字中看到清代官府对煤矿工人可能摆脱人身控制的担忧和无奈。
清末,近代文化教育事业清新而来,新式中小学堂和私塾并存于河南城镇乡村。如宜阳的《创建高等小学堂记》、西华的《清创修西华县学堂章程》等碑刻就朴实无华地记载了新式教育在河南腹地开展的情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河南人民对文化知识的追求,即使在清末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为沉沦的时代,河南人民同样没有丧失这个不懈的追求。
河南号称四战之地,清代虽然战争不及之前那样频仍,但是仍然经历了规模不等的战争或武装冲突,比较出名的有捻军起义太平军北伐,而且,清代河南匪患相当严重。清末,河南许多地方在乡绅的组织下,筑起圩寨,用以抵抗捻军或土匪武装。一些碑文站在清朝官方的立场上,对这些历史事件加以记载。如刻于咸丰六年的《重筑清化镇城碑记》就记载了太平军北伐时在河南的军事行动。刻于咸丰十一年的《重修虞城县碑》就记载了捻军由皖入豫的活动。
清代,又是河南自然变迁的时期。黄河治理问题一直是关系河南人民安危的大事。咸丰六年的铜瓦厢决口,夺占淮河河道数百年的黄河改由大清河河道北上入海,更是极大地改变了河南的黄淮水系。治河是清代河南碑刻的重要主题之一。如刻于乾隆年间的《请开归德水利疏》《敕建杨桥河神祠碑记》等,让我们看到当时河南面对黄河挑战,所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和斗志。
关于宗教信仰或民俗活动,更是不绝于清代河南碑刻中。我们可以看到城镇乡村民众,对佛祖、玉皇、老君、土地、龙王、比干、关公、岳飞等形形色色的偶像的崇拜,表达了他们对社会安定、健康富裕的持久期待,如登封的《重修老君庙碑记》、上蔡的《魁星楼文昌宫并三皇阁碑记》等。
如前所述,记载民间纠纷调解过程和结果的碑刻具有契约意义。这类碑文在清代河南碑刻中是比较常见的。有些碑刻还镌刻了乡村或宗族制定的行为规范,严格约束相关人员,如刻于同治年间的鲁山《北来河里社规矩碑》、林县的《禁止开场赌博立石》。当我们看到这些近乎千篇一律的刻板说教,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感触:中国即使处于自身发展的低潮时期,也不放弃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和规范——尽管依靠的还是旧式的礼教制度,但这种约束和规范势必越来越多地带有思考和改变的意义,而不是墨守成规,中国人必将跨越这个看似沉沦无底的艰难时代。
清代河南碑刻的碑文当然远远不如诗词小说来得生动,但是在朴实刻板,甚至严厉无情的碑文中蕴含的历史意义,却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研究工作者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些从石头上移到纸上的史料——这也是对王兴亚先生和他所带领的团队的辛勤劳动的继续。(作者系天津古籍出版社编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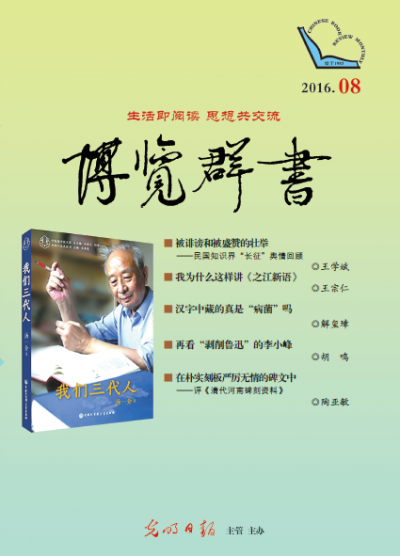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