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前,2000年,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对报考本系研究生的考生进行复试。由于上线考生甚多,而限于招生名额,那次复试需要大比例淘汰上线考生,于是我出了一张相当特殊的复试考卷。这张考卷的难度,在本系招生史上堪称空前绝后——此后我们再未出过难度如此之大的考卷,例如,占70分(百分制)的35道选择题,皆为多项选择题,只要有一项错选或漏选,全题即为零分。那次考试的结果是,数十名考生中成绩最高的一名竟然仅得42分。这张考卷至今在全国各考研网站上还能查到。这张相当特殊的考卷发表后,引起了持续数周的争议。有人痛批这张考卷,说它是“自炫博学的精神早泄”,当然也有不止一位读者发表文章力挺。
那时南京有一位工科大学的学生,从报纸上读到了这张考卷,自己做了一遍,在心里说:出这张考卷的地方有趣,我要去考那里的研究生。一年后他真的来报考本系,而且顺利考取了,成为我带的研究生,后来又成为我指导的博士。
这个学生就是《十世纪前中国纪历文化源流》一书的作者孔庆典。
孔庆典天资聪颖,兴趣广泛,而且风格独特。这里我举两个小例子:一、他在读期间,一直在本系被视为第一号电脑高手。二、他是本系唯一敢向我推荐阅读盗墓小说《鬼吹灯》的学生。
孔庆典治学,沉潜扎实,外表看来却仿佛游戏人间。他又是有治学与写作双重天赋之人。他第一次引起我注意,是某次课程的考试文章,在同学们交来的文章中,他的文章让我有点惊艳之感,知道这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人。
孔庆典的博士论文《十世纪前中国纪历文化源流——以简帛为中心》,是他根据自己的兴趣选定的。在此之前他也考虑过若干个别的题目。我对他的选题几乎没有任何干涉,因为我相信以他的能力,最终写出一篇精彩的博士论文是不成问题的。结果正是如此,他的论文在审查时颇受专家好评,遂以优秀成绩获得博士学位。
中国古代的纪历文化,经过大约一个世纪的“现代化”言说之后,已经被湮没在人为的历史迷雾中。无数当代的读物,要么将古代纪历文化整体视为“封建迷信”、“封建糟粕”而唾弃,要么将它过滤成为“数理天文学”——主要的做法是将纪历文化全方位地过滤掉,只谈论历法中的数学和天文学内容。这种做法的“善良”初衷,是要为我们的祖先在当代公众心目中留下一个“科学”的形象。
但是,这样的“科学”形象当然是虚假的。20年前,我在拙著《天学真原》中,对此做了初步的廓清,力图恢复中国古代纪历文化的本来面目,并说明它在古代中国社会中所发挥的文化功能。那点工作,也许可以算是“筚路蓝缕”吧。
现在,孔庆典在纪历文化的研究上,摆开阵仗,以“阵地战”的气势,全方位地进行了深入研究,其所创获,何啻十倍于我,实在是令人欣喜。我认为他的主要贡献,可以简单归纳为如下三方面:
一、他系统搜集、考证、释读了以近数十年出土简帛为中心的古代文献,全面呈现了中国古代纪历文化的整体面貌和精确细节。
二、凭借过硬的文献考证功夫,发掘出了大量古代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在纪历方面相互交流和影响的证据,勾勒出一幅古代各族文化交流的生动图景。
三、在上述两项的基础上,他为中国纪历文化建构了一幅新的早期历史图景,这幅图景与我在《天学真原》中所勾勒的颇有不同。
孔庆典最后的结论说:“本文所论及的种种纪历周期,则更多地是一种意识的节律和生活的节律,它们是古人对神秘自然力的探索与认知,后期则演变成对传统习惯的因循和对集体生活的认同。”也是非常精当的总结和论断。
在阅读这本书各章时,我脑海中不断浮现出一篇文章的标题——《释支干》。这是郭沫若在他学术盛年的一篇力作,其中充分体现出对历史文献考据的严密和功力,充分展示出对中外文化交流的敏感和渊博。当然,郭沫若诚属大家,《释支干》堪称经典,而孔庆典的《十世纪前中国纪历文化源流》只是学术新秀的初试啼声。但是“怎将我墙头马上,偏输却沽酒当炉?”——异日若将孔作与郭作相提并论,必有谓孔作后来居上者。
孔庆典在他书末的“致谢”中,也谈到了本系2000年那张考卷的故事。他告诉读者:“这些年里不断有好奇的人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要从工科转来读科学史?我每次都能随口说出不同的答案,其实心里同样不甚了了,或许很多行为实际都是盲目,越是振振有词,越是有可能流为虚浮的诳言。”这固然是他直抒胸臆的实话,我们却也不妨给出一种更为浪漫的解读——在他“年少轻狂”的时代,他就是因为那张考卷给他带来的一时冲动而转来读科学史的。
这种冲动奇怪吗?可以说一点也不奇怪。迄今为止,我们科学史系毕业和在读的博士生、研究生已经过百,他们百分之百都是“转行”而来的——因为中国没有科学史的本科专业。这些学生中的许多人,都是具有浪漫情怀的,他们或是对某些学问有特殊的爱好(比如因儿时的某种梦想),或是对某些学问有特殊的厌恶(比如对自己不幸错选的本科专业)。他们投考来这里的时候,根本没有将这里当作世俗的跳板,根本没有将这里当作就业的捷径。尽管最后他们的就业都没有问题。
这种冲动有害吗?对于经常患得患失的中年人来说,也许真的有害;但对于那些握随侯之珠、抱荆山之玉的年轻人来说,这种冲动就像一场一见钟情的热恋,有什么害处呢?事实上,我一直相信,年轻人少考虑世俗荣利,多听从内心召唤,常常是会有好结果的。如今孔庆典已经成长为学术新秀,大家都相信他的学术生涯前程远大。另一方面,他已经开始的“新上海人”生活,也被他安排得妥帖温馨,井井有条。他当年的冲动,给他带来的都是美好的结果。
他当年的冲动,给我带来的也是美好的结果——说实话,对于2000年的那张卷子,仅仅看在它曾吸引了孔庆典来到本系这一点上,我就觉得已经“物超所值”了。(本文为该书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略有改动)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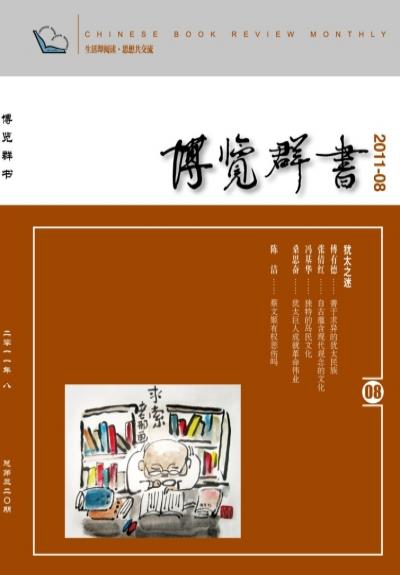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