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谭集》
王学泰先生《燕谭集》(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最引起我兴趣的是“话说游民”这一辑——作者本是率先研究游民文化的先驱,早在许多年前就著有《游民的理想与现实》一书(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版,改题为《中国流民》),收在这里的几篇短文由博返约,于随意谈笑之中发挥其深刻独到的见解,最是益人神智。
王先生说,“游民文化是广大游民与游民知识分子共同创造的。”(《燕谭集》P131)此言极是。所谓游民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当于古人所说的“游士”。中国古代的农民和知识分子都有某种流动性。农民与土地关系密切,一般来说是安土重迁轻易不肯离开故乡的,但过于沉重的压迫剥削、灾荒和战乱往往迫使他们离乡背井,远走他方,这一类的迁徙流浪,史不绝书,另外还有由政府组织的移民塞边等;知识分子则比较自由,为了争取某种政治理想或表明某种政治态度,为了过更好的生活,为了实现人生价值,他们流动起来总是更加厉害。农民的流动一般是不得已的,知识分子的流动则往往是主动的。前者被称为“流人”、“流民”或“游民”(这几个概念 之间颇有些差异,这里姑且忽略不谈),后者则向称“游士”。
春秋战国时代许多士人周游列国,有所活动,孔、孟二圣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孔子提倡流动,甚至发表过“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这种近于绝对化的意见。但孔孟的活动都是为了实行他们的“道”,原则性很强,理想不能实现就回家授徒著书,寄希望于未来,完全是思想家的作派;他们虽然曾经“游”过,但几乎从不被称为“游士”。后来的纵横家则没有什么原则了,谁出好价钱雇用他,他就为谁卖力。顾炎武概括战国时代的风气道:“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先秦的纵横家大约可算是资格最老的“游士”。战国时代的权贵“养士”之风很盛,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尤为此中大腕,他们利用权势和财力收养门客,储备人才,以供不时之需,而这些被养的士也确实为他们的主人、为所在的国家作出了贡献。可见这时“游士”还是在体制之内寻求出路,同宋元以下的游士或今之所谓游民知识分子仍然有所不同。
如果“游士”们在体制之内找不到出路,长期在体制之外作无序的流动,这样的人一旦形成气候,那就会成为潜在的危险。苏东坡在《游士失职之祸》(《东坡志林》卷五)一文中写道:
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他又指出,秦王朝不注意这个问题,单纯地“恃法而治”,结果造成“游士失职”,“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等于是“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由此可知,让游士在体制之内有一定的活动空间,有相当的出路,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苏东坡的观察看来很有点道理。到宋代,“失职”的游士已经日见其多,明眼人不免要先天下之忧而忧了。
汉初的诸侯王继续养士,后来国家设立“太学”,也等于养士,而且将这些知识精英直接纳入到正宗体制之内来。若干儒家大师聚徒讲学,从而游之者甚众,亦复有利于稳定。隋唐以下以科举取士,士人固然趋之若鹜,而在正宗体制之外士人仍然有各种出路,例如在唐代可以游幕,到各地的使府去充当幕僚,这样大批的游士就不至于“失职”了。古代的幕府之中历来是人材济济的,直到近代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之流的幕府中仍然是如此。历代散落于江湖上的游士都不乏其人,古代的政治家懂得要想办法安顿好这些人,不能让他们走投无路,惹是生非。尽管朝廷的爵禄有限,“不能尽縻天下之士”,但相当一部分在野的知识分子总还是能够通过各种形态的“游”,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够“超稳定”,与其内部这种富于弹性的自调节自完善的机制大有关系。
如果士人的出路过于狭窄,游来游去老是没有着落,则必然引起“游士失职”。这样,游民知识分子就会成为问题人物。例如到元朝,大小城市里“失职”的游士比比皆是,蔚为大观。这里就潜伏着很大的危机。
王先生说,古代不能进入仕途的知识分子“有钱的可以高卧隐居,有背景的可以奔走权门,做幕僚清客。一些文化水平不太高的,绝了做官之望,又没有固定的家业,不能高卧归隐,只能流浪于江湖,从事不正当的、或为当时社会所不屑的职业,如做游医、书会才人、做江湖艺人说书唱曲,或为他们演戏打本子等。其他如游方僧道、游食四方没有固定职业的下层文士,皆属游民知识分子之列”。(P130)既在体制之外,又富于流动性,乃是游民知识分子的基本特色。这一批人与通俗小说、戏剧的繁荣关系极大——研究这一段文学史非高度注意这一帮人不可。
游民知识分子能量很大,岂但同文学有关而已,一旦天下有变,这些一向在体制之外乱说乱动、找不到正当出路的“游士”就容易与穷则思变的“流民”结合起来,充当后者的领袖或智囊——这就是苏东坡所说的“为之先”——制造出很大的社会震荡来。元末、明末的农民起义以至太平军的队伍中,都有相当的“游士”加入进去,其结果是人所共知的。
基本上没有文化的土匪历来成不了什么大气候,而流氓无产者加上“游士”的集团则具有非常可怕的能量,在最严重的情况下甚至能够动摇国本、导致改朝换代,元末明初即为典型。研究游士的变迁,认清“游士失职之祸”,至今也还是不可以等闲视之的。
王学泰先生又著有《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近有同心出版社2007年增修本),所论尤为深广,虽然关于文学讲得比较多,其实也很值得史学界注意。
《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
2010年10月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00周年,母系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我本来是计划好回去参加的,不料临时因为健康方面出了点意外,未能成行,殊为恨事。幸而从报纸上看到不少报道,又有在京的老同学及时给我寄来一份《大学》杂志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百周年专号》,稍慰饥渴;而最高兴的是后来又得到温儒敏先生寄赠他所主编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一书,对母系的历史特别是现状得以进一步有了比较系统而且直观亲切的了解。(书中有老照片三百余幅,外间颇不多见;其中有一幅我们班1964年到湖北去搞“四清”时摄于武汉长江大桥之侧的合影,见P130。)一边拜读,一边就冒出许多感想来。
该书序言说,北大中文系的系格,除了具有关注并参与社会的传统以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思想活跃,学风自由,环境宽容,同时具有严谨求实的风尚;二是教学方面注重为学生打下厚实的基础,然后放手让他们各自寻路发展。
这两条总结得很好,我个人也略有体会。我在中文系读了7年本科(1961-1968,后两年是所谓的“留校闹革命”),对自由与严谨并重这一条体会很深。只讲严谨,很容易产出一批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书呆子或学究;只讲自由,则容易催生一批天马行空的活动家。这两种人才当然也各有其用,但到底落入第二义。“各自寻路发展”这一条也很有道理,地上本没有路,只要有人走,路就出来了。我们年级后来出了将军,出了高官,母系并不以培养这样的人为目标,但也不妨有这样的杰出系友并引以为荣——基础打好了,干什么不行?
如果还可以补充一条的话,我想也许是中文系还有一种拼命的精神。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中文系的人走上街头,集会游行,大声疾呼,虽被捕杀头在所不顾,是众所周知的光荣历史;这回我从《百年图史》中又得知,1928年为了反对所谓“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抵制莫名其妙的跨省大合并,“北大师生展开历时半年的护校复校运动,甚至组织‘敢死队’,反对强行实施大学区制”(P271),到第二年,政府收回成命,取消大学区制。为护校复校而拼命,其风骨何等令人神往!如果没有前辈学长的拼死奋斗,北京大学已不复存在,更谈不上什么纪念中文系建系百年了。
“文革”中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服毒自杀于香山,当时颇震动人心。程书记很平易近人,记得他曾到我们宿舍来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和我们谈笑风生;他即使有执行了错误路线的问题,批斗一两回也就罢了(当时这么看),而他竟义无返顾地自杀了!时年38岁(详见P135、244)。后来看去,此乃以死相争,维护人格的尊严,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学生中也颇有因维护人格尊严而自杀的,更可痛惜。我根本不赞成自杀,但对他们的拼命精神非常钦佩。
做学问也要有拼命的精神。西南联大时期,师生生活条件都极其艰苦,还要常常钻防空洞,但依然弦歌不辍,老师们出了许多可以传世不朽的科研成果,学生中涌现了大批高级人才。这是什么精神?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否则就干不成什么大事。
我们60年代的学子比起前辈学长和后起之秀来,自然相当惭愧,但在三年困难时期,也能拖着浮肿的小腿跑图书馆占座位苦读书,在宿舍里囚首垢面而大谈学问,不改其乐,也算是无愧于系格了。那时的中青年教师(其中现在颇有大师级的人物),面有菜色,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一吃过晚饭就跑到三十二斋(中文系男生宿舍)来辅导我们,切磋讨论,不知熄灯时间之将至;老教授也偶尔光临,答疑解难,令人如坐春风。其情景犹在眼前,可惜那时没有照相机,这方面的图片,该书中只得付之缺如。
现在的条件同几十年前完全不同了,学生再穷再苦,也不至于饿着肚子,但认真读书的风气据说不如过去;著名的学术成果大抵出于老一辈学者或比较老一点的先生们之手,中青年教师中特别有成就者固然有之,相对来说总是少了一点。《图史》序言中说,“百年中文系,五四时期的社会贡献与影响最大,二三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前期是做学问与人才培养最下工夫,而且成效也最显著的时期”,也许还应该加上一个西南联大时期——那么,第五度的高端什么时候到来呢?
现在不是革命的年代了,也没有什么整人的运动,按说学问应该做得更好,而事有不甚然者。这是什么道理,实在很难说明白。
(本文编辑 谢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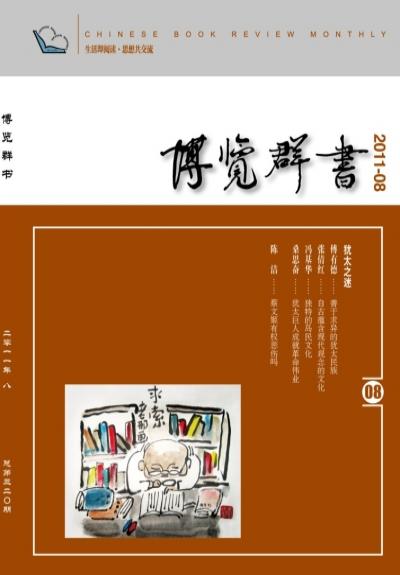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