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宗岱的《晚祷》,总有这样的画面在我眼前涌动:1859年,巴黎南郊巴比松镇上质朴的乡村画室中,法国19世纪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米勒,正若有所思地凝视着一张未完的画作:画中一对农民夫妇沐浴在昏沉的暮色中,虔诚地颔首祷告着,赤裸的双足踏着贫瘠的土地,脚边有两小袋马铃薯,便是他们几个星期的口粮。画家米勒皱了皱眉,迅速地抓起画笔,蓬松而茂密的胡子也随之上下颤动,寥寥数笔,画中遥远的地平线上,隐现出一座小小的教堂。几周后,米勒将这幅原名“土豆的歉收”的画,更名为“晚祷”,在巴黎的艺术沙龙中展出。画中悲凄而圣洁的意境,震惊四座。
1924年,中国广州郊外一所绿树环抱、花荫掩映的教会学校里,20岁的梁宗岱,刚结识了娴静文雅的同班女同学陈存爱。结识虽很传统,他心里却泛起了阵阵爱的涟漪。青涩的恋情很快便因梁家的包办婚姻早早地凋谢。梁宗岱为此写下了两首以《晚祷》为题的诗,纪念这段纯真与悲苦的青春岁月。
一年之后,梁宗岱来到了巴黎,寄居在近郊艺术氛围浓厚的玫瑰村,闲暇时常常留连于巴黎奥塞博物馆。米勒《晚祷》中昏黄的暮色,常映在他清澈而充满理想的双眸中。身处异国他乡,乡愁时常涌上心头,诗人总会默默地吟诵起旧日的诗:
我独自地站在篱边/主呵,在这暮霭的茫昧中/温软的影儿恬静地来去/牧羊儿,正开始他野蔷薇的幽梦。
我独自地站在这里/悔恨而沉思着我狂热的从前/痴妄地采撷世界的花朵/我只含泪地期待着——/期望有幽微的片红/给暮春阑珊的东风/不经意地吹到我的面前:虔诚地,静谧地/在黄昏星忏悔的温光中/完成我感恩的晚祷。(《晚祷》二)
这时,梁宗岱的第一本新诗集正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诗集就命名为《晚祷》。今天,这本初版诗集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橱里。那些负载着诗韵的书页,虽经时光之洗礼,染上了黄色,但只要打开轻轻地翻看(因怕纸线脱落),那一句句诗,仍如夏日清晨晶莹的露珠洒溅至脸上,刹时感到久违的清新。
南国诗人留学欧洲
梁宗岱(1903-1983),祖籍广东新会,1923年,免试保送入广州岭南大学英语系学习。此时的梁宗岱已显示不凡的文才,在培正中学期间,他主编了《培正学报》、《学生周刊》(或称《学生周报》)等,同时以“菩根”笔名在广州各大报纸发表新诗,在商务印书馆刊行的《东方杂志》、《学艺》、《太平洋》、《学生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作品。中学和大学时期,他写了200余首新诗,被誉为“南国诗人”。1921年时,郑振铎、沈雁冰从上海来信,邀请梁宗岱加入文学研究会。他成为文学研究会的第一个广州会员。
1924年,梁宗岱深感岭南大学已无法满足他与日俱增的求知欲,决意赴法留学。1925年秋天,梁宗岱踏上了梦想中的法兰西土地。欧洲留学生涯令梁宗岱超高的悟性和无穷的精力,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1926年春天,梁宗岱经朋友介绍,结识了法国文坛巨擘、后期象征派诗人保罗·瓦雷里。梁之文采深得瓦雷里赏识,二人交往密切。梁宗岱在巴黎,每天用法文写新诗和译中国的古诗。梁的法译本《陶潜诗选》由瓦雷里作序在巴黎出版。
1927年初秋,梁宗岱陪瓦雷里在绿林苑散步,瓦雷里向他讲述了自己的长诗《水仙辞》。从这时起,梁宗岱开始翻译这首长诗,直至1928年7月12日译就。这期间,梁宗岱还结识了法国文坛的另一位巨匠——罗曼·罗兰。
1929年10月,梁宗岱拜访了罗曼·罗兰。他将译成的陶渊明诗文稿寄给罗曼·罗兰。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即回信盛赞:“这是一部杰作,从各方面看:灵感、移译和版本都好……”
留学期间,梁宗岱著述颇丰。所译瓦雷里的名诗《水仙辞》和所作《保罗梵乐希先生》发表于当年的《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上,他第一个向国人介绍了这位法国杰出的象征主义诗人。翻译的法文本《陶潜诗选》出版后,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1930年,梁宗岱从巴黎到德国柏林,在海德堡大学学习德语一年,结识了冯至、徐梵澄,又熟练地掌握了德语。
1931年1月,《诗刊》创刊,由上海新月书店发行。创刊号发行不久,远在海德堡大学的梁宗岱,写了一封长信给《诗刊》主编徐志摩,畅谈读了《诗刊》创刊号后对中国诗歌以及新诗建设的看法。4月20日,《诗刊》第2期刊出了他于德国花了三天写的长信,加了一个标题《论诗》。
与梁实秋的论战
1931年秋,梁宗岱赴意大利,欲入佛罗伦萨大学学习意大利文,此时接到国内北大和清华的邀请。梁宗岱接受了北大的聘书,准备回国,临行前他向罗曼·罗兰告别。罗氏因父亲逝世及大病初愈,闭门谢客,却破例接待了梁宗岱,且长谈四个多小时。1932年,年仅29岁的梁宗岱任北京大学法文系主任兼教授,又兼清华讲师,一时名动北平。
梁宗岱在北大仅停留了两年,1934年便辞去教职。辞职之因,是一场婚姻诉讼。梁之原配何氏,虽已另嫁他人生儿育女,但得知梁游学归来当上了大教授,遂追至北平要求共同生活。梁宗岱坚拒不纳,于是闹上法庭。一向主张接纳原配夫人的胡适,亲上证人席,为何氏辩护,指责梁宗岱抛弃发妻,梁宗岱因而败诉。梁宗岱最终赔偿赡养费两千元,办理了离婚手续而了结此案。
梁宗岱离开北大后,旋与女作家沉樱在天津结婚,并至日本度蜜月,回国后任教于南开大学、复旦大学。这时的梁宗岱发表了一系列诗论之文,如《新诗底纷歧路口》、《论长诗小诗》、《关于音节》等。此时,他与中国诗坛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梁实秋,就诗歌观念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论战”。
梁实秋针对梁宗岱在北京大学国文学会作的《象征主义》的演讲,发表《什么是象征主义》一文,用象征主义是“神秘主义”,“象征主义的文学,不过是捣鬼,不过是弄玄虚,无形式,实在亦无内容”,“象征主义者无疑的是逃避现实”等论调来嘲讽梁宗岱。
1936年,梁宗岱的译诗集《一切的峰顶》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发行。梁实秋再次在《自由评论》第25、26期合刊上,发表了书评《诗与真》,认为梁宗岱的“象征主义是一个迷迷糊糊的东西”,“他不能用简单明白的理论与文字来解说,愈解说愈使人茫然”。此外,梁实秋还尖刻地指责梁宗岱的专著是“不用常识,不用理智,不用逻辑方法去思维”,而是“用感情,用直觉,用幻想去体验。这种性格,本来宜于写诗,因为不宜于做旁的事,不过若趋于极端则变为病态。这种性格不宜于说理,因为在说理时是用不着感情、直觉与幻想的”。
为此,梁宗岱写了《释“象征主义”——致梁实秋先生》一文,来回应梁实秋。在这封公开信中,梁宗岱先是心平气和地指出梁实秋“过去的文章底立场”距离自己太远,“立论又那么乖僻”,以致自己和他的朋友都认为梁实秋,要么是“意气之争”,要么是“不宜于做诗乃至谈诗的”性格。随后,梁宗岱直取梁实秋的“诗必须明白清楚”的诗歌理论,认为梁实秋“缺乏哲学底头脑,训练,和修养,实在达到一个惊人的程度”,因而看不懂自己“关于‘契合’的理论,却是植根于深厚的哲学里的”。
可以推想,当年与著名诗人瓦雷里和罗曼·罗兰之交往,全面升华了梁宗岱对诗歌的认识,他从仅凭一腔灵感作诗,转而开始深刻地思考和探索中国新诗的命运,也由此改变了梁宗岱之后60多年的人生轨迹,他由一个诗人、歌者,过渡至一位诗歌理论家。
唯一的诗集《晚祷》
《晚祷》是文学研究会早期所出的丛书之一,1921年至1937年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为48开的小版本,薄薄一册,盈盈一掌之大小。青灰色的封面中间,印着竖排的书名,右上角署作者,左下角印有“文学研究会丛书”的字样,均为竖排,仅在封面下部横排着“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全书装帧十分朴素,不着任何纹饰图案,但透出典雅之气息。
唐弢在《晦庵书话》曾写道:“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里的诗集,开本和《旧梦》一样,尚有王统照的《童心》、朱湘的《夏天》和梁宗岱的《晚祷》。”《晚祷》的初版于1925年3月(民国十四年),第二版重印于1933年4月(民国二十二年),与初版不同的是在版权页上,加印有“国难后第一版”字样。原因如《晦庵书话》所说:“商务书版,大都毁于‘一二八’炮火,以后重印,版权页上一律注明‘国难后’第几版,留此数字,以志不忘,倒也颇有意思。”《晚祷》全书共收录了梁宗岱1921年至1924年所作之诗,共19首。最初的诗是写于1921年7月的《失望》,最末的诗是1924年6月的《陌生的游客》。
《晚祷》是梁宗岱一生惟一出版的诗集。他曾回忆自己创作《晚祷》时的心境:
那是二十余年前,当每个人都多少是诗人,每个人都多少感到写诗的冲动的年龄,在十五至二十岁之间。我那时在广州东山一间北瞰白云山南带珠江的教会学校读书。就是在那触目尽是花叶交荫,红楼掩映的南国首都的郊外,我初次邂逅我年轻时的大幸福,同时——这是自然底恶意和诡伎——也是我底大悲哀。也就在那时底前后,我第一次和诗接触。我和诗接触得那么晚(我十五岁以前的读物全限于小说和散文),一接触便给它那么不由分说地抓住(因为那么投合我底心境),以致我不论古今中外新旧的诗兼收并蓄。于是,踯躅在无端的爱乐之间,浸淫浮沉于诗和爱里,我不独认识情调上每—个音阶,并且骤然似乎发见眼前每一件事物底神秘。我幼稚的心紧张到像一根风中的丝弦,即最轻微的震荡也足以使它铿然成音。
《晚祷》用象征主义的手法写成的,如以翠竹上的晨露,象征悲苦的泪珠,以白莲在碧池中碎落,暗示爱情失意的痛苦等,显得既含蓄又自然,体现出一种新的美学追求。如《暮》:“像老尼一般,黄昏/又从苍古的修道院/暗淡地迟迟地行近了。”
梁宗岱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忠实地实践自己的诗歌理论。他对所定义的“纯诗”如此解说:
所谓纯诗,便是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借那构成它的形体的原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的感应,而超度我们灵魂,到一种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像音乐一样,它自己成为一个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朽的宇宙;它本身底音韵和色彩密切混合,便是它底固有的存在理由。
他留下的这些诗论,早被后来的现实主义掩没;静不下心来的后人,怎能去接受独立、自由像音乐一般的诗呢?
纯粹之诗人早走了,他离今天浮躁的人心、社会也太远了些。今天的我们,仿佛成了梁所说的诗国“陌生的游客”。就用诗人90年前的一段诗作结吧:
什么,陌生的游客?你的面庞/这样的绯红,呼吸又这样微细/可是严冽的秋霜,已紧压你的心苗/虽然青春还荡漾在你的脸上?/……我不是为采花而来!
(本文编辑 李文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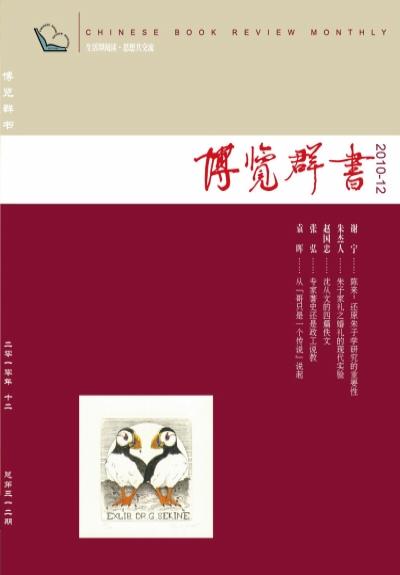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