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什么样的重新审视
韩毓海教授的《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以下简称“韩著”,引文只注页码),书名有一种前无古人的气概;然而他在绪言中却说自己在这段历史方面的学术工作“其实完全就是学习的过程”(P1),还说这本书“当然不能算是史学,连历史研究可能也谈不上”(P18)。一本开篇就在剖白著述情怀上自相矛盾的书,却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多次重印,实在值得人深长思之。
自民国以来,对明清两朝衰亡原因的探究就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从蒋廷黻、钱穆、郑天挺、郭沫若、吴晗到胡绳、商鸿逵、毛佩琦、黄仁宇、徐中约……名家迭出,成果斐然,有的已成学界定论。韩教授既然发出“五百年来谁著史”的宏大疑问,是不是对上述名家公论做过仔细的梳理、提出了有据的疑问、有了全新的看法呢?
通观韩著我们不难发现,韩教授不仅没有认真去推陈出新,而且对中国现代史学家很是轻蔑甚至不屑,如“晚清和民初就有的议论,它终究要流于一种耳食之谈,沦为与历史和现实实践脱离太远的空洞教条”(P5);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观点错误,需要重写(上篇第6节);“钱穆、傅孟真以来的‘民国历史学家们’一直坚持的,也是至今一般教科书上所能够告诉我们的……这种表面化的解释是最无力的”(P135-136);“当代中国人将鸦片战争的失败,简单地归结为英国的‘船坚炮利’和科技文明之类的说法,就几乎是完全不着边际的……唯一值得参考的中国著作,可能也就是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了”(P207)……
韩教授说他写此书的目的,是“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并将其重新审视的框架概述为三个支点——“基层组织”、“财政金融”和“世界大势”。他的基本结论是:首先“官无封建,吏有封建”造成了基层失控,其次缺乏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却以大量进口白银作为基准货币造成金融失控,这是中国在明清两朝由盛而衰、“中国文明的辉煌、中国经济的发展才变得不可持续”的根本原因(P22-23)。韩教授还在“下篇·导语”部分进一步阐述说,中国被西方打败的主要原因是“三个脱节”:一是国家与社会脱节,造成了“文化帝国”的弊端(政治上依赖地方社会自治、经济上依赖社会互助);二是中央与地方脱节(边疆和藩属国治理主要依靠松散的文化认同,国家不知何为);三是生产和军事脱节(市场发展的高度平衡反而导致了积累的下降和军饷的缺乏,如此兵制不能对抗英国的军商合一)(P176-177)。
韩教授的这些“重新审视”,其实不过是从美国的所谓“加州学派”那里转手而来(最多加上一点对钱穆、黄仁宇的生吞活剥)。作为一家之言,大陆史学界对其并不陌生;但像韩教授这样综述趸卖即定为确论,俨然要以新换旧横扫百家者,实在罕见。在存有明显盲区的情况下进行的“重新审视”,就难避空疏笼统、无知无畏之嫌。
有力印证还是以偏概全
历史学家回望历史,并不热衷于使用当下的知识体系去评述历史事实,而更倾向于以一种“在场者”的眼光去打量历史的原委。“事后诸葛亮”似的言说,只是茶客的谈资,不是史家的研究。韩教授却似乎更热衷于将这样的言说写进书里。
用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观来揣度中国传统社会、并以此衡量政权的“强势”与“弱势”,绝不合理。在宋明两代出现的早期市场经济中,“国家缺位”确有踪迹,但其根本原因并非“市场发展的高度平衡”,而是政权性质本性使然。因为“天下太平”(也就是皇家统治的稳定)与否,才是其命脉所系、心思所在。至于其与现代国家相比在工商运营和税收征管方面的相对粗疏,那是因为自汉代“盐铁专卖”形成以来,统治者早已热衷于通过垄断的方式“与民争利”,或通过巧立名目的加赋添捐来压榨民间财富;对肆无忌惮的国家权力来说,“经济生活的数目字管理”,不啻于舍近求远自讨苦吃。以出卖盐业垄断权而换来军事后勤外包的“开中法”,虽然有助长奸商从中渔利的弊端,但是统治者最愿意接受的省心方式。至于明代以来是否已经具有今天意义上的货币金融,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究竟是“货币进口”还是铸币原料(即商品)进口,这些都值得多加斟酌。
诚如韩教授所言,“基层失控”的确是传统社会的特征,但历史上的基层失控绝非仅仅因为“官群体”和“吏群体”的管理技术差异,而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属性和权力机制决定的——皇家要天下太平,官吏要上司垂青,凡与之无关的,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参见任恒俊《晚清官场规则研究》第2章“做官与做事”)。再说,在封建王朝的制度层面(对秦朝以后的中国是否应视为“封建社会”,史学界现有讨论,本文仍沿用旧说),吏与官的关系本是一种“幕僚关系”,权力行使是由官向吏的单向制约;而吏属对官员的对抗,却只能是技巧层面或心智方面的“隐形对抗”,属于“庶人用暗器”的范畴(参见吴思先生《血酬定律》一书“正编”第7章)。如果仅仅从今天的国家职能上去衡量封建官吏,并且武断地认为是官员群体缺乏基本的经世治国之才,才导致从事技术性工作的“吏”隔绝了国家与民众,这显然是舍本逐末。如果明清的衰亡仅仅源于社会治理的技术性问题,我们还需要改良立宪、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吗?
我们不妨看看最切近的实例:如果说是“官无封建,吏有封建”而导致了基层失控,那么民国时期基层政权的建设,已经深入到了对保、甲长等基层公务员的任命,而事实上“基层失控”的问题没有得到任何改进。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完成的高度基层动员,所依靠的绝非是简单的统治权力向下延伸,而是建立在“土地革命”这种深刻的社会变革基础上的。韩教授自己也说是“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之密切结合……才谈得上今天的‘伟大复兴’”(P3)。这和他自己的“货币体系-基层控制决定论”,怎么统一呢?如果说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其实质不过是“货币财政”和“基层组织”的改变,请问哪一位革命者会同意?
一家之言还是一孔之见
韩教授在绪言中说:
知道了西洋怎么样,就照猫画虎,开口即说中国怎么样,看了明代初期怎么样,就说明代如何如何,那么历史研究就变得索然无趣,好像几个公式就能解决问题似的。(P10)
但韩教授对近500年世界史的归纳显然有流于公式化的倾向:他对明清衰亡的解释都是“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他所谓“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货币财政,同时看到世界大势”,不过是简单地“货币金融体系决定论”:为了寻找该体系失败的原因,才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的基层建设,再与该体系成功建立的西方作一对比。而这样的论述还可以进一步简化,归结成两个字——“白银”。仿佛只要解决了白银作为基准货币的问题,中国的衰落就可以避免。这当然是违背常识的。
中国近代的衰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多年来,历史学家们的研究虽各有侧重,但其实是多种问题的陆续提出,而不是以一个问题代替所有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衰落不是一个因素(例如闭关锁国、军事技术落后或者统治阶级腐败)所决定的。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它受制于“多种力量的合力”(恩格斯语),有时甚至是大量模糊性和偶发性事件的聚合,才呈现出某种历史的因果关系;而辨析、确认、分析这些因素各自的态势和作用,正是历史学家的基本课题。以历史发展规律说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其基本观点也只是历史呈阶段性的向前发展的态势,而决不是某种单一因素的决定论。但在韩教授的研究中,明清以降的中国史,显然是由经济因素和基层控制技术两个原因所决定的。他甚至将鸦片战争的中方战败归咎于缺饷,又将缺饷归咎于国贫,再将国贫归咎于缺乏独立货币金融体系——这种一语定乾坤的方式,明显是将历史研究泛文学化了。
中华文明在近代的衰落,民国以来的中国历史学者多坚持外患与内乱的“双重作用说”。如徐中约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认为是“中国内部的腐败和外来帝国主义的羞辱性掠夺,如同一对孪生恶魔,给中国带来了长时期的衰落”;郭廷以先生在《近代中国史纲》中提到: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中国内部秩序已不易维持。即令无外来的冲击,清的治权已不易保,对于虎视眈眈的西方强敌,又焉能抵御?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则追溯到中唐,认为近世中国的“病态”其实是长期以来积聚的痼疾,而清政府对知识分子的严酷政策,使士大夫“趋利避祸”,“故使世运益败坏于冥冥漠漠之中……而中国政治、社会之百病,遂全部暴露。”1949年以后,秉持马克思主义史观的研究者多认为是“封建王朝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了中国的衰落,有幸被韩教授认可的胡绳先生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理论的代表。对这些观点,韩教授竟然一概视而不见。
“国家能力”是由多种因素复合而成的社会历史现象,其中包括了“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李慎之先生语)、政治体制或统治方式、经济形态和生产效率、财富的积累方式和消费模式、军事制度及军工技术……国家实力的强弱对比,实际上是上述诸因素的综合较量。也许对某些读者来说,所谓“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韩著封面勒口)的观点,不乏新鲜感。恕我直言:一个历史学者说某个国家战败是因为“国家能力不足”,而不从上述诸方面探讨“国家能力”的成因,那就好比医生说一个人病死是因为“肌体不健康”,而不去确认病症和病因,那是令病家哭笑不得的。
缺了些基本功
历史学家的研究是以史料为基础的,即胡适所说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韩著的一些观点并没有建立在确凿的史料基础之上。例如这本书最基础的观点——明朝以来中国白银的大量进口——书中仅使用了一条史料:明崇祯十年福建晋江景教堂刊刻、意大利籍传教士艾儒略撰写的《西方问答》中一段对话。这个对话,让韩教授认为“非常关键”,并且说明了“明代中期以降,中国的大部分白银供应依赖向西方进口”(P117)。仅仅以一个普通外国传教士的谈话记录(还没有说明与他对话的中国人是何身份、发生在什么场合),就断定中国白银大量进口——这样的论证方法很值得商榷。
任何经济史的研究,都需要对详细的经济数据加以分析。而通观《五百年来谁著史》全书,竟找不到几处对原始经济数据的引用,全文所使用的几乎都是“大量”、“丰富”、“缺乏”这一类模糊性词汇,或者直接就下了论断,这就造成了论证的无力。如韩教授既然认为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因为白银而与世界挂钩,那就应当详细说明世界银价的波动对中国的财税、物价等问题带来的具体变化,或者直接指明中国的哪些经济领域必须遵循西方货币规则进行结算,等等。很遗憾,韩著通篇没有与之有关的论述,这种“全无新料弄新知”的方式,绝不应该是学人论史的理路。——也许他认为国外的学者已经把这些都说清楚了,他只需沿用他们的结论就行?
对于清朝的衰亡,韩教授的论述更为苍白。由于没有数据的引用,我们也只能知道“清朝大量进口白银”这样大而化之的“史实”,却并不能明白白银流入与清朝经济间的确凿联系。韩著的论述甚至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白银流入中国好似现在的人民币伪钞进入大陆,这完全有违学界公认的常识,即正是中国在早期的中英贸易中收益丰厚,英国为了平衡巨额逆差,又没有可资交易的对华大宗出口,这才开始鸦片贸易的。还有学者将中英贸易顺差的收益解读为成瘾性消费品的出口,也说明鸦片战争之前的贸易顺差对中国是有益无害的(参见仲伟民:《茶叶和鸦片在早期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观察19世纪中国危机的一个视角》,《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
除了缺乏史料作为论证基础,韩教授对引用的史料还存在许多误读。例如他认为元代将漕运改走海道,是“将海洋与中国内陆联系起来,这是中国面向海洋的一次革命”(P55),事实上这不过是一种交通手段的运用,与面向海洋的文明扩张行为性质完全不同。再如韩教授认为英、俄两国没有参与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不具备处理“世界事务”的意义,而《尼布楚条约》不仅涉及中俄,还有法国传教士张诚的参与,并引入蒙古地方法,所以成为国际法的鼻祖(P108)——不考虑《尼布楚条约》的影响范围,将或然的联系解释为必然的联系,这样的论述也缺乏科学精神。
韩教授这种粗枝大叶的引证,在关于鸦片战争中的技术差距问题上酿成了一个大错:韩教授转引罗志田等学者的研究,强调“即使在鸦片战争的时代,火车、电报、铁甲军舰等现代科技手段,对于中英双方而言也还都是未知之物,换言之,近代以来象征西方‘先进’、‘优越’的‘船坚炮利’,在鸦片战争时代基本上还不存在”,“所以当时中英双方科技实力大致相当,所谓中英之间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根本不能成立”(P191)。对这一大违历史常识的观点,我甚为奇怪,查看韩教授转引的出处——罗志田教授著《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发现原文乃是:
应该提请注意的是,马戛尔尼访华时英国的工业革命不过刚刚起步,鸦片战争后中国人了解到的(对时人特别是后来的史家越来越具有象征意义的)先进西方工艺产品如轮船、火车、电报及快速连发枪等,对乾隆帝和马戛尔尼同样都是未知事物。换言之,近代象征西方“先进”或“优越”的“船坚炮利”,那时基本不存在。
结 语
谈史与著史,不是一回事。韩教授知识的广博和思维的活跃都令人佩服;但韩教授一会儿用技术性分析取代历史现象的定性分析,一会儿又用简单论断来代替必需的数据分析,用这样的“学术工作努力”来横扫一个学术领域,就难避 “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的嫌疑。韩教授在绪言里说“这当然不能算是史学,连历史研究也可能谈不上”,大概是为了谦虚,却不失为自知之明。
中国的近代史是屈辱的,从情感上讲,我们都不愿意接受中国近代的衰落是一种必然过程的观点,而宁愿相信是出自某种技术性失误的偶然,甚至宁愿选择许多“排除消极面”的假设:假设明朝高度的商品化生产带来了国家的近代化;假设皇家的财富转化成为科技进步的源泉;假设慈禧太后没有挪用海军费用修建颐和园……但这一切假设除了带来阿Q式的精神胜利,别无他用。韩教授将历史归于简单因素的努力,无疑为类似的想法提供了土壤,这或许是韩著畅销热卖的深层原因。这种共鸣中透露出的今天某些国人的历史诉求,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倒真是值得社会学和历史学界认真关注、仔细思考、深入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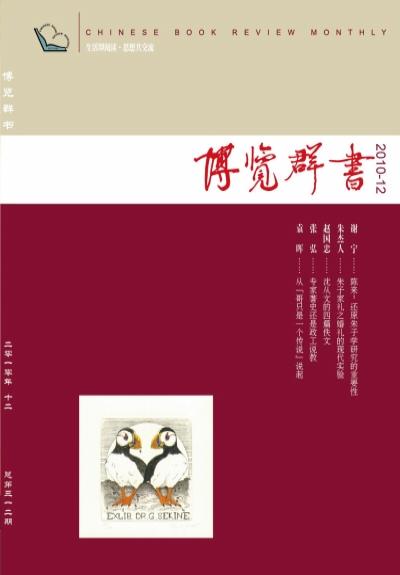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