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相当于博士
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神甫曾说,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一个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作哲学家的人来统治的。
这里所说的全国,自然指的是利神甫当时亲历的中国。不过,利神甫的话会让今天的人读来有些糊涂,也就是所谓统治国家的哲学家云云。这是利神甫作为一个虽然博学却终是蛮夷的外人角度直接导致的。
利神甫指认的哲学领域,当然就是科举考试。并且,利神甫还十分对位地将科举考试的等级出身,用西方人认同的学位表示:秀才相当于学士,举人相当于硕士,进士相当于博士。这样的类比,果然形神兼备,也让习惯于用本土的今天诠释古代和异域的人,感到十分亲切。拿了丈人钱财到欧洲懒散的方鸿渐,被丈人逼宫取博士学位当回报的契据,其振振之辞云: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贤婿似宜举洋进士,庶几克绍其裘,后来居上,愚亦与有荣焉。孝廉公对仗洋进士,这位在上海开铁铺子发了财的点金银行经理,倒和几百年前的洋和尚,有息息绵绵的沟通呢,所以无可辩驳地让鸿渐用40美金从爱尔兰人手里赚来了被称为和清华大学齐名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
当然,得承认,用学士对等秀才,在今人的眼光里,会觉得略略降格,而相关的,举人之于硕士,又不免打进了若干水分。不过,利神甫的立论自有他的道理,因为作为科举考试出题题库的四书五经,正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著作。其实,让利神甫感到奇怪的,并非四书五经的哲学意义与否,而是仅仅凭借对这几部哲学著作的熟悉,就可以掌握对国家权利的捭阖。按照利神甫自己的说法就是,委派即便是最有势力的大臣的根据,主要是候选人所写文章的好坏。
这种奇怪,在利神甫本人,倒并没有得出什么惊世骇俗的结论,反倒有善良温和的解释:从帝国建立以来,人们就更愿意学习文科而不愿从事武职,这对一个很少或没有兴趣扩张版图的民族是更合适的。不过,这解释让敏感的人听了,也不能保证就不会生发积贫积弱祸由此出的感慨。
按照历史教科书的训教,欧洲思想正式跟中国接触,是在明朝中叶以后,所以天主教徒常说那时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不过按照那位方博士从线装书里趸来的论断,明朝天主教士带来的科学现在早过时了,他们带来的宗教从来没有合时过。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
这样的结论虽然有实证主义的嫌疑,但的的确确是心脏位置没有偏颇的中国人说的。所谓传教士带来的科学过时云云,倒是值得商榷,因为即便到了戊戌维新的时候,中国必须占据地球中央的理念,仍然不可撼动;倒是本土的传统,可以存续几个世纪而照旧顽固,譬如科举。
考试的流弊
从进化的角度讲,相对魏晋以降的九品官人法而言,隋唐开辟的取士制度,自然是一种进步,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点评,用非我族类的异己眼光,阻断了平民致身通显的路数。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科举的目的,在于选拔统治人才,但它所提倡的读书方式,却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固然表征了读书的某些重要,但读书的目的,却也同时发生了狭窄性的偏斜。生物界的某些进化,同时也是退化。说这话的老前辈,真的具有预见性。
无论什么人,只有通过读书,考过了科举的四六级,就可以做官,这当然体现了考试制度的某些优点,但也同时印证了考试的流弊。
周作人在讨论中国的国民思想时认为,正是这种考试制度,使得本来很平常很健全的中国思想,生出了毛病。为避剿袭嫌疑,以下不妨抄录原话:
考试制度最大的流弊的两点:第一,因为作文章不肯说真话,完全是说谎。我们平常作文学的文章,自己照自己的思想去作,今天心里高兴,写出来的文章,就是高兴,今天有悲伤的事情,写出来的文章就是悲痛的,但是考试的文章却不能如此,虽然我有很悲痛的事情,在考场上出了庆贺皇太后八十万寿的题目,就非得作颂扬的文章不可,因此千余年来,中国人作文章的本领很好,一般外国人,特别是友邦人,说中国人的宣传本领很好,这就是由于千年来学成的遵命文学的缘故。人家说杯子是圆的,我就作一篇杯子是圆的文章,人家说杯子是方的,我就作一篇杯子是方的文章,就是有人说这不是杯子,我也照样可以作一篇文章,于是文章完全依据题目去作了。我们从前学作论文,先生就是这样教,若不这样做,文章就作不好。但这种文章,决不是自己的文章,完全是替题目说话,弊病很大。第二,是胡说八道。从前在书房里作什么《汉高祖论》、《管仲论》,谈论一二千年以前的事情,汉高祖怎样与匈奴作战,我们完全不知道,怎样作论文呢?结果只好乱说了。如果向来大家都说汉高祖如何的好,你能翻案,说他如何不好,这便是更好的文章了。有了这样的好文章,一旦考中,点了翰林,做了御史,就更可胡说八道了。从前汉高祖打匈奴都可批评,都可以骂,何况是现代的人?因为有考试,所以要作文章,因为作文章,所以不说真话,胡说八道,这种习性养成之后,于是把中国的国民性弄坏了。中国儒教的思想,原来并不是如此,孔子对子路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才是真实的知道,可是因为考试制度,把这点精神完全丧失了,变成说谎同胡说八道,因此只在文章上讲空论,真实的学问一齐都不发达了,科学也因此不能发达了。(《中国的国民思想》)
周作人的话,按照他的逻辑,实在是说考试之害人乃至误国,这样醒目的立论,不能说都对,但也的确不能说他说的不对。利神甫也曾提到,“在这个国家有一条从古代帝王传下来并为许多世纪的习俗所肯定的法律,规定凡希望成为或被认为是学者的人,都必须从这几部书里导引出自己的基本学说。除此以外,他遵循这几部书的一般内容还不够,更为困难得多的是他必须能够恰当而确切地按这几部书所包含的每一条具体的学说来写作”(《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利神甫眼里所谓更为困难得多的,正是周作人提到的经过考试制度历练出来的令外国友邦人士惊诧钦佩的文章本事。
利神甫也体察到了科举对中国国民思想的影响,他看到,这里每个人都很清楚,凡有希望在科举也就是利神甫所认为的哲学领域成名的,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钻研数学和医学等等,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也就是科举门砖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
有趣或者巧合的是,周作人在论证考试制度流弊的时候,也例举了医学。虽然中国的圣贤们认为,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因为两者都可以救人,当然更是安全糊口的高端和底线。尽管医生担负的是人的生命,但这种纯粹哲学意义上的道义,并不被大家看重,从事这种行业的,都是不第的童生或者失业的塾师。他们姑且行医,同时还在准备着赶考,因为考中之后的飞黄腾达,是通往良相哪怕良相以下若干阶梯的功名,那是人生足以自豪的幸福顶峰。行医不过是解决生计的权宜手段。这便是祖国传统医学永远不得进步发达的一个死穴了。
歧视到歧途
周作人还拿日本做说明,说他们本来很受中国思想的影响,但于科学态度,却大有不同,因为首先他们没有考试制度,其次明治维新之前绵长的封建制度,也规定了做医生的及其子孙永远需要做医生,没有考试攫取功名的任何可能,于是他只好只能沉湎于此专心于此,一代复一代,经验积累,更探求西洋人的诊治手法,终于得以进步。
考试的流弊,大概更直接的还在于,考试如果仅仅作为一种统治人才或曰做官者的甄别方式,也还罢了,但它同时又作为了一种教育的制度,而这种教育制度的目的,却仍旧在执著于成为统治人才,这便是了一种令人担忧的游离。换句话说,用考试的方式让人读了书之后去做官尚且无可厚非甚至足可发扬蹈厉,但是让所有的人读了书只是为了经历考试去做官僚,就是一种歧途了。徐大椿的《洄溪道情》里面,有一首曲子叫《时文叹》,正是写照:“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计。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1917年,梁任公到全国教育最高机关的教育部做讲演,说的正是现在教育未脱科举余习,虽然形式上采用新式教科书,而精神上仍志在猎官,与科举无甚出入,即班固所谓利禄之途。任公说:
鄙人前在日本时,遇后藤君,叩以台湾教育,后藤君谓台湾教育,无法办理,该处人入学校,即志在做官,不做官即不入学校云云。当时余闻是言,心中颇有感触,岂独台湾,中国全国,亦何尝不然?其时中国初办教育,学校尚未完备,而主持教育者,仍沿用科举之方法,惟知奖励学生做官,如学生毕业奖励,留学生考试分部章程,纷纷颁布,此在他人所深恶痛绝者,而吾国方竭力奖励之不暇。夫以二千年来之恶习,久已深印吾国人之脑筋,极力矫正,尚恐不足,而况加以奖励,其结果尚可问乎?至今日其险象已露矣。即西河沿一带客栈,求官者多至数万,遑论他处?此时教育尚未能普及,已有此现象,假使将来教育普及全国,人皆有做官思想,试问何以应付之?(《现代教育之弊端》)
宋朝的人说:“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自有千钟粟;读,读,读!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刺激读书的著名口号,尤其对于贫寒交迫的苦孩子,锥刺股,头悬梁,一步登天,衣锦还乡,让仍在蓬蒿之中的故旧乡人挤挤挨挨地瞻仰自己,虚荣的满足是不待言的。只是,大家若是都将做官之外的行为视为蓬蒿,那又靠谁来支撑社会呢?做官,用现代的时尚话头表述,可以说是一种人力资源管理,只是这管理的饭碗,端的比较他人更加结实。如果大家都去梦寐端这饭碗,也许这饭碗便不免端不大结实了。因为这饭碗之下,再没了作为资源的人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饭碗存在的意义,果然大可置疑了,这时候再仅仅看到考试种种,给予了苦孩子什么机会,就显得十分的乏味。大概不能说,苦孩子就更比别人有权利享受陋习吧,这就如同对未开化人群的过分重视,实际上等于对其他人群的歧视。不论对谁,歧视总是不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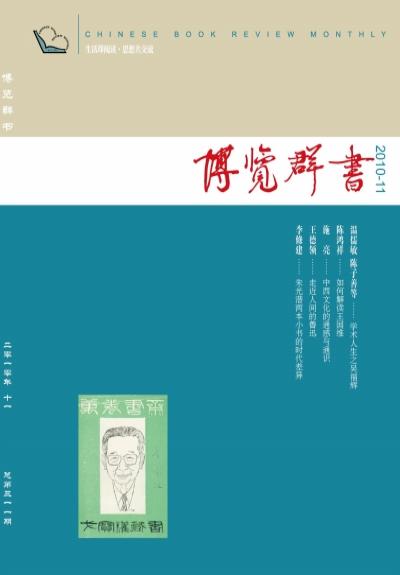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