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家里有学者家都会有的东西:顶天立地霸占一整堵墙的大书架、复印的港台版书、凌乱的书桌书稿等,但他家还有几样一般学者家不多见的东西:梭镖、跑步机、围棋盘边上的大瓶可乐。
所以,他会做一般学者不会做的事情,也就不奇怪了:出很不像学术著作的畅销“学术著作”,点名骂人,亲密拥抱市场。我手里拿着他的《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一书,敲门。张鸣开了门,核实了身份,将我延至阳台上的围棋桌前,便开始说:“我吧……”我瞪着他,有点傻了。我的手还插在包里,笔、纸、录音笔一样都没拿出来,一句开场白都没说呢,他已经说完第一段“家世”,开始第二部分“童年”了。
天生一个倔强的人
新中国成立之前,开始在东北北大荒垦荒建农场时,一对江南上虞的国民党俘虏夫妻便被发配过去。在全国大鸣大放那一年,他们的第四个儿子出生了,取名“张鸣”。这个以“鸣”为名的孩子在农场出生和长大,有着还算快乐的童年回忆。小时候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到处迁徙,天高地阔,管束又少,自由自在,为所欲为。张鸣是野生的、放养的,小时候蓄着的一股子蛮荒之气,一直留到今天,从骨头缝里嘶嘶地往外漏。
“文革”前夕,一家人回到农场。刚开始上小学、学文化,文化就“革命”了。张鸣当时9岁,小家伙开始很是兴奋了一阵子,天天去学校,但不上课了,烧书玩儿。但很快他就觉得不好玩了。那是一件很可悲的事儿,一个孩子,刚开始会看书,就没书可看了。他感到了饥渴,到处找书看,倒是因祸得福,反而看了不少书。
两年后的1968年,父母双双被关起来了。张鸣和大他4岁的哥哥两人在家,独自生活,活得很艰难。不仅是两个半大的男孩要管柴米油盐,而且作为“地富反坏右”贱民,会被别的孩子追着打。对于制度性挨打,哥哥的态度是受着、忍的、躲的,可张鸣不,这孩子性子倔,脾气大,想法还老跟别人不一样,天生的离经叛道。谁骂他,他一定骂回去,谁打他,他一定要打回去。有时候被打得厉害了,嘴巴都肿了,张不开口,吃东西只能一点儿一点儿往小缝里塞。饶是这样,下次碰到挨打,照样还是还手,一点儿不怯,就是不服。后来别的孩子也就“懒得”打他了,因为知道他每次都反弹,而且都不要命,镇压起来也不容易。所以,挨打多的,还是哥哥。
张鸣去监狱给父母送东西,看守纯粹是为了取乐,要张鸣表态,骂自己的爹妈。威胁要揍他、抓他、告发他,都没用,张鸣不干,就是不干。看守们不高兴了,没见过这样的孩子。倒也没揍他,但把他的表现告到了学校。学校正好有一个出身好的老师当家作主是革委会主任,本来就出于革命义愤,看不起张鸣。这一来正好,理所当然就将他开除了。张鸣倒也无所谓,就天天在家里待着,给哥哥做饭,送哥哥上学去挨打。
过不多久,开除他的革委会主任也被发现是“中右”,靠边站了,学校换了管理人,张鸣又回学校了。其实回不回也没什么区别,上课都在瞎闹,能记住的就是劳动,少数爱看书的自己交换书看。闹哄哄、懵懵懂懂地长大,直到一架飞机坠毁。
那时候的学制,是从小学到高中九年制,张鸣八年级的时候发生了林彪事件。对他个人来说,这是一次奇迹般觉醒的契机,国家形势有所缓和,学校突然开始抓教育了。张鸣平生第一次参加了考试,感觉很新鲜,也很开心。成绩好的人是向往考试的,可惜这也是张鸣求学阶段唯一的一次考试。国家很快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而且在这一松一紧的过程中,有些重要的变化发生了。
气氛宽松的时候,张鸣跟着说了些话,这些言论到了气氛紧张时,就成了大问题。1974年,黑龙江农垦建设兵团四师对张鸣的错误言论进行全师通报,这个17岁的少年被整得很惨,不堪回首的批判和批斗,家里也受到了牵连。张鸣为此自杀过,还不止一次。他尝试了很多种自杀办法,居然都没死成。他也就烦了,豁出去了,“老也死不了,那就不死了”,之后他再也不想死了,他还非要活得滋味起来不可。
学农机时对历史来了兴趣
知青大规模返城之后,兵团出现了空缺,一个兽医的位置被张鸣填上了。不久,中国迎来了1977年高考。张鸣自然去参加了,但他的政治问题还没解决,不让录取。第二年他再考,分数高出录取线老多,但是在“限制录取”之列。他延续着养猪和兽医的人生轨迹,识趣地报考了两个学校,其中一个“东北农学院”的招生简章上有畜牧兽医专业,实际上却不招,可见当时招生有多乱。就这样,张鸣别无选择地进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却调剂到了农机专业。
那所现在已经迁移到大庆的农垦大学,坐落在山窝里,三面环山,校门外是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路。用张鸣女儿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独立村,不过以大学的形式存在。从这以后,张鸣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大学村”里,读书、教书、成长、成熟、结婚、生子,断断续续生活了十多年。
大学的专业是农业机械。张鸣倒不太失望。他当时的志向是当作家,对于文学青年来说,所有的一切都是经历、是写作素材,干什么都可以的。
大学四年,张鸣成了乖孩子、好学生。张鸣的课上得很辛苦,每天从早到晚8节课,一堂都不拉下,晚上写作业、上图书馆,从不惹是生非,成绩一直在年级排名靠前,最后的平均分是89。
其实他对自己的专业不喜欢也不投入,也会消极对付。他还记得制图课的作业就是抄的,但总的来说没得选择,也没有多少闲暇思考“人生方向”,天天都忙着上课。动乱刚过,学校里大家都有一种向上的劲头,紧张追回时间,这感觉不错。
就是从那时候起,张鸣开始对历史感兴趣。他每天到图书馆去读《资治通鉴》,一直看到闭馆。后来连图书管理员都被感动了,破例允许他借回宿舍去看。他大学期间读完了全套20大本的《资治通鉴》。当时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有朝一日历史将成为他终身从事的专业,而且还会“遗传”给他的宝贝女儿。
1982年张鸣毕业,有两个选择,是回农场当技术员,还是留校教党史,这是一个问题。张鸣很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刚参加工作,他就被派到中国人民大学旁听一年,这是他与人大结缘的开始。其实旁听经历是让人失望的,张鸣不觉得那儿的党史教育吸引他,不久便流窜到各校胡乱旁听去了。但这经历开阔了他的眼界,他从北京回去后就想考研了。
上学与上班的交替
张鸣总结自己,“上学的时候都乖,上班的时候都叛逆”。之所以走到哪里都是刺毛头,都叛逆,是因为他酷爱自由,也非常在乎尊严。他最不能容忍的事,是被侵犯尊严,被强迫干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以及不人道行为。偏偏他追求的价值——自由和尊严——恰恰是时代最稀缺的,所以大家都觉得他另类。放眼当今世界,有钱人不尊重穷人,上级不尊重下级,只要能支配你,就能随便凌辱你,家长对孩子的爱,也是侵犯和凌辱式的。张鸣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了,说,中国的问题不仅在于专制制度,而且是专制文化深入骨髓,连自称“自由主义者”都压制别人,一旦大权在握,也不定干出什么事来。从一个人对异端和荒谬的态度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本质。
张鸣其实也能妥协,也能与人合作,但一旦碰到他的底线,就一定会反抗,会爆发。这时候就不在乎面子了,学术会上他会直言不讳给人难看,但那是针对学术、不是针对个人。别人也可以这么对他,他并不以为冒犯。难怪有人说,张鸣的性格像美国人,虽然他没有一点海外背景。
在工作岗位上,张鸣与同事的相处时有摩擦。他是大学生,同事都是工农兵学员,彼此看不起,价值观也不同。1985年,张鸣考取了人大党史专业的研究生。不是他喜欢的专业,但是当时他在做党史教员,别无选择。
对他来说,考研是件颇富挑战的事情,原因说起来很奇怪:他从来没有上过文科的课,比如从小学到大学,没上过一节历史课。所以考试的题目他都会,却不知道该怎么答。蒙了好些,好歹算蒙上了。
从表面上看,从北大荒到北京来读研究生,并没有真正改变张鸣的命运,对大学失望的感觉不减反增,他感到失落和迷茫,有一段时间整天看武侠小说、下围棋,无所事事。后来自己都觉得这样不行了,改邪归正又天天去泡图书馆,像牛一样地看书,精神面貌马上就不一样了。
这时候,张鸣放弃了作家梦,正经想当学者了。但当时整个国家的文化环境并不能让张鸣振奋和激动。1988年所谓的“文化热”中,人人都在侃老庄、易经,不懂装懂,说得玄乎其玄,张鸣觉得这样特没劲,毕业后又回了八一农垦大学。这个地方闭塞,但安静,张鸣带了好些传统文化的书,他准备好好读一下。
回到单位,他再一次发现自己与单位的磕磕碰碰很多,作为学校唯一的研究生,别人都不敢惹他,而他的叛逆劲头儿也暴露无遗而且蒸蒸日上。他所在的社科系开会时,领导在上面发言如果太官样,他会直接叫头儿闭嘴,别废话了。
更重要的是他找不到有共同语言的人,深刻感觉到了没有交流的痛苦。他的目光再次瞄准了外头的世界,准备考博士。但是单位不准考,这事便搁浅了。张鸣一日日熬着,直到1994年单位领导换届,趁着工作交接的混乱之际,张鸣的报名被批准了,这时候的张鸣,已经年近40,考试的冲劲远非昔日可比,为了保险,他还是报考的人大。
人生终于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读博期间张鸣算是正式进了学界,他开始给《读书》写文章。第一次发表似乎是讨巧,他写的是驳斥别人的文章,很快就发表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有那么七八年的时间,他每年都在《读书》上发两三篇文章,考虑到那个年头《读书》杂志在思想、学术和文化界的地位,张鸣的成绩是惊人的。
博士毕业后便留校工作了,开始在党史系,2002年并入国际关系学院,成了政治学系。有那么几年,他很安分,自己写文章发表,上教授也很顺利。他照例还是很牛气,述职那天,背着一编织袋的文章进去,往桌上一倒,杂志期刊哗啦啦流得满桌子都是,他很耍酷地一句话没说,倒完就出去了。成果多,没的说,他就上了。当然,据说也是他运气好,捡了个便宜。因为两派人都要晋升自己的人,互相掐上了,反倒让张渔翁得利了。后来,他当了政治学系的主任。
在市场里获得认可
系主任到底还是跟院长干上了,后来因为萧延中没评上教授,张鸣为之鸣不平,矛头直指院长。这就是传说中的人大教授“离职风波”。
我问,你想过后果吗?他说,是,大不了被开除,当自由撰稿人,生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而且,他算着被开除的可能性其实很小。
不过,张鸣说,领导不支持,他另有“后台”和靠山,那就是市场。市场不等于粉丝,粉丝是无条件挺偶像的。张鸣自称没有粉丝,但是会有支持者,如果哪天他说的不对了,他们就不支持他了。张鸣的底气在于,他有思想,他说的是对的,而且他比别人说得好。这样就有了市场,让他说了话会有收益,所以有底气。张鸣说:可靠的是市场。如果没有市场了,他就死路一条了。
但张鸣关注的,并不仅仅是在市场里生存的问题,还有更高的意义。在一个纷繁的时代里,当然会充斥很多声音,但至少,张鸣是其中之一,他没有缺席,没有沉默。这些年来,他用自己的博客和微博,一直不停地“鸣”,批评教育行政化、批评本科教学评估。他说,有发言权的知识分子,要敢于批评,要启发民智,有没有用先不管,这是责任,必须要做的事情。
对于历史,张鸣强调“文笔要好”。因为历史不同于别的纯学术,普通人也会有兴趣的,历史也是要人看的。他看民国时的人文章写得多好看,可他的前辈写的论文何其枯燥乏味。张鸣痛恨那些学术八股。著作一开头,为什么非要有个“研究综述”,爬梳以往的研究?作为学术训练是需要的,但不该因此就成为定式。
张鸣自称做历史从学术上是很传统的。他必然先看材料,看得足够多了,再写,从不观点在先,为观点找材料。他只是不接受学术八股的形式,也不能容忍学术缺思想,没生命关怀。他坚持学术和生活要有交融,不能做死了。这些果然都是很传统的观点。
在学问方面,张鸣有他的骄傲。他看好自己的《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和《北洋裂变:军阀和五四》。“100年不敢说,但再过50年,肯定还有人看我的书。”张鸣说这话时,眼睛一点儿不眨,语气也平淡,像在讲一个常识。他说自己的学问肯定不如民国的学者,但他对人的透视不输于他们,自己那些大起大落的经历是他们没有的。他以前总觉得自己倒霉,现在发现还是幸运的,毕竟出来了,赶上了时代的市场。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的勤奋。现在学界的很多人不用心做学问了,做出一点成绩后就坐享其成了。张鸣不,他一直很勤奋。
说到“勤奋”,张鸣抬起上臂,向我展示他的两个胳膊肘,灰黑一片,居然都有茧。张鸣说,他脊椎有问题,坐着看书不能持久,只能趴着看书。中午的阳光照在棋盘上,也照在张鸣那张不驯化的脸上。他说,现在的世界多没劲呀,大家都那么功利,那么物质,好玩的人越来越少了。他这么叹息时,围棋很寂寞地散落着。我想,这个“鸣”个不停的、找不到棋友的、有盔甲般胳膊肘的人,是可爱的。
(本文编辑 宋文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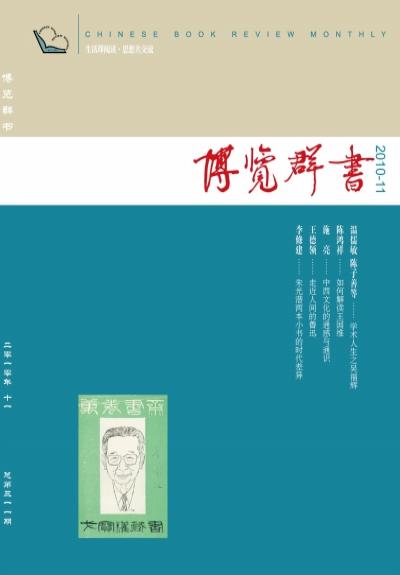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