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花落:历史边缘的知识女性》,桑农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26.00元
除了要承受战乱、饥饿、繁重的家务、感情的折磨,萧红还要承受妇科病、怀孕的负担、产后的虚弱。这一点,被人们忽略了。在大家眼中,萧红只是一位女作家,很少有人想到她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性。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里,萧红的悲剧是宿命的。面对根深蒂固的男性霸权,她只能是一个“软弱者”、一个“失败者”。
事实上,萧红打破文学陈规的创作,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批评。这使得萧红常常深陷在不被认同的苦恼中。她的文学理念超越了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因而也就不能被同时代人所理解。
最近读到一本书《我的婶婶萧红》(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作者曹革成是端木蕻良的侄子。其间许多文字,显然是在为他叔叔申辩。此前还有一部《端木与萧红》,也有此动机。而该书的作者钟耀群,是端木蕻良的第二任妻子。作为端木的亲人,出来澄清一些事实,是在情理之中,可一厢情愿地要证明两人的婚姻多么美满,未免矫枉过正。
人们对端木蕻良印象不佳,是有事实依据的。端木的某些行为,的确让人看不过去。例如新婚不久,他先行赶往重庆,将身怀有孕的萧红一个人留在战火纷飞的武汉。还有在萧红生命垂危之际,将她托付给骆宾基,自己却很少去医院看望。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具体的情况,但不管怎么说,他无疑是未尽到丈夫的责任。
关于他们婚后的生活,还有许多对端木蕻良不利的描述。绿川英子在《忆萧红》一文中写道:“我想到微雨蒙蒙的武昌码头上夹在濡湿的蚂蚁一般钻动着的逃难的人群中,大腹便便,两手撑着雨伞和笨重行李,步履为难的萧红。在她旁边的是轻装的端木蕻良,一只手捏着司的克,并不帮助她。她只得时不时地用嫌恶与轻蔑的眼光瞧了瞧自己那没有满月份的儿子寄宿其中的隆起的肚皮——她的悲剧的后半生中最悲剧的这一页,常常伴随着只有同性才能感到的同情与愤怒,浮上我的眼帘。”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对萧红与萧军共同生活的回忆中。据说,当时有人看见萧军和萧红一起在街上走的时候,萧军大踏步地走在前面,萧红在后面跟着,很少看见他们并排走。当我们为萧红和端木蕻良的结合而惋惜时,是否想到,她和萧军在一起的日子就是幸福的吗?
不错,是萧军将萧红从危难中拯救出来,是他们一起从东北逃亡到上海,一同见到鲁迅,加入了左翼文学阵营。可在日常生活中,萧军给萧红带来的是什么呢?虐待、蔑视、背叛,该犯的错误都犯了。萧红去世后,他居然还说:“作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作为一个有才华、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也许可以这样说:在文学事业上,她是个胜利者!在个人生活意志上,她是个软弱者、失败者、悲剧者!”殴打了妻子,却不许她在外人面前掩饰;让第三者珠胎暗结,还不许妻子难过、抱怨。否则,就是“个人生活意志上”的“软弱者、失败者、悲剧者”,这便是萧军“男子汉”的逻辑。
萧军和端木蕻良分属截然不同的类型,一个是所谓硬汉,一个是生性娇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悠久传统的大男子主义。男性的自我中心,使他们无视萧红作为女性的身心需求。像绿川英子所说的“只有同性才能感到的同情与愤怒”,他们是无从察觉的,更不要说做到许广平那样感同身受的体贴。
许广平在《追忆萧红》中写道:“她(萧红)同时还有一种宿疾,据说每个月经常有一次肚子痛,痛起来好几天不能起床,好像生大病一样,每次服‘中将汤’也不见好。……(我说)白凤丸对妇科不无效力,何妨试试?过了一些时候,她告诉我的确不错,肚子每个月都不痛了,后来应该痛的时候比平常不痛的日子还觉得身体康强,她快活到不得了。等到‘八一三’之后她撤退到内地,曾经收到她的来信,似埋怨似称谢的,说是依我的话服过药丸之后不但身体好起来,而且有孕了。战争时期生小孩是一种不容易的负担,是不是我害了她呢。后来果然听朋友说她生过一个孩子,不久又死去了。不晓得生孩子之后身体是否仍然康强,如果坏起来的话,那么,真是我害了她了。”
几乎所有的萧红传记,都没有认真对待以上这段叙述。现在看来,这里所体现的身体关怀,才是对一位女性真正的关爱。除了要承受战乱、饥饿、烦重的家务、感情的折磨,萧红还要承受妇科病、怀孕的负担、产后的虚弱。这一点,被人们忽略了。在大家眼中,萧红只是一位女作家,很少有人想到她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性。不是得了肺炎、得了癌症,才叫有病在身。身体的不适引起精神的忧郁,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多愁善感、小资情调。萧红一生遇到的男性,无论是萧军、端木蕻良,还是早年的汪恩甲、临终前相伴的骆宾基,都从未想到这一层。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里,萧红的悲剧是宿命的。面对根深蒂固的男性霸权,她只能是一个“软弱者”、一个“失败者”。弥留之际,萧红终于有所醒悟,感叹道:“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据骆宾基《萧红小传》记载,萧红临终前在一张纸片上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有人说,这体现了她“不平和反抗”的性格。但她有什么“不平”,又在“反抗”什么呢?早年,家庭乃至家族的压迫,汪恩甲家人的干预,都引起她过激的反抗。这自然可以说成是反抗旧的封建势力。与萧军一起逃离东北,经鲁迅推荐蜚声文坛,她也一度倍受青睐。虽然身在左翼阵营,由于没有参加党派斗争,尚未见有来自外部或内部的迫害发生。让她愤愤不平的,一在感情生活方面,一在文学创作方面。关于前一项,已经说得很多了;关于后一项,注意到的人却很少。事实上,萧红打破文学陈规的创作,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批评。这使得萧红常常深陷在不被认同的苦恼中。
鲁迅去世后,萧红与胡风等人过从甚密,也可以说属于一个文学圈子。胡风要办一份刊物,取名《抗战文艺》,萧红不喜欢,建议改成了《七月》,这才有后来文学史上“七月派”的称谓。然而,萧红与胡风的思想分歧很大。《七月》上刊登的一些座谈会发言记录,就有这方面的内容。
1938年1月的座谈会上,有人提出,留在后方写不出反映抗战生活的作品。萧红反驳说:“我看,我们并没有和生活隔离。比如躲警报,这也是战时的生活,不过我们抓不到罢了,即使我们上前线去……如果抓不住,也就写不出来。”胡风插话道:“恐怕你根本没有想到抓,所以只好飘来飘去。”萧红接着说:“譬如我们房东的姨娘,听见警报响就骇得打抖,担心她的儿子,这不就是战时生活的现象吗?”
同年4月的座谈会上,萧红尖锐地指出:“胡风对于他自己没有到战场上的解释,是不是矛盾的?你的《七月》编得很好,而且养育了曹白和东平这样的作家,并且还希望再接着更多地养育下去。你也丢下《七月》上战场,这样是不是说战场高于一切?还是在应付抗战以来所听惯了的普遍口号,不得不说也要上战场呢?”
萧红与胡风争论,实际上也是对当时主流话语的抵制。除了胡风,还有许多重要的左翼作家对萧红的文学创作不满。前面提到的,茅盾所写的《〈呼兰河传〉序》里,批评的篇幅就远远超过了赞扬的部分。序文中质疑道:“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1938年4月座谈会上萧红的发言,正好有一节与之相应:“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看来,对别人可能有所指责的地方,她不是不晓得,而在她心目中那正是自己追求的。她的文学理念超越了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因而也就不能被同时代人所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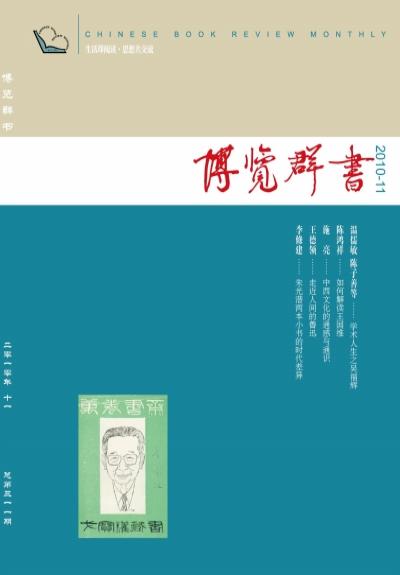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