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真实到残酷的历史事实,他不隐瞒,不虚饰,不为己讳,不为贤者讳。他不避讳运动初期自己曾写过“派性大字报”,也曾“声嘶力竭”地在斗争会上批斗过他人;他写了高尔泰先生经受的苦难和灵魂的重创,也揭露了他对好友的告密与背叛;他衷心赞美了常书鸿先生对敦煌事业毕生的热爱与贡献,也写出他的某种“策略失误”和晚年的无奈。对于写史的人来说,这种“有一说一”的态度是可取的。这样写出的历史才是信史,对后人才有参考价值。
透过表面的“冷”看到内在的“暖”,从充满大恶的历史场景中剥离出源于民族优秀传统的道德精神,这正是《一叶一菩提》胜人一筹之处,也是作者对现实社会世道人心的一种贡献。
萧默先生的《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我是一口气看完的。掩卷思之,深感这是当前难得读到的好书。好就好在,它不仅非常真实地记录了“文革”的历史,而且对那个极端特殊年代的人性,进行了展露与揭示,从而促使人们深刻地反思——从国民性的角度反思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过去与现在,以便更好地关照未来。
这本书之吸引人,从书名就可看出端倪。一是地点——大漠孤烟中充满东方艺术神秘色彩的敦煌;二是时间——15年中,整整10年是在“文革”期间,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不容错过、无法漏掉的一页。它的荒诞与大谬,对文明的破坏,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灾难,都是无以复加的。真实记录这段历史,深入研究、反思这段历史以警示后人,是亲历者和当代的研究者无法绕过的一种责任。遗憾的是,以前这方面的出版物少而又少,以致40岁以下的许多中青年人并不知“文革”为何物,甚至无端将之想象为一个充满浪漫激情的“阳光灿烂”的年代。这真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它的害处不仅在于对一段历史的误读和误解,也许还会产生更加深刻和可怕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佩服萧默先生写出真实的勇气。作为一个建筑专家和建筑艺术研究者,萧默先生在专业著述之余写出这样一本独具特色、耐人寻味的个人断代史,是有着强大的社会责任感作为动力的。
如今50岁以上的中国人,不管从哪个角度,“文革”都是一个巨大而重要的存在,是绕不过去的生命体验。对于萧默这样的知识分子,尤其如此。1963年,由梁思成先生促成,他到敦煌莫高窟从事建筑历史研究。谁料,不待这项令他心仪的事业真正展开,就遭遇了“文革”。他和“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美学家高尔泰,和莫高窟的干部、知识分子和职工,和敦煌的工宣队、农宣队、工作组和群众一起,经历了漫长的动乱年代。用萧默自己的话说:“从25岁到40岁,是人生最宝贵的一段。我当初豪情满怀,活力四射,信心百倍,想要做出一番事业,但遇到的却是我们国家最黑暗的一个时代,虽然相对来说,我个人只不过是有惊无险,却也是身心疲惫,遍体鳞伤,痛定思痛了。我虽然后来离开了敦煌,但在敦煌的经历,对我来说却已经成了生命不可分割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1978年他有机会搭上考研的末班车,回到母校清华大学深造,后来又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敦煌建筑艺术研究。可以说特殊年代在莫高窟清苦寂寞的生活,成就了这位建筑理论家、艺术家后来的事业。但离开敦煌的30年,他一时也没有停止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反思。他说:“这三十年,可以说,就是在漫长的思念和企图更多地理解这段历史中度过的。”他坦承“至今也不能说已经有了足够的理解”,“但可以有把握地说,比起绝大多数年轻朋友来说,我的理解还是很具有参考价值的”。他愿意“趁着思考力还没有完全丧失,记忆也还清晰的时候,面对着当前某种企图倒退回那个灾难时代的思潮,为了对子孙后代负责,我觉得把当年的历史真相写出来,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看到,萧默先生是以极为客观、坦诚的态度叙写这段历史的。他写的是15年中自己亲身的经历,和自己耳闻目睹的身边的人和事。对真实到残酷的历史事实,他不隐瞒,不虚饰,不为己讳,不为贤者讳。他写自己和其他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遭受的打击、迫害,也不避讳运动初期自己曾写过“派性大字报”,也曾“声嘶力竭”地在斗争会上批斗过他人;他写了高尔泰先生经受的苦难和灵魂的重创,也揭露了他对好友的告密与背叛;他衷心赞美了常书鸿先生对敦煌事业毕生的热爱与贡献,也写出他的某种“策略失误”和晚年的无奈。笔者认为,对于写史的人来说,这种“有一说一”的态度是可取的。这样写出的历史才是信史,对后人才有参考价值。对比有些写作者,把历史看作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按照个人和“形势”的需要随意涂抹和更改历史,是必然会失去读者信任的。
萧默先生写出了“文革”中,社会各色人等受命运无情驱使的众生相,和一幕幕“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悲喜剧。然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写“文革”,并不仅仅是揭露、控诉与批判,而是立意于一个更高的层面——写出了阴霾密布岁月中的暖色,颂扬了“人性和社会的正面”,使人看到我们民族精神与文化传统中积极的因素,给人以信心与希望。萧默先生说他的书“不是‘伤痕文学’,因为并不重在揭示伤害,而更重于坦现复杂的人性和展现广阔的社会”,“更着重的还是颂扬在那个被扭曲了的社会中人性的正面”。
诚然,“文革”是一个把“斗争哲学”推向极致的年月,是一个毁灭传统、压抑人性的年月,是一个充分调动人性恶的年月。多少好人和比较好的人,在政治斗争的高压下不得不做出一些违心的事,以致在后来的岁月中追悔莫及(曾引起轩然大波的冯亦代先生的《悔余日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在《一叶一菩提》中,写出了即使在那样恶劣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也有相互的理解、信任与感人至深的救助。萧默念念不忘那些正直、善良的“敦煌人”。在他笔下,凡是敦煌人,工宣队、农宣队、本土的干部和群众,几乎都是好人,不整人的人;即使当地的红卫兵,也比外来的红卫兵老实得多。可能正因为此,敦煌才不是重灾区。他写到县干部老刘、工宣队长老郑和革委会主任“老孙头”、“老钟头”,还有县四清展览工作组赖团长、党河水库指挥部白主任等人,顶着压力对他这个“臭老九”加以保护,使他在险恶的斗争中数次化险为夷,不致遭受灭顶之灾。他写常书鸿这位可敬的老人,虽然自己身处逆境,还关心着萧默等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家庭,还忘不了去解救曾经与自己有过恩怨的段先生。当然,萧默本人在当时的一件聪明善举给读者印象尤深:他奉命“押解”受重伤的常老去酒泉治病,运用当时人们十分娴熟的“极左”语言,成功地让医生改写了诊断单,使老先生能够转去兰州获得有效的治疗。正如辛子陵先生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所说,许多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在那样复杂危险的境地中,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利用各种机会,保护和援助”受迫害者,从而“才很大减轻了这次政治大地震的烈度、灾难、损失和伤亡”。也如萧默本人所说:“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没有被外来的并曾经独霸几十年的‘斗争哲学’彻底征服,而仍然葆有‘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基本道德种子,就得益于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传承。”“任何社会都需要一种代表主流的正面的时代精神,才能拥有充沛的发展动力,而这种时代精神,又必须建立在历史的传承之上,是历史的一种积淀。所以,尽管我写的是一个灾难的年代,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积淀了数千年之久的、优秀的、代表正义、善良人性的传统精神并未被掩没,反之,对于今天,是更加显得可贵了。”
透过表面的“冷”看到内在的“暖”,从充满大恶的历史场景中剥离出源于民族优秀传统的道德精神,这正是《一叶一菩提》胜人一筹之处,也是作者对现实社会世道人心的一种贡献。“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之语原本出自佛学,大意是指无论善恶是非,均隐藏于万事万物之中,一个人只有做到大义或真理,才能真正具有佛心慧质。无独有偶,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也写过这样一首诗:“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这里无疑是富有禅意和哲理的。而萧默先生用此语做书名,大概更立意于发掘那些存在于大千世界、万事万物、芸芸众生中的大善,只有这些点点滴滴的善聚积与弘扬起来,才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与困厄中复兴的希望。具体到“文革”历史,诚如作者所言:“若人们仍仅停留于倾诉、揭露或是追究某些大小人物的个人责任,那还不是真正的反思。……只有提升到对制度性层面和民族整体素质的思考与忏悔,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才有望实现真正的复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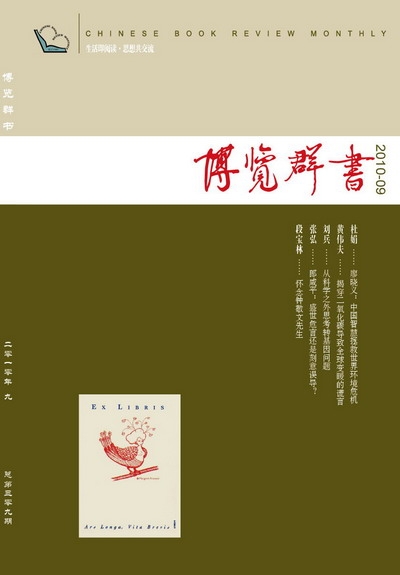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