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爱情诗,如从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说起,已两千多年。进入现代,“五四”以后的诗人中,知名的爱情诗人不得不提鲁迅与周作人都认可的汪静之。
提到汪静之,不能不提湖畔诗社。它既是由几位志趣相投的年轻人组成的民间团体,也是上世纪20年代中国白话诗歌的一个重要流派,因此,中国诗坛上有“湖畔派”之称。湖畔诗社第一个诗集《湖畔》,由在上海银行任事的应修人筹钱,自费印刷出版,印数1000册。这本小又巧的诗集,在沪杭等地一上市,很快就被抢购一空。我有幸藏有这一册诗集。此书开本极精致,朴素而淡雅,封面的上半部是春意盎然的湖畔,在极为简洁的画面右下角,印有黑体“湖畔”两字;而在左下角标出“1922年油菜花黄时”,7号楷体。
瞧着这诗集封面上的远山近湖,读着“油菜花黄”四个绿色的字,我不由得在脑中泛起几个历史镜头:1920年,初夏的西子湖畔,浓荫低垂,小荷才露尖尖角。18岁从安徽绩溪走出的汪静之,正漫步在苏堤上。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人间天堂的杭州。湖光山色,绿柳红舫的迷人风景,让他陶醉不已。这个身材瘦削、斯文白净的年轻人,刚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带着无限的憧憬,来到这朝思暮想之地。晚年的汪静之,历经“文革”后,几乎像“梅妻鹤子”的林逋一般,隐逸在杭州。当时我有机会问他第一次到杭州的观感,他兴奋激动地说:“那时到杭州,只是想能考一所学校读书求学,但未料到年青时内心洋溢的诗情,不期然正遇上了中国新诗的黄金时期,尔后,却成就了我一片繁花硕果的人生风景,这是当时想不到的事!”
当年,湖畔诗社的主要成员绝大多数来自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这些年轻的学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敢于冲破僵化的思想道德束缚,借助新诗礼赞美好的青春,歌颂人类纯真自然的感情,也表达了自身对人生的种种期许,对爱情的憧憬和追求。“湖畔派”的诗风,清新、淳朴、真实、单纯,在当时的诗坛独树一帜,引起了不少名家前辈的关注。朱自清十分赞赏湖畔诗社,曾说:“中国缺少情诗……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可以说生活在诗里。”鲁迅、胡适、周作人曾为湖畔诗社担任导师;叶圣陶、朱自清、刘延陵也曾担任顾问。鉴此,可一窥当年湖畔诗社于文坛的重要地位。
汪静之就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不久,便有诗作发表在《新潮》杂志上。他许多科目都挂“红灯”,唯独国文成绩出类拔萃,在学校里成了名人,同学们纷纷以“诗人”相称。1920年,汪静之写出第一本处女作《蕙的风》。有人评说:“《蕙的风》便是其中一场并不成功的恋爱结晶:汪静之与湘女傅慧贞(杭女师三号美女)已经山盟海誓,因女家棒打鸳鸯而分手,《蕙的风》是写给傅的情诗,蕙慧谐音。”尔后,汪静之结识了同在第一师范学校求学的潘漠华和冯雪峰。潘与汪同岁,冯小他一岁;之后,又认识了在上海的年长一岁的应修人。就这样,四个风华正茂的少年,满怀着对生活、对诗歌的无限热忱,走到了一起。
1922年3月底,应修人特地从上海来杭,与冯雪峰、潘漠华和汪静之相聚于西子湖畔。他们谈新诗,说人间之爱,带着激情与诗兴,游玩了一星期;这期间,应修人发起,从四人的诗作中,遴选若干,结集出版。汪的诗,是从他已付印的《蕙的风》里取出的。四个年轻人在诗集的扉页上题词:“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这样发自诗人内心的话,真有点如钱钟书所说,“诗人们就像古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尤其像那种参加动作的合唱队,随着搬演的情节的发展,在歌唱他们的感想。”(见《宋诗选注》序)他们“不仅敢爱而且敢写,不仅敢写而且还敢拿出来发表,敢于让全世界都知道,甚至唯恐别人不知”。(见裴毅然《汪静之五四情诗》)
那时的汪静之,就像在湖畔放飞爱的小鸟。我们不妨来听听他当年放飞之歌:“风吹皱的水/没来由地波呀,波呀”,“花呀,花呀,别怕罢/‘我慰着暴风猛雨里哭了的花’/花呀,花呀,别怕罢!”,“你该觉得罢/仅仅是我自由的梦魂儿/夜夜萦绕着你么?”这些诗句,犹如古代的小令,充溢着芳香、清纯!而前一年创作的《蕙的风》,是一个少年诗人饱含深情,为爱情所歌:“是哪里吹来/这蕙花的风……/温馨的蕙花的风?/蕙花深锁在园里/伊满怀着幽怨/伊的幽香潜出园外/去招伊所爱的蝶儿……”
在今天的人看来,这诗中含蕴的爱,似没什么刺激;可在当时,影响甚广,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封建顽固派的反对声中,鲁迅站出来说话:“静之的情诗……可以相信没有不道德的嫌疑。”朱自清也评说:“这是向旧社会道德投下了一颗猛烈无比的炸弹!”
我们再读另一首诗:伊的眼是温暖的太阳,/不然,何以伊一望着我,/我受了冻的心就热了呢?/伊的眼是解结的剪刀;/不然,何以伊一瞧着我,/我被镣铐的灵魂就自由了呢?/伊的眼是快乐的钥匙,/不然,何以伊一瞅着我,/我就住在乐园里了呢?/伊的眼变成忧愁的引火线;/不然,何以伊一盯着我,/我就沉溺在愁海里了呢?(见《伊的眼》)这是抒写爱情之力。当然,爱情之眼,是解结的剪刀、快乐的钥匙,但也是忧愁的引火线。
《湖畔》诗集出版后,周作人1922年5月8日就有短文评道:“《湖畔》是汪静之君等四人自费出版的诗集。这四个人的诗在本附刊上,也曾经发表过好些,看过的人大约自然知道,不用我来批评好歹,我在这里只说一句话,他们的诗是青年人的诗,许多事物映在他们的眼里,往往结成新鲜的印象。我们过了三十岁的人所承受不到的新的感觉,在诗里流露出来,这是我所时常注目的一点。”鲁迅也即评说,这些情诗是“血的蒸气,是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作为“湖畔诗社”的四位诗人的诗,有其共性,又各有各的特色。应修人在编讫《湖畔》诗集后,于1922年4月1日以《心爱的》为题写道:“柳丝娇舞时我想读静之的诗了;晴风乱飐时我想读雪峰的诗了;花片纷飞时我想读漠华的诗了。漠华的使我苦笑;雪峰的使我心笑;静之的使我微笑。我不忍不读静之底诗;我不能不读雪峰底诗;我不敢不读漠华底诗。”他还在诗的首尾说:“逛心爱的湖山,定要带着心爱的诗集的。”“有心爱的诗集,终要读在心爱的湖山的。”如今的读者,也许很难想象,这位诗人是上海一家小银行的职员,后来从多情善感的诗人而投身于革命,尔后,为了保护革命者,从楼上跳下,壮烈牺牲。另一位诗人冯雪峰,是鲁迅的朋友,反右、“文革”中,多受冲击,后写出不少杂文。而潘漠华于1933年12月在天津市委宣传部长任上,领导北方左联工作,不幸被潜入内部的特务逮捕,关押在国民党市党部特务队。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却一无所得,就把他押送到天津法院看守所,随后转押河北省第一监狱。1934年底,他被折磨致死于狱中。今天,很难想象当年那些为诗而歌、为诗而哭的人的心灵世界究是什么?也许在今日,重读他们的诗,了解他们的经历,定会有年轻人说:“真有这样的人吗?”
朱自清于《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重申了他的评论。他说:潘漠华的诗“最凄苦,不胜掩抑之致”,冯雪峰的诗“明快多了,笑中可也有泪”,汪静之的诗“一味天真的稚气”,应修人的诗“却嫌味儿淡些”。在为《蕙的风》所写的序言中,朱自清从一个天真烂漫的20岁的少年“少经人间底波折”为出发点,认为汪静之的诗“多是赞颂自然,咏歌恋爱”;认为其所赞颂的“又只是清新,美丽的自然,而非神秘,伟大的自然”,其所咏歌的“又只是质直,单纯的恋爱,而非缠绵,委屈的恋爱”;认为“这才是孩子洁白的心声,坦率的少年的气度!”可谓一语中的。如从四个诗人之后的人生命运来看,朱自清的话几乎成了谶语。除汪静之为爱情吟唱一生外,潘漠华一生最为凄苦;冯雪峰后来的命运确是“笑中有泪”;应修人一瞬间的壮烈之死,如从人生旅途视之,却嫌“味儿淡些”。
作为终身诗人的汪静之,1926年出版了他的第二个诗集《寂寞的国》,同时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翠英及其夫的故事》、一部中篇小说《耶稣的吩咐》,以及一个短篇小说集《父与女》。四诗人中,汪静之是湖畔时期唯一独立出了诗集的,《湖畔》只是象征性地收入了他的6首小诗,后出版的《春的歌集》中,完全没有他的作品。汪静之的作品都收在他的个人诗集《蕙的风》里。《蕙的风》是一部纯粹的自由、大胆、浪漫的爱情诗集。
抗战期间,汪静之先赴粤任中央军校四分校国文教官,后随校迁往广西宜山,再迁贵州独山。1942年,因拒绝重庆川大教授约聘,经济困难,他做酿酒生意。1945年,与人合伙开小饭馆,亲自跑堂。抗战胜利后,他先后执教于徐州江苏学院、复旦大学中文系。解放后,应冯雪峰之邀,由复旦大学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1956年转入中国作家协会为专业作家。“文革”前夕,他敏锐地感觉到时局不太好,便悄悄地回到了西子湖畔。从此,一个市民杂居的居民区里,隐居了个白发苍苍的老诗人。没人认得他是谁,也没人想追究他是谁,汪静之奇迹般地成为未受任何冲击的“五四”老人。“幸亏自己远离政治,半做隐士,才苟活性命于乱世”,晚年的汪静之这样回首。1982年4月4日,湖畔诗社建社60周年,新的湖畔诗社在杭州成立,汪静之任社长。在成立大会上,汪静之宣告:“我们从此要歌笑在湖畔。”于此,这位古稀诗人重又弹起竖琴,弦歌了14个年头。
1996年10月10日,95岁高龄的汪静之停止了步履,放下琴弦,轻轻地躺下,再也不能歌吟于湖畔了,宛如一泓宁静的西湖之水。在汪老遗体告别的那天,我随一位诗人奔向杭州,谁知堵车晚了半个小时,未能送汪老一程。我只能呆呆地凝视他的儿子、著名翻译家飞白,捧着诗人的遗像,在那里徘徊。
中国失去了一位终身诗人,也许,我们如今只听到“终身教授”、“终身院士”,从不会想到一位诗人在人世间的重要(在这方面,我们应想想孔子、亚里士多德,他们对诗是多么看重)。从杭州回来的那晚,我彻夜未眠,总想起汪静之晚年对我说的:“真诚是诗人的高贵气质!”这句话成了我心中的“不灭之物”!尽管诗人离开了这喧嚣的世界,尽管我们面临的是浮躁与物化的时代;但是,我相信诗人的语言,现在还活着,并将一直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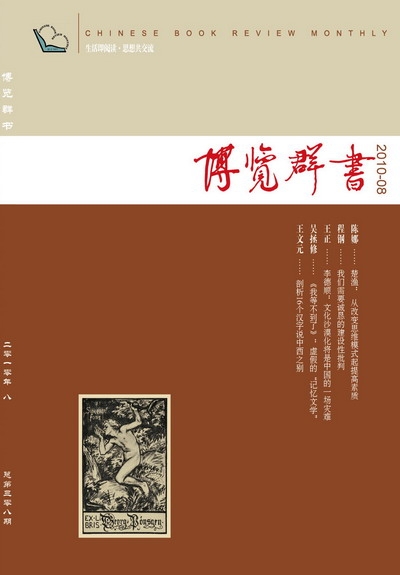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