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南朝时萧统《文选》开选“赋”(或称“选赋”)之风,历代赋选继出不穷,至明清两代尤盛,然皆属古典选赋范畴;迨至上世纪瞿蜕园编《汉魏六朝赋选》,始以新批评观选赋,开启现代“赋选”之路径。数十年间,继起而编赋选者不下数十种,其中篇幅最为宏大的是毕万忱等先生历时8年(1990-1998)编纂出版的四卷本《中国历代赋选》,书中选古代赋家126人,赋作197篇,计180万字。迈进21世纪,赋学研究又有了长足的进展,选赋工作也未停止,在众多成果中,新近出版的赵逵夫先生主编的《历代赋评注》(巴蜀书社,以下简称“赵编”),以七卷本(分别为《先秦卷》、《汉代卷》、《魏晋卷》、《南北朝卷》、《唐五代卷》、《宋元金卷》、《明清卷》)之宏制,选历代赋家329(佚名者除外)人,赋作583篇,420万字,成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内容最为丰赡的一部赋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自1992年开始编纂,至2010年出版,历时18年,跨越两个世纪,堪称令人瞩目的跨世纪的赋学工程。
为什么要编这样一部宏大的赋选,赵逵夫在《后记》中所提出的三个针对与四点想法,有助于读者对其编选用心的理解。所谓三个针对,即针对目前研究重理论而轻文献、关注重点作家而忽略面的拓展、学术化明显而普及性不足诸问题。综此三端,其本质是针对20世纪以来赋学研究的反思。所谓四点想法,其一,通过广泛选录,显示历代赋家的创作成就,并提供赋学入门的基础;其二,通过注解使古本中的赋作成为文学爱好者的读物;其三,通过作品简析,以彰显赋作光华,推进辞赋思想与艺术的研讨;其四,通过对作者的介绍,使历史上的赋坛高手为人熟知,并阐发其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综此四点,其主旨在促进赋学研究的同时,更着意于对赋学经典的普及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这部赋选在普及经典的同时,也在树立一种经典,因为“经典”的树立,实质是一种“纠正”,辞赋经典的树立,就是在不断地纠正与变迁中发展的,而选本则充当了重要的角色。赵编所说的三个针对就是一种纠正,其四点想法又是树立经典的构想。这部赋选虽由赵逵夫先生主编,而参与的主编尚有尹占华、霍旭东、龚喜平诸先生,还有韩高年、李占鹏等40多位教授学者,其学术价值已隐含于此艰辛而漫长的研究过程中。赵编全书有总前言,历述中国赋学的时代变迁与思想艺术,在每卷前又有“概述”探讨一代赋风及成就;每篇赋作前有介绍文字,赋中详注,赋后品评,或考证其真伪,或辨析其义理,或品鉴其词章,使之成为一部既具有广泛普及意义,又具有很高学术研究价值的赋学经典。当然,这并不仅限于赵编丰富的内涵和诸多具体而微的创见,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体现出编者对赋学的深刻理解,其中包括赋学的主旨、体式与意义。
首先,赵编体现了一种立足于创作本身的赋学历史观,从而使这部赋选成为主旨鲜明的形象化的“赋史”。这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赋的起源问题,赵编在《前言》中撇开争论不休的“诗源说”、“隐语说”等,从宏观的视野与本体的意义,探寻其内在的“语言”本质,阐发赋体产生与形成的“汉语特征”。缘于此,编者一改前贤重“汉赋”而轻先秦的思路,特辟《先秦卷》,以展现先秦赋滋生发展的整体风貌。同时,也改变了人们把赋源依归于“屈宋”或“荀宋”的做法。赵编首选《师旷》篇中的《五指之隐》、《太子晋》、《天下有五墨墨》、《炳烛》,分别录自《说苑》、《逸周书》、《新序》等杂史著述中,展现其“赋”的讽谏内涵与铺陈特征。与其说赵编首选之作是反映其赞成“赋起于隐”的观念,毋宁说是站在新的高度即“语言”学原理的批评观使然。正因如此,赵编在《前言》中针对当代赋学批评,提出对“不能说用现代汉语写的赋就不是赋”的质疑,而他肯定的方面显然承续了郭绍虞先生早年在《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一文中有关“当现在语体盛行的时期,不应再有语赋——白话赋——的产生吗”的期待。二是赋的发展与变迁,赵编最突出的思想表现于每卷的概述中。七卷本卷首的“概述”,前四篇由赵逵夫先生撰写,分别是《赋体溯源与先秦赋概述》、《汉赋概述》、《魏晋赋概述》、《南北朝赋概述》,特别是第一篇的论述尤见其治赋思想与功力;后三篇则分别是尹占华先生撰《唐五代赋概述》、霍旭东先生撰《宋金元赋概述》、龚喜平先生撰《明清赋概述》,因时论赋,各具特色。如果将此七篇文字抽绎出来,就是一本简明赋史,再配以大量辞赋作品与评论,谓之形象的赋史,似不为过。尽管赵编表现的赋源思想仍可以讨论,然其体现的“史观”,正是“赋选”的灵魂。
其次,赵编以辨体的意识从事选赋实践,所以书中始终贯穿着编者对赋认知的“体式”观,而这种“体”的观念,既是其选赋的思想基础,也是一种具有理论意义的批评态度。一种文体的形成、发展与批评,始终处于尊体与破体之间,而辨体则是一种批评态度,由于赋体的包容性(体类众多)与依附性(介乎诗文之间),辨体显得尤其重要。古人选本,体类多异,例如清代一些赋选本有的将“骈体”列入“古体”,有的则列入“近体”,而骈文选本,或是“赋”皆入“骈”,或是“赋”皆非“骈”,大相径庭。赵编辨析赋之体式,虽多依从前贤之四分法,即骚体赋、诗体赋、骈体赋与文体赋,且以“文体”为主,但其更为关注两方面文章,也彰显为其特色。一是对问、设论之作,虽不标赋名,赵编多有收录,例如前引《师旷》诸文,另外还有如《晏子春秋》诸篇,《史记》中的淳于髡《讽齐威王》,佚名《宋元王梦神龟》,佚名《说弋》,《国策》中的莫敖子华《对楚威王》,《庄子》中的庄辛《说剑》等,尽归于赋。这一思路虽承续姚鼐《古文辞类纂》收《国策》《史记》中三文(分别是《淳于髡讽齐威王》、《楚人以弋说顷襄王》、《庄辛说襄王》)入赋,但赵编更加突显其义,兼收更为广泛,究其根本,仍在赋体的铺陈特征。二是对俗赋的重视,赵编将此视为一大赋类,而区分于所谓雅致的文人创作。例如《汉代卷》收录无名氏的《神乌赋》和王褒的《责须髯奴辞》等,既突显出土文献的价值,也能以赋体“铺陈”的特征兼融雅俗,使赋选显得视域更广,体裁更加丰富多彩。出此赋学视域,编者对汉代以散体大赋为主的“一代文学”之说的偏颇提出商榷;也正因如此,编者对一些隐藏于其他文献的赋文多有发掘,例如《唐五代卷》收录李商隐的《三怪物赋》,在旧题苏轼撰《渔樵闲话录》中,经王应麟、陈心源的考证,始归李氏,编者从之,则改原名《赋三怪物》为《三怪物赋》,落点正在其文本的体式。当然,由于魏晋以后赋作众多,赵编采用非标明“赋”者不收的原则,与其广视域的赋体观产生龃龉,比如明人黄省曾《钱赋》远源于成公绥、鲁褒《钱神论》,鲁作素为选家视为赋,因其体例,赵编只能舍弃,得失之间,或可商榷。
再者,赵编本着修辞的原则对赋所作解析,具有赋体“词章”学意义,这也是该书提供给读者的审美体验。早在上世纪40年代,万曼撰写《辞赋起源:从语言时代到文字时代的桥》,而饶宗颐在《辞赋大辞典序》开篇即谓“赋以夸饰为写作特技,西方修辞术所谓Hyperbole者也”,均已关注赋体由语言到文字,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修辞艺术。赵编讨论赋源,主张从语言学原理考量,且落实于文本,所以书中对赋的词章分析,可以说由零汇总,构成极为宏整的赋体词章学的审美体系。例如对《国策》中的《对楚威王》和《晏子春秋》中的《景公饮酒不恤天灾》等,编者不仅视之为赋作而选入,而且通过详细而深入地分析,从词章结构着眼,逐层解读,展示出赋之体式与美学价值。如此例证,在赵编中是举不胜举,而通观全书中对汉大赋的铺张,对骈体赋的对偶技巧,对科场律赋的艺术法则,对宋文赋中散体中的诗意,分析钩沉,从字句、段落、谋篇到体势,考述具体,体悟深切,是值得关注与肯定的。这其中既有赋学研究价值,也有赋学的鉴赏趣味。
以上三点,从表面上看难以概述赵编的成就,甚至与其具体内容相去或远,但如果从赵编的宏大建构与具体分析中去体味其编选用心,此三点作为本人阅读该书的一点体会,或可为读者提供一些借鉴。
(本文编辑 陈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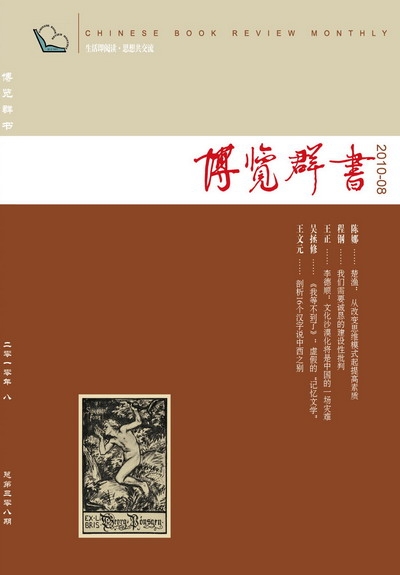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